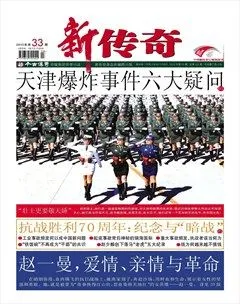寒冰地獄:蘇聯日俘的生與死
在很多地區,進入醫院等同于死亡,肺結核病人只能任由其咳死在不斷嗆出的血痰里。醫生不懂得消毒,憑著一腔蠻勁兒,用普通的剪刀為戰俘剪掉凍傷的手指,用礦場里切金子的鋸為戰俘截肢,術后三四十天的高燒和幾乎百發百中的感染使很多戰俘命喪黃泉。
1945年8月9日零時10分,蘇聯屯駐邊境的160萬大軍突然大舉入境。9月2日,全體關東軍向蘇軍投降。在鋪天蓋地的蘇聯紅色海洋中,昔日傲視東北大地的日本人已無立錐之地,能在這個新世界里茍延殘喘的唯一方法,就只有按照“天皇玉音”里所說的那樣:“堪難堪之事,忍難忍之物”。
通向極寒地獄
到底有多少日本士兵放下武器后被關進蘇軍收容所仍然是個未知數,蘇聯方面公布的戰俘數字是59.4萬人,遠遠超過關東軍總參謀長秦彥三郎向蘇軍報告的45萬這個數字。但實際上,這兩個數字都同樣水分不少。秦彥三郎試圖將停戰前被強征的16萬新兵刨除在外,在他看來,這些毫無軍事經驗的新兵不應對戰爭負有任何責任。但蘇聯人卻不這樣認為,在他們看來,只要是身著軍裝的人,哪怕是出現在軍事設施中人,都應當被看作戰利品。
每一列長達數百米的狼狽的日俘隊伍,都由荷槍實彈的蘇聯士兵騎馬押解。在這群日俘被蘇軍的押解下一路北上時,幾乎沒有人知道自己的最終目的地是蘇聯。在蘇聯人看來,這個謊言卻是必要的,因為他們相信如果一開始就告訴這些戰俘他們的目的地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勞改營,那一定會造成極大的恐慌和混亂。負責押送的蘇聯士兵開的槍已經夠多了,每一顆子彈都很珍貴,至少比這些戰俘的生命更值錢。
這個謊言在蘇軍出兵東北時就已經初具雛形。蘇聯人有自己的理由,他們是這場世界大戰中犧牲最大的國家,超過2700萬人死在戰場上或是消失在蘇聯關押自己被遣返戰俘的勞改營里,直到戰后15年,蘇聯20到30歲的青年人口男女比率仍是6:10,滿目荒夷的戰后大地亟須輸入新血來恢復活力,這些來自各國的戰俘就成為最適合不過的勞動力。8月23日,也就是蘇軍與關東軍簽署正式投降協定的5天后,蘇聯國防委員會通過了第9898號《關于日軍戰俘的接收、安置、勞動使用》決議。
在這份出自一個計劃經濟已經高度成熟的政權之手的文件中,各人民委員部的戰俘人員分配精確到了個位數,從人數最多的內務、建筑工業、林業、煤炭、冶金一直到人數最少的海軍、河運和造船工業,近60萬日軍戰俘被精致而科學地分配到不同的行業之中。“質量最好”的戰俘會被送進斯大林和貝利亞親自“關懷”之下的直系收容所,享受和蘇聯正統的古拉格勞改犯一樣的待遇;其他戰俘則分別送進各企業管理的戰俘營和武裝力量部管理的戰俘營,他們的“待遇”也許不如直系戰俘營那樣管理得“系統而有序”,紀律會比較松散,但工作環境可能會更加嚴苛。
勞役的餓鬼
每當碰到自己的大腿,山本善丸就會想起伊爾庫茨克漫長的、寒冷的、缺衣少被的冬天,還有脫得一絲不掛,凍得上牙打下牙地站著,被神情嚴肅的蘇聯女軍醫檢查身體的情景。這種檢查名義上是記錄每名戰俘的健康狀況,但實際上,只是“捏捏肚子和屁股的表皮,以胖瘦決定身體的狀況。”根據肉的厚薄,這些戰俘會被分為三等。
沒人愿意分在第一等。那些“屁股上肉最多”的人,可能是最不幸的一群,因為這些“最健康”的人必須從事最重的體力勞動:伐木、采石、搬出枕木和模板、房屋建筑、鋪設鐵軌。如果在礦區的話,這些身材矮小的日本人被當作是最合適的挖掘機器,他們會被派遣到最危險的狹窄礦洞里,在完全沒有任何安全設施的情況下安裝炸藥或是架設框架。即使他們逃過了頻繁發生的礦難,粉塵和窒息也會時時刻刻要了他們的命。
但最不幸的是那些在“特殊機構”工作的日俘,在負責開發原子彈的車里雅賓斯克-40工程場地中,荷槍實彈的蘇聯士兵嚴密地監視著這些日本戰俘的一舉一動。1949年7月底,就在原子彈試爆之前的一個月,蘇聯政府下達指示,“參與了與制造原子彈相關的重要特殊工程建設的各類戰俘和犯人都應成為幽靈”。
如果被分在了二三等,也并不意味著他們就能逃脫苦役的厄運。蘇聯人對日本戰俘的順從和賣力贊賞有加,“在很長時間里蘇聯都不太愿意釋放這些日本戰俘回國。”
但最具有黑色幽默的一點是,高強度的勞動,反而與刺骨寒冷下的缺衣少被相得益彰。從某種意義上講,“生命在于運動”這句話非常適合成為收容所的座右銘,到了戶外,不運動血液就有可能凍住,甚至可能會凍死在這片被遺忘的冰雪荒原之中。
盡管高強度的勞動可以給身體帶來暖和起來的假象,但身體真正的熱量來源,卻是食物。為了體現共產主義人道的優越性,1945年9月28日通過的《日本戰俘糧食供給標準》無比精細地規定了每天的食物數量。但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名日軍戰俘體會過蘇聯政府的人道關懷,在戰俘穗苅甲子男的記憶里,從冬到夏,從春到秋,每一天的兩頓飯都是黑面包和土豆泥,外加半桶紅茶水或是略有咸味的菜湯。一塊3公斤的黑面包,要分給16個人,即使分配得再平均,每人也只能大致分配到190克。但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
在那些更加貧乏的收容所里,所有可以果腹的東西都成為人們搜求競逐的目標:貓、狗,甚至是鼴鼠、野鼠、青蛙和蛇。在安吉連收容所,蘇聯士兵會用“恐懼輕蔑的眼神”盯著日本兵們“平靜地吃著蛇和狗”,而且“因為第一年捕獵得太多了,以至于第二年春天時,幾乎見不到蛇了”。
死亡并不平等
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日軍戰俘的日常生活,應該被稱為日常死亡才對。因為生存本身已經成為一種近乎獸類的本能,而無時無刻襲來的死亡反而更具有生活的氣息。
比起凍死和餓死,疾病和瘟疫的死亡都已經算得上是善終,這些病人有時會被送進蘇聯軍醫院或是可怕的遺忘收容所。但對大部分戰俘來說,這兩者完全是一回事,在很多地區,進入醫院等同于死亡,因為一般的醫院里甚至連阿司匹林和止瀉藥也沒有。肺結核病人只能任由其咳死在不斷嗆出的血痰里。醫生不懂得消毒,憑著一腔蠻勁兒,用普通的剪刀為戰俘剪掉凍傷的手指,用礦場里切金子的鋸為戰俘截肢,術后三四十天的高燒和幾乎百發百中的感染使很多戰俘命喪黃泉。
對戰俘來說,惡劣的環境讓死神滿載而歸是件無可奈何的事情,畢竟在面對死亡這方面,大家似乎取得了平等。但內部的魔鬼卻也在向死亡進行殘忍的獻祭,就更為令人發指。
吉村是烏蘭巴托西北部羊毛廠戰俘收容所里的隊長,他發明了“祈禱天明”這種聽起來很美的私刑懲罰。吉村規定他手下的戰俘必須每天早晨四點半起床,早飯前每人必須從兩公里外的山上運回兩根木頭,早飯后,則是連續八個小時的燒磚、紡羊毛和鑿石頭以及收木筏的工作,直到晚上九點半才結束。如果有人完不成任務,吉村便會罰這個人脫光衣服,綁在樹上,站在戶外“祈禱天明”,而吉村和他的同伙卻在屋里飲酒作樂。天寒地凍加上饑腸轆轆,到天明時,這個戰俘往往只剩下低低的啜泣,然后便斷了氣。事實上,吉村并不是唯一以虐待難友為樂的戰俘隊長。
戰俘營里的官兵待遇也各有等差,軍官往往在分配食物時獨霸最大的一份。死亡的平等就這樣被輕易地破壞了。一名叫村山常雄的戰俘,在離開西伯利亞后統計了46300名死亡戰俘,結果將校死亡只占死亡總人數的1.5%,下級士官也只有8.3%,剩下的90.2%全是像他一樣的普通士兵。至于死亡的總數則至今是個爭論不休的數字,蘇聯官方從來沒有通報過一個直接的數字和死亡名單。日本自己的統計數字則是5.5萬人左右。日本的民間卻流傳著死亡人數實際上超過20萬人的說法,在這個說法中,到西伯利亞的行進途中就有4萬人死亡,而后來的奴隸勞動則造成16萬人死亡。
盡管這些戰俘一直在西伯利亞冰冷的荒原上被人遺忘地勞動,但日本國內卻一直堅持不懈想方設法地接他們回國。最終,日本政府答應了蘇聯政府提出的7760萬美元的巨額遣送費,用必需的商品作為抵償。這些努力最終換回了51萬名戰俘的歸來。日本共產黨領袖德田球一暗中向蘇聯當局提出要求,“俘虜的日本人不經過共產主義教育,不能讓其回國”,蘇聯政府對這個想法相當贊賞,認為這樣可以將日本戰俘改造成埋在日本國內的一顆共產主義革命的定時炸彈。活著的人不得不“高聲大嗓地唱《紅旗歌》和《國際歌》,并且表達自己對斯大林同志和共產主義的無比熱愛之情”,才被允許返回自己的祖國。(水云間薦自《國家人文歷史》2015年8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