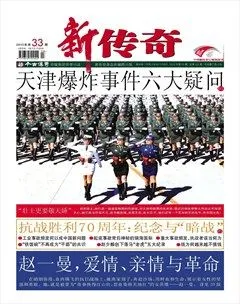“一·二八”事變中的各方博弈
華界地區一塊面積巨大的狹長地帶,被劃入了日軍的防區。更令人吃驚的是“防衛委員會”在擅自作出這一重大變更之后,竟然沒有以任何形式向上海市政府或中國軍事當局進行通報。蔣杰認為,這為此后“一·二八”事變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1932年在上海爆發的“一·二八”事變,構成了中國抗日歷史書寫的重要部分。在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博士后蔣杰看來,“過往的研究者習慣于將這一事件放置在整個中日沖突的大框架下來審視,比較注重從宏觀的政治、軍事和國際關系的角度來解讀這一事件,但忽視了上海本地的因素。”他強調,1930年代初的上海,是一個中、日、西方列強以及工部局相互博弈斗爭的復雜“角力場”。他認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一·二八”事變的源起中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
工部局的“防衛委員會”是什么?
不少人認為,公共租界工部局就是英美勢力在上海的代言人。但事實上,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情況不同,公共租界工部局自建立之日起就與英美外交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與沖突。蔣杰將工部局比作一個股份有限公司,它甚至試圖擺脫各國控制,成為一個類似“中立國”的獨立市。
蔣杰介紹,自租界設立以來,租界防御一直是與地政、稅收、警務以及市政建設同等重要的關鍵問題。租界建立初期,防御問題主要是由僑民和海軍、水手等一起負責。此后又產生了萬國商團并逐漸將租界的防御制度化,最終衍生出專門負責租界防御問題的工部局“防衛委員會”。
工部局“防衛委員會”成員包括:高級駐滬防軍司令、工部局總董,各國駐軍司令官、萬國商團司令、工部局警務處總巡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機構中,不包括任何中國籍委員和觀察員。換言之,它做出的任何決議,中國政府都不得而知。
1927年,北伐軍兵鋒直指上海。西方列強為了保護各自的殖民利益,紛紛派遣軍隊保護公共租界,便有了“防區”的劃分。按照“防衛委員會”事先擬定的計劃,英國、意大利和美國海軍負責公共租界西部及滬西越界筑路地區,租界中區由萬國商團和英美聯軍負責,而租界東部的楊樹浦和虹口地區由日軍防御。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上海原本已經十分緊張的中日關系,變得更加劍拔弩張。隨著十九路軍的進駐,公共租界當局更感到了明顯的壓力。因此,“防衛委員會”于1931年11月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討論了十九路軍進駐上海以后的租界防衛問題,并修改了原來的“防區”范圍。
這一修訂最大的變化在于日軍防區的西擴。1927年時,日軍的防線被嚴格限制在工部局所控制的北四川路越界筑路一線。1931年的修訂,則將防線被擴展到吳淞鐵路沿線,推進距離約為700碼(約640米)左右。結果華界地區一塊面積巨大的狹長地帶,被劃入了日軍的防區。更令人吃驚的是“防衛委員會”在擅自作出這一重大變更之后,竟然沒有以任何形式向上海市政府或中國軍事當局進行通報。蔣杰認為,這為此后“一·二八”事變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一·二八”事變是怎樣爆發的?
在“一·二八”事變爆發之前,1932年1月18日發生了“三友實業社”事件,1名日本僧人因此喪生。兩天后,一群日本暴徒來到三友實業社尋仇,他們在返回的途中又與工部局警察發生沖突,1名華警與1名日本人死亡。從此時起,中日間在上海的局勢急劇緊張起來。
20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正式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五點要求:道歉;賠款;拘捕兇手;取締排日活動和解散抗日組織。
21日,日軍將領鹽澤幸一發表聲明,要求吳鐵城接受村井的一切要求,否則駐滬日軍將會“有所行動”。在此其間,日本人又指責《民國日報》發表有辱天皇的文章,這猶如火上澆油一般,使得原本已經十分緊張的中日關系變得更加劍拔弩張。
25日,村井給吳鐵城發來最后通牒,聲稱如果在28日下午6點前無法得到滿意答復,日軍將要采取必要行動。27日,日軍也通知工部局,如果日方無法獲得滿意答復,日軍將要采取必要行動。
28日下午,吳鐵城接受了最后通牒。村井在下午4點致信上海領事團,對事件的處理表示滿意,并表示日軍暫時不會采取行動。可問題就是,28日晚間,“一·二八”事件爆發了。
既然吳鐵城已經接受了最后通牒,而且日本領事也表示日軍暫時不會采取行動。為什么當天晚間還是爆發了中日武裝沖突?蔣杰提出,工部局的“防衛委員會”其實與這一事件的爆發有無法撇清的干系。因為即便得知“日軍不會有所行動”,“防衛委員會”還是決定從28日下午4點起,宣布公共租界進入緊急狀態。什么是緊急狀態?就是各國軍隊根據此前確定的防御計劃,進入各自“防區”。
隨后,英、美、意軍隊及萬國商團在下午4點先后進入指定防區。日軍則在夜間11點才開始進入防區。當日軍按照既定計劃,試圖進入擅自劃入防區的華界地區時,遭遇了擔負防御任務的十九路軍。十九路軍也是一頭霧水,他們不明白為什么吳鐵城已經接受了最后通牒,日軍還來挑釁?但無論如何,雙方都沒有退讓。“一方毫不妥協,一方又急于推進,沖突在所難免,‘一·二八事變由此爆發。”
“由于吳鐵城全盤接受村井的最后通牒,日軍失去了發動戰爭的由頭,但‘防衛委員會下達了戒嚴令,日軍還是需要進入指定防區駐防。而該委員會給日軍劃定的防區,卻包含了一塊被擅自劃入的華界地區。”在蔣杰看來,“公共租界工部局對‘一·二八事變的爆發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是“無心之失”還是“有意為之”?
蔣杰說,事變爆發第二天,吳鐵城發表文章對工部局進行嚴厲的指責。但吳指責的重點并不在于工部局為何執意下達戒嚴令以及“防衛委員會”為何擅自擴張防御范圍,而是指責“工部局聽任公共租界被用做進攻中國部隊的軍事行動根據地”。
當工部局發現上海市政府根本不了解引發戰爭的真正原因后,也就“順水推舟”地把話題引開,狡辯說“工部局作為一個團體不能對那些能夠共同保證租界中立的強國之一的侵犯公共租界的行為擔負責任。日本作為這些強國之一,像其他有關的主要強國一樣,對維持公共租界的完整感到興趣;任何強國的可以被解釋為破壞這種中立地位的行為,其責任應由各該強國擔負,而不是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擔負。”
現存史料無法證明,英國駐滬外交人員在事件爆發之時是否意識到工部局的決定將會造成一場巨大的沖突。但他們事后提交英國外交部的文件顯示,他們對引發沖突的真正原因心知肚明。至于工部局為何執意宣布戒嚴,英國駐滬外交人員的辯稱是為了防止公共租界邊界附近的中國難民進入租界尋求庇護,同時為了防止中國部隊進入租界進行搶劫。
至于工部局的真正目的,有學者認為是“借刀殺人”,即利用日軍來“教訓”上海的中國當局,從而獲取更大的利益。因為在1927年,中國的民族主義隨著北伐戰爭的爆發蓬勃發展,這引發了工部局與上海華界政府的大量矛盾,包括上海華界政府要求收回公共租界、廢除治外法權、租界增設華董席位、抵制日貨運動以及越界筑路問題等,尤其是后者對工部局的打擊最大。
“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而言,這只是一種推測,我們無法找到直接的證據來佐證這種說法。要弄清工部局所犯下的錯誤究竟是‘無心之失還是‘有意為之,還需要找到更多的檔案資料。”
“一·二八”事變給工部局帶來了怎樣的后果?蔣杰分析,事變發生之后,隨著工部局介入調停,華界政府對公共租界的態度有了一定的“軟化”。但工部局在這一事件中也損失慘重。“一·二八”事變時期,日本人在公共租界東區的勢力急劇膨脹。虹口和楊樹浦地區逐漸演變為日本人的勢力范圍。
蔣杰表示,由于缺乏一手文獻,有關“一·二八”事變的很多問題仍是未解之謎,例如“防衛委員會”擅自修改防御范圍后,有沒有向外國公使團報備?為何1月28日“防衛委員會”下達戒嚴令后,英美等國軍隊以及萬國商團都在下午4點就陸續進入防區,而日軍卻在晚間11點才推進到他們的指定防區等。這些問題的解答,都還有待于檔案資料的開放與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入。
(澎湃新聞 201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