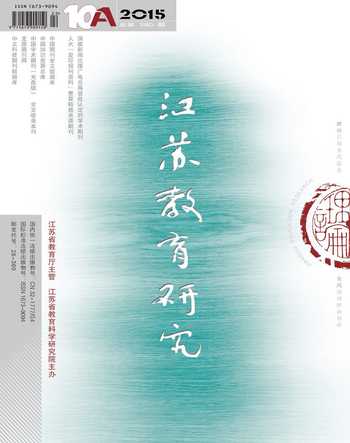本體·本因·本旨:哲學視角的教育反省
林宣龍 潘旭輝
摘要:以哲學的目光來審視,教育之本體乃是蘊含教育價值的生活,教育之本因乃是人之學習需要,教育之本旨乃是實現人之整體和諧發展;現代教育脫離了本體,割斷了本因,迷失了本旨,亟待回歸生活,遵循需要,致力“成人”。
關鍵詞:教育,生活,需要,成人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15)10A-0007-04
學校的全部意義在于履行社會賦予的教育使命,這毫無疑義;履行教育使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教育質量,這毫無疑義;提高教育質量的重要策略在于教師傾注心力教學生傾注心力學,這也毫無疑義。然而,當目睹“五嚴規定”、“減負禁令”從來都難以治本、當今學生依然身處“水深火熱”的應試教育痛苦之中時,你是否起過質疑之意?是否動過惻隱之心?是否盡過點滴之力?
有人說,因為驚異,所以哲學;有人說,因為迷惘,所以哲學;有人則說,因為痛苦,所以哲學——這些都足以表明:哲學確實是“智慧”之學。中國的教育,目前是真正讓人驚詫,讓人迷惘,讓人痛苦,所以應該哲學地審視一下了,讓哲學去洞察教育(原為何物、竟有何理、終求何的)的本原何樣、本真何理、本旨何在。于是,筆者面對當今教育聊作哲學之思。
一、教育的本體之思
2011年暑期在揚州參加省級培訓面授,聽了嚴華銀先生一個報告。他用這樣一個案例作為開講導入:
某教師教《阿Q正傳》,走進課堂,說:“同學們,咱們今天學習《阿Q正傳》,請打開教輔用書某某頁,先做1—8題。”一看,這8題是看拼音填詞語、加點字解釋、完成成語之類。做完這些用了10分鐘,教師就講解這些題目,讓做對的舉手,不時表揚“哎,不錯”。我以為下面可以學習課文了,誰知,他又說:“好,接下去做9—12題……”
一堂課上完,還沒有去碰碰課文。我把教輔用書拿來,問他:你下面還想干什么呢?他說:接著做13—15題唄。我仔細看了13—15題,里面有一點涉及課文中的語段。
這個故事聽來耐人尋味,發人深省,甚至令人驚詫莫名,令人憂慮無比!筆者聯想到了另外聽到的“教學趣事”,說現在中學里的物理生物化學都不再“做實驗”了,而是以“背實驗”替代“做實驗”,這是不是比以做習題替代學課文更荒唐?我為之驚詫的是:這竟然是教育?教師竟然這樣來“做”教育?教育本來究竟是怎樣的?于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對教育作本體之思。
何謂本體?本體即是人或事物之自身、本身、本相,是人或事物保持其作為“自我”而非他者存在的內在同一性與時空確定性特質。人或事物處在不斷的發展與變化之中,其發展變化包含外在形態(量變)與內在性質(質變)兩方面,但它們往往并非內外同變,外變也往往不可能真實反映內變,而是可能呈現內外異步、內外異向、內外異質等復雜情形,故從外變現象往往無法得知事物是否依然保持著那個自身、那個本體,在這種情況下,追根溯源,究其最初的原始的存在形態,方能重現其本原,見得其本體。教育,經歷了漁獵、農耕時代,已經到達發達的現代工業乃至大數據時代,其外部形態與內在性質都發生了超乎想象的變化,它是否還保留著原先那種“本性”?是否還是它自身?我們不妨回望人類最初的教育狀貌,進而再認教育之本體。
教育之本體,即是教育原生態,即是人類誕生初期的教育形態,是“荒野文化”[1]背景下的教育,那時的教育“尚未分化成專門的活動”,“而是在生產與生活中,并結合勞動與生活進行”[2]的,它與生活完全同一,兩者融為一體,不分彼此,處在同時、同在、同步、同構狀態。長(所謂教育者)幼(所謂受教育者)同處于生存實踐場景與過程中,他們在生存實踐中進行著生產、消費、交往、娛樂等活動,在生產、消費、交往、娛樂活動中發現、生成著經驗、意義,同時傳遞、授受著經驗、意義,所以生活便是教育,教育也是生活,更直白地說,教育與生活同體同在。經驗的日益豐富,意義的日益復雜,且生存條件的日益富足,催生的專門化教育。經驗、意義,被人們從生活中抽離出來,并將其課題化、體系化,這原本不是壞事,只要付諸教育過程時作精當的還原,經驗、意義依然不會空洞,依然能以親和的“形象”被學習者愉快地接受。然而,形如《阿Q正傳》的教學,不僅沒有將魯迅創作該作品的時代背景作必要呈現,甚至連“生成”意義的整體語言環境——文本都拋諸腦后了;又如,“做實驗”變成“背實驗”的教學方式,將科學原理植根的最基本事實都丟棄了,這還能算作教育嗎?這種所謂“教育”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必將枯竭、凋敝——終究不再是教育,終究不能給學生任何裨益,更遑論促進人的整體發展!
二、教育的本因之思
從教幾十年,我常見這種情形:
老師說“今晚老師不布置作業了,你們可以讀自己喜歡的書,也可以與家人合作搞個對對子或成語接龍什么的”,同學們會喜形于色;可假如老師說“今晚回家,請大家把新學的課文讀3遍,并且背下來”,學生便會立刻眉頭緊皺,覺得做這事兒太沒勁。
老師說“同學們,學校決定星期×到××地方春游”,學生立刻會歡呼雀躍:“哇!”“太好啦!”可假如老師說“同學們,這兩天咱們美術老師生病了,下午美術課改上語文課”,學生馬上像泄了氣的皮球,癱坐在椅子上,各有各的痛苦表現:有的拉下臉,現出不滿的神情;有的搖搖頭,大有不可思議的意思;有的“啊”了一聲,表示非常驚異;有的“噓”聲連連,自然是難言的失望。
在家,常見到孩子這樣的情形:放學回家做完作業,習慣從書櫥的童書中抽出一本,有時是翻了翻,馬上放回去再另拿一本,又翻了翻又放回去另拿一本;有時翻了翻,立即拿去專注地看起來,而且很專注,到該吃晚飯時叫她,她都不想站起來……
以唯物辯證的哲學目光觀照世界,任何事物都處在發展變化之中;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有其原因,又稱動因,事物之發展變化是由原因引起的結果,原因與結果構成一對哲學范疇,“揭示了事物之間前后相繼、彼此制約的關系”[3]。必須指出,引起事物發展變化的諸多原因中,有的來自客觀外物,有的源于主體自身,前者通常稱之為外因,后者通常稱之為內因。內因源于事物本體(自身),故筆者將其稱為本因。我們知道,“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因此,考察事物的發展變化,探尋內因比摸索外因更重要;促成事物發展變化,激活內在動因比創造外部條件更重要。
以因果關聯原理來看教育以及教育場景中學生的學習,我們應該由偏執外力催迫轉向注重內力激發,通過探尋學習本因實施因勢利導,來達成提高教學質量、促進學生發展之目的。那么,引發學生學習行為的本因是什么呢?“人有許多需要”,“他們的需要就是他們的本性”[4],“教育和生命內在地融合在一起”,“教育是生命的需要”[5]。這就足見,對教育的需要乃是人的本性,是人愿意學習、樂意接受教育的本因,問題在于我們能否因人而異,適時適性適切適需地提供良好的教育。
前述現象,就其具體內容看,是老師在向學生下達學習任務,或者孩子自選學習項目;就其普遍意義看,均屬教育活動。這些現象在我們眼前身邊隨處可見,我們甚至經常這樣做著,但幾乎從未追問個中奧秘。其實,這是作為教育者絕不該有的麻木,正是這種麻木,使教育固守在傳統牢籠或定勢思維中不能自拔。當我們對這些司空見慣的現象稍加留心稍加辨析稍加比較,便會發現其中差異,如再能做點“哲學”審視,便會猛然發現:老師規定學習內容或下達學習任務,有的之所以會招致學生的厭惡和排斥,那是因為他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需要;有的所以能引發學生的興趣和熱情,那是他們在這方面有著知之或得之的強烈需要。我們知道:教育關涉師生雙邊,是“教”與“學”兩個主體間的互動,直言之,“教”終須指向于“學”,見證于“學”;同時,“學”終須回應于“教”,吻合于“教”,只有這樣,才意味著教育發生了,才表征著教育有效了;而“教”與“學”的這種互動,本因就是學生的學習需要。因此,教育必須植根于學生的學習需要,通過激活需要、喚醒需要、遷移需要、轉化需要,來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又通過順應需要、物化需要、滿足需要,來展開學習過程,進而實現最佳效果,促進學生最佳發展;如果我們熱衷于追求分數,或偏執于關注“教”的需要,無視“學”需要,行埋頭蠻干之“教”,那就必然會撲滅學生原本好奇、好學的激情,必然會事與愿違,導致教育的低效、無效,甚至使教育淪為“偽教育”“反教育”。
三、教育的本旨之思
那是一個冬天的上午,我走進教室剛上幾分鐘課,就見外面又飄起雪來,雪花越飄越大,樹上地上很快開始染上白色,由星星點點到成簇成簇。宜興很少下雪,于是我立刻停下講課,說:“同學們,快到走廊上看雪吧,直接下樓到前面草地上看也可以,好好享受雪的樂趣吧……”話音剛落,學生歡呼著奔出教室,有的站在走廊扶欄前,有的“飛”下樓梯到樓前的草坪上。扶欄前的同學,有把胳膊伸倒外面用手掌接雪花的,有仰探出半個頭臉去淋雪花的;比起他們來,草坪上的同學玩法更多,有從草地上抓了一抔雪朝空中拋去的,有從樹葉上刮下雪捏成團兒扔來扔去的,還有盡力仰起臉張嘴接了雪品咂滋味的……叫聲笑聲在飛舞的雪花間蕩漾。我探頭透過窗玻璃瞄了一下鄰班,見他們很多學生不時伸長脖子往外看我們的學生,顯然也十分想出來看雪,但正專注地講著課的老師嚴肅地批評說:“看什么看?下雪沒看過嗎?就想玩,就會開小差,上課不專心,老師講的東西怎么能聽得懂?怎么能記得住?又怎么能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學生呢,自然是嘟起了嘴。
事之當時,筆者只是做了,只是見了,并未去想:自己這樣做,鄰班老師那樣做,對學生意味著什么?如把兩種做法視為兩種取向的教育,分別蘊含怎樣的目的期待?學生發展狀況又將怎樣?事后重溫,甚是困惑:這樣漫天飛雪的自然景觀,近幾年難得出現,學生更是難得一見。難得“解放”學生片刻,給他們一個難得的機會,看一看,玩一玩,體驗體驗,不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活動嗎?不是可以學到課堂上很難學到的東西嗎?一些老師為何常常吝嗇至此,連這點時間和空間都“舍不得”給學生呢?困惑之余,若有所悟,似有所獲:教育長河里,教育宇宙中,這兩件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的小事,看上去不過是兩位老師不同的“一念之差”偶然為之的,然而,這“一念之差”的偶然中,何以就沒有潛隱著一種必然呢?兩件“差之毫厘”的教學細節中,何以就沒有蘊含著“相隔千里”的教育“大道”呢?筆者以為,它們是目的取向截然相反的兩種教育的縮影,我們可以借此深度追問和探討教育的本旨問題。
何謂教育本旨?即教育的根本目的、根本意圖。我國教育學教科書對教育目的的表述是“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勞動者和各種建設人才”[6]。無疑,這種提法很完備,但帶有明顯的“社會本位”色彩。“教育本旨”則超越社會本位,旨在體現“人本位”理念,體現教育最初那種對人的觀照和對人根本價值的認同。這一問題,中外學界已有頗多研究,灼見甚多,只是不同學人對該問題給出的概念各不相同罷了。康德有“人是目的”的著名命題;馮友蘭說過教育的真義在于“使人作為人成為人”[7];此外,有人強調“教育應將受教育者培養成為主體”[8];有人認為“教育的最高目標就是激發主動性,培養獨立性”[9];有人指出教育“最基本的著眼點就在于培養人對于境遇中各種關系的敏感性與洞察力”[10]……不難看出,以上觀點無不聚焦于“人”,無不表明教育的本旨是“為人”,讓人“成為人”。展開看,就是讓人成為具備高度敏感性、洞察力、主動性、獨立性,能夠融入世界、主宰自我、創造幸福的“生活主體”。
上述案例中的兩種做法,前者在引導學生關注“外面的世界”,培養學生對自然、對生活的敏銳感覺,以及相應的探索興趣,最終能成為“主體人”。后者呢?往高里說是教者在執行官方意志,努力讓學生把國家規定的課程學扎實,成為國家、社會需要的人。可是從其教育行為看,似乎只是想讓學生成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儒生”,甚至只想讓學生成為“考試高手”。不敢想象,長久經歷這種教育的學生還能有什么敏感性、洞察力?還能有什么主動性、獨立性?
上文的探討,大致可以表明:從哲學視角看當今教育,很多教育行為顯然已經脫離了本體,割斷了本因,迷失了本旨。而教育返回本體,便要回歸生活;植根本因,便要基于需要;實現本旨,便要致力“成人”。教育決策者應該在頂層設計上周密規劃,教育管理者應該在評價考核上加強引導,教育實踐者應該在具體行動上從自己做起,從現在做起,否則,人人埋怨大氣候不好卻人人都在助推大氣候惡化,教育何日能有玉宇澄清風和日麗的好氣象?
參考文獻:
[1]閻光才.教育的生命意識[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2(2):49-54.
[2][6]羅正華.教育學[M].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8:22.101.
[3]潘佳銘,郭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12.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6.
[5]馮建軍.教育即生命[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4(1):23-26.
[7]韓淑萍,姜德剛.論人學視野中的教育真義[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3(2):5-8.
[8]陳佑清.培養“生活主體”:教育目標的一種選擇[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9(6):6-10.
[9][德]第斯多惠.德國教師培養指南[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85.
[10]蔡春,易凌云.教育是什么[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6(5):1-5.
責任編輯:楊孝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