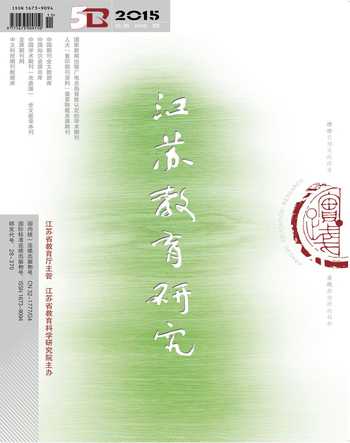家訪,一個重溫的夢
家訪,一個似乎很遙遠的詞語,在來到崇川學校的這一年,它又開始被憶及……
最開始接觸家訪是在2000年,當時還是學生的我被選派到了崇明島上的一處農村小學——海永小學參加教改實驗。那是李慶明老師“鄉村田園教育”的實驗基地,地處偏僻,初來時竟發現校園四周無圍墻遮掩,均為水田環繞。
來到學校,李慶明老師專門為大家作了一些工作指導,其中一項就是晚上要進行家訪。當時的海永原為長江泥沙沉積在江中而形成的荒灘,七十年代才與崇明島相連,九十年代初才設鄉鎮。雖屬海門市,卻與海門市隔江相望;雖位于崇明島,卻與崇明分屬不同行政。由于交通不便,一般有能力的學生都轉到江北的海門市就讀,留下就讀的學生大部分是父母務農的或是外出打工的。學生的家庭情況復雜,輔導學生能力也有限。了解他們的家庭情況,給予孩子最需要的幫助,那是當時二十出頭的我們最淳樸的想法。
于是,每每到了放學后,大家匆匆扒完飯,就會打著手電走向家訪的路。當時參加教改實驗的師范生一共有七人,分屬三個班級。由于僅我一個男生,于是每次家訪,我都是必備人選。鄉間的路窄,不少只是田埂,如遇陰雨更是泥濘不堪。偶爾路遇掛在電線桿的簌簌作響的塑料袋、從草里竄出的貓狗,都會引得大家一片驚呼。
不過,海永鄉地方不大,要找個人家,隨便一問都知道。經常還會有陌生的熱心人一路引領你前往或者推出自行車給你,在感受鄉民們淳樸的同時,每個人的心里都有一些小小的感動。
來到學生家里,每個孩子都顯得異常興奮,或跑前跑后的招呼,或拽著父母的衣角滿臉通紅地注視著你,每個人那閃光的眼神至今記憶猶新。家長也是異常熱情,或泡上一碗紅糖水,或到地里摘個西瓜,更有甚者一溜煙到村口買包瓜子,怎么也拽不住。
往往和家長一聊就是個把小時,有時計劃一晚跑三家,可一聊,跑了一家就打道回府了。那些家長很多是小學畢業甚至小學也沒上完,對于還是學生的我們卻莫名的信服——“你們是城里來的,水平高。我孩子不聽話,你就給我打,沒事的。”這是我們當時聽得最多的話。那時,我們聊的除了教育還有家長里短、油鹽醬醋,在簡陋民房里笑聲飄蕩。
當時,我們用行動得到了所有家長的信任——“南通來的老師最認真”成了鄉間公認的一句話。最后的期末考試,我們幾個班的平均分也總會超出平行班級近十分。
2002年,我畢業了,來到了南通市最好的一所小學——南通師范第二附屬小學,她是李吉林老師情境教育的成長地。來到學校,有些莫名的興奮與激動,一股“干出點成績”的沖動也在心里躍動。
家訪,于是也成了我的最初工作。當時我單獨租住在一處公寓,放學后在街邊一碗面條或者幾個包子果腹后,就會循著家庭信息登記表上的信息,來到學生家里了解情況。由于二附小是名校,當時擇校生也多,學生分布較散。就算找到了小區,找樓牌號也要花費一番功夫。來到家里,孩子一般都被關在書房里看書或做作業,我與家長會交流些孩子的在校情況。家長們也很熱情,切水果、泡香茗,他們似乎對教育也很有見地,會談一些他們的教育理念、手段。不知怎的,彼此竟常會有尷尬的沉默。臨走時,家長總會向你塞一些東西,或是一盒茶葉,或是一盒月餅,有時百般推辭竟不得,只有在事后買些東西給孩子算是回禮。
每次家訪都是這樣,自己也覺得很是尷尬,似乎每次上門是去討東西的。三四次后,干脆就停了下來,有什么情況就在家長接孩子時進行溝通,或者通過手機、家庭留言本來解決。家長也挺主動,沒有家訪,感覺溝通已經足矣。
漸漸地,家訪也似乎成了一個過去式,十余年間也幾乎沒去過任何一個孩子的家,直到來到了崇川學校。崇川學校是委托南通師范第二附屬小學興辦的東校區,但地處城郊結合部。這里以前是農村,五六年前才開始開發建設。從2011年開始建校招生,第一屆的學生生源較雜,有來自當地的農村拆遷戶,有來自城市的白領家庭,也有相當部分來自外來務工家庭,家長們很少會主動和老師交流。考慮到學生家庭情況的復雜,為了更好地讓老師了解學生情況,學校決定讓老師們進行家訪活動。聽說,家訪的效果不錯,了解了不少復雜的家庭情況
2014年,崇川區進行集團化辦學,每位老師都要進行流動,我主動申請來到了崇川學校。到學校的第二周,就接到了家訪的任務。第一次家訪挺搞笑的,班主任聯系了一個孩子的媽媽,說好周五去家訪,可父母沒有交流好,當天孩子的爸爸又來接孩子了。提到家訪的事,孩子的父親呵呵一笑:“省得你們跑了,我這不都來了,去教室里吧。”于是,第一次“家訪”,就在教室里進行了。
第二次的家訪,是孩子的奶奶放學后帶著我們去的。到家后,家里還都沒人,父母加班還沒有回來。于是和奶奶聊了起來,了解孩子的一些情況。正聊著,爸爸回來了,于是一起加入。我教的是第一屆學生,家長大部分學歷不高,有小學有高中,一個班上極少有大學畢業的。他們一般從事著保安、工人、銷售等職業,相對工作較忙,對孩子的教育比較滯后。有的家長沒有能力教,有的家長沒有時間教,甚至還有個別家長持有“讀書無用論”的觀點。他們比農村的家長多了份精明,卻又比城市的家長少了份視野。每次家訪,家長也很熱情,但聽得最多的是“我不懂弄呀”。于是,會一遍遍地提及作業的要求、閱讀的重要。家長也總會認真聆聽,頻頻點頭,他們很少會打斷你,像一個認真學習的孩子。
在家訪中,我們獲得了很多信息——家長介紹的,自己觀察的。家訪后的第二天,每個孩子都會顯得異常神氣——“老師到我家里來了”,也成了他們課余的炫耀資本。現在,與家長交流的渠道也越來越多,QQ群、微信、手機,但家訪仍在每兩周一次繼續著。
三段家訪,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我接觸著不同的家長,也有著不一樣的感觸。也許,家校溝通的方式很多種,但彼此的真誠是最好的橋梁。
(姜達,南通市崇川學校,226014)
責任編輯:顏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