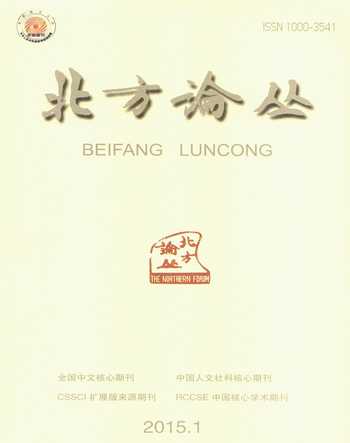唯物史觀在理解或消解中的命運
丁振中 楊思基
[摘 要]唯物史觀創立以來,給哲學甚至整個社會科學帶來了一場革命,一直吸引著思想家們不斷地探索和研究。“西馬”早期代表人物能科學地理解唯物史觀,甚至能對經典理論進行有益的創新和補充,后期代表人物與唯物史觀越走越遠。“后馬”對唯物史觀的態度主要是消解與顛覆,其理論“創新”也基本上與唯物史觀相背離。我們必須用堅持和發展的態度、嚴謹科學的態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范式。隨著時代的變化,我們也應該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加以革新和發展。
[關鍵詞]唯物史觀;西方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
[中圖分類號]B0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5)01-0124-05
Abstra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rought a revolution to philosophy and eve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early western Marxists hav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even can give some supplement or innovation. The late western Marxists go far away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me post-Marxists decompose or subvert historical materialism.We should underst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cientifically by insisting and developing it with the Marxist basic theory paradigm as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Key words: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stern Marxism; post-Marxism
唯物史觀,即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第一個偉大發現”,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也是馬克思及其繼承人從事各類社會實踐活動的理論指南。“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1](p.601)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被認為是馬克思的“兩大發現”,這“兩大發現”才使社會主義從空想發展到科學。唯物史觀創立以來,不僅給哲學甚至整個社會科學帶來了一場革命,也一直吸引著思想家們不斷地探索和研究。梳理“西方馬克思主義”(以下簡稱“西馬”)和“后馬克思主義”(以下簡稱“后馬”)對唯物史觀的認識、理解、創新、解構,以厘清唯物史觀在理解或消解中的命運。
一、走近與補充:“西馬”早期代表人物試圖找回本真的唯物史觀
20世紀,實踐層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曲折發展,西方社會發生許多重大變革;理論層面,斯大林主義經院式、教條地宣傳唯物史觀,第二國際將唯物史觀變為消極的經濟決定論。因此,面臨重重危機的唯物史觀應該予以重新審視和研究,很多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給予了回應。“西馬”早期代表人物如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等,主張返本求源,回到馬克思的文本,重新理解和找回本真的唯物史觀。
青年盧卡奇在他的被標志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圣經”的代表作《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明確指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對這個或那個命題的‘信奉也不是對‘圣書的解釋。與此相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指的只是方法。”[2](p.2)從這個意義上說,相對于第二國際,青年盧卡奇“走近”唯物史觀的本真。青年盧卡奇在“重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基礎上,提出了他所理解的“歷史”、“辯證法”、“總體性”、“非直接性”和“階級意識”等核心概念。[3](p.9) 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實質是總體性,正是總體性的觀點,而不是第二國際的經濟決定論,將唯物史觀與資產階級的科學區別開來[4](p.28)。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首要任務不是消極地反映對象,而是對現實的革命性改造。一旦離開了“總體性”范疇,就談不上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或歷史辯證法,就丟失了唯物史觀的先進性和革命性;相反,掌握了總體性辯證法,才能認識到歷史進程中主、客體的相互作用,才能看到主體的優先地位,才能重建唯物史觀的本真意義。他批評恩格斯把馬克思的辯證法導入自然領域是不合理的,是沒有抓住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質。他還把唯物史觀看成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且與資產階級的物化意識相對立。這些,都是青年盧卡奇在“重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過程中努力“走近”甚至“補充”唯物史觀的體現。當然,青年盧卡奇的“理解”也是有局限的,例如,由于他還沒有讀到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年創立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文本《德意志意識形態》,不能理解與區分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狹義歷史唯物主義[3](p.29)。
柯爾施在重讀經典著作的基礎上,著有《馬克思主義和哲學》、《我為什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唯物史觀原理》等著作。他批評了列寧的“唯物主義哲學”沒有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質。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從本質上看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不能簡單理解為辯證唯物主義,也不能簡單理解為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簡單疊加。柯爾施認為,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演變成了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造成了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的危機[4](p.39)。“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必須再次成為《共產黨宣言》的作者所描述的東西——不是作為一個簡單的回復,而是作為一個辯證的發展:一種關于包括整個社會一切領域的社會革命的理論。”[5](p.33)柯爾施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種關于社會革命的理論是完全正確的。他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觀,特別是他的“總體性理論”,為我們全面、正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方法論的啟示。可惜的是,他過分強調主觀因素而缺少客觀現實性,未能完成他為自己確定的重新實現理論與實踐統一的任務。但是,他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是促使工人運動能夠奪取政權的思想以及“工人階級能夠運轉世界”的思想,沒有人能對其表示懷疑。
葛蘭西在繼承盧卡奇思路的基礎上,結合革命斗爭實際,對唯物史觀進行了重新理解和補充。他強調,要真正領會唯物史觀的原旨思想,必須重讀馬克思的原著。在《獄中札記》中,他強調指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構成了一個統一的歷史總體,唯物史觀把人的意志、觀念等主觀因素放進歷史發展的客觀過程中進行考察,并通過具體的歷史運動來把握歷史必然性,主張歷史就是人的實踐活動,歷史過程中物質和精神的統一,這樣才能反映真實的歷史運動。在《反對〈資本論〉的革命》中,葛蘭西強調唯物史觀的法則并非一成不變。他還指出,深入明確人的實踐活動才是歷史發展的首要因素,這是理解和發展唯物史觀的關鍵。在葛蘭西那里,國家和市民社會同屬于上層建筑,是上層建筑的兩個方面。他認為:“在東方,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處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狀態。在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存在著調整了的相互關系。假使國家開始動搖,市民社會這個堅固的結構立即出面。”[6](p.180)他認為,西方革命的核心是爭奪文化領導權或意識形態領導權。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主要是指一種非暴力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控制手段,這種領導權是通過被統治階級的積極同意取得的[4](pp.41-43)。這可以說是葛蘭西在對唯物史觀重新理解的基礎上的嘗試性補充。
二、誤讀與偏離:“西馬”后期代表人物試圖“改造”唯物史觀
事實上,“西馬”在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和態度上是有很大分歧的,在青年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之后,“西馬”后期代表人物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偏差越來越大。如人本主義、存在主義等對唯物史觀存在一定程度的誤讀與偏離。
人本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馬爾庫塞把弗洛伊德的愛欲本質論與馬克思的人類解放論相結合,提出了“愛欲解放論”;把弗洛伊德關于愛欲受壓抑的觀點與馬克思關于勞動被異化的觀點相結合,發起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他認為,發達的工業社會實行國家干預經濟和高生產、高消費政策,統治者對工人階級的壓制和統治,不再是經濟的,而已轉為意識形態的或心理的了,這就成功壓制了社會中的反對派和反對意見,壓制了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從而使這個社會成了單向度的社會,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不過,馬爾庫塞認為,“科學-技術的合理性和操縱一起被熔接成一種新型的社會控制形式。”[7](p.117)造成單向度的社會、新型極權主義社會的原因是技術進步。馬爾庫塞的理想社會是:“多余的壓制”已徹底消失,人們從現有的勞動中解放出來。[4](p.103-108)馬爾庫塞還認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革命的主體力量是新左派。在《反革命與造反》一書中,他認為,工人階級已經被當代西方社會所同化,喪失了革命意識,甚至有反對革命的意識,于是他更加重視人的心理革命對于實現西方革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人的解放本質上是“自然的解放”的論題。 人本主義過分地強調了主觀性和不確定性,嚴重偏離了唯物史觀的精神實質。
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薩特認為,存在主義的第一原則就是人的“主觀性”,因此,他還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質”的著名命題。薩特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缺乏這種“主觀性”,所以必須用存在主義的“主觀性”來補充馬克思主義,并在此基礎上,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改造成“歷史人學”,對人類發展史作了重新解釋。薩特認為,歷史人學的基礎是“實踐”——一種“主觀性”的“自由”行動,階級則是一個群集體性的群體。薩特強調的不可超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指那種自以為發現了一種自然辯證法的形而上學妄想的辯證唯物主義,而應該是設定了一種歷史的內在辯證法的歷史唯物主義。在薩特眼中,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按照薩特的邏輯,馬克思主義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就是一種辯證法,而這種辯證法是內在辯證法、歷史辯證法,即人學辯證法[4](pp.163-166)。
阿爾都塞在發現人本主義、存在主義的錯誤之后,對他們進行反駁。他同樣強調“回到馬克思”、“回到經典”,在此基礎上,重新理解唯物史觀。作為一名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堅持用歷史結構性方法來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并認為,歷史結構性的方法論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但是,他指出,黑格爾的“總體”沒有復雜的結構,在黑格爾那里,萬物只不過是精神在異化狀態中的具體表現,而在馬克思那里,“總體”是一個由多環節主導結構形成的統一體,馬克思雖然強調了經濟活動的決定性作用,但他也強調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社會要素的并存關系,并沒有把經濟當作一切社會歷史現象的本原。從這個意義上說,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的理解,對唯物史觀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阿爾都塞認為,唯物史觀是多種矛盾并存的“多元決定論”,這一點違背了唯物史觀的“一元論”,違背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
三、消解與顛覆:“后馬”哲學家們對唯物史觀的嚴重背離
后馬克思主義是產生于西方世界的一種激進理論,其突出特征是一方面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提出一系列的質疑與批判;另一方面,又繼續推進全球解放的革命規劃。從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馬克思主義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主義的東西徹底鏟除掉:解構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概念、解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解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還原論、解構馬克思主義的激進革命概念。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后馬克思主義的界定、關于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身份的確認至今也沒有完全一致的說法,但這并不影響人們對后馬克思主義保持一種有增無減的學術興趣[8](pp.1-27)。我國學者俞吾金、陳學明將后馬克思主義劃分為以下四大派別:一是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后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二是以詹姆遜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的文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文化闡述學的馬克思主義);三是以哈貝馬斯、塞麥克為代表的解釋學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后解釋學的馬克思主義;四是其他類型的后馬克思主義,如拉克勞、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后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9](pp.706-707)。
解構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哲學的代表人物德里達,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幽靈”來看待,唯物史觀在德里達那里,沒有具體內容,只是“幽靈”。“幽靈”是德里達建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范疇,解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幽靈說。“幽靈”的根本特征就是它的不在場的在場。德里達認為,必須把馬克思的精神與目前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區別開來,必須從馬克思文本的內部去尋找其精神實質[4](pp.252-259)。德里達強調要繼承馬克思的精神,聲稱“我們是馬克思遺產的繼承人”,他說:“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們愿意與否,知道與否,他們今天在某種程度上說都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10](p.127)。然而,他宣稱的我們要繼承的馬克思的遺產,并不是具體的唯物史觀,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而是經過解構邏輯中介過的所謂的“批判精神”。唯物史觀的重要的基本原則和理論,在德里達那里全部被消解殆盡甚至被否定[11](p.115)。德里達在消解唯物史觀的具體內容的同時,還把馬克思的幽靈、馬克思精神復數化,其實他把馬克思精神也虛無化了。總之,德里達所說的“幽靈”,沒有唯物史觀的具體理論內容,他一直宣揚的馬克思精神中除了“批判”之外看不到其他具體內容,從他所謂共產主義精神中除了“解放”之外也看不到絲毫具體內容。
后現代主義的文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詹姆遜,結合時代特點,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創新和發展,主要體現在他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批判理論”。詹姆遜認為,“缺場”的歷史與“在場”的當下之間具有“同一性”還是“差異性”,造成了歷史主義矛盾或困境。他強調,只有把馬克思主義生產方式作為闡釋歷史的絕對視域,才能解決這一矛盾或困境。然而,詹姆遜過于偏重于文化或意識形態重要性,他提出的“生產模式”,不僅包含經濟發展和勞動技術的方式,還包含文化生產和語言生產的方式。他以文化視角、人的主觀視角來看待歷史,混淆了“個體主觀”與“歷史客觀”,這明顯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方式”概念和歷史決定論的背離。總之,他試圖超越經濟生產層面,并賦予其文化與語言層面的“新內涵”;他試圖用“文化”、“意識形態素”把整個社會結構“擰成”一個更緊密、更具整體性的“社會整體框架”。于是,他的唯物史觀必然與馬克思基于“生產方式”的唯物史觀大相徑庭、越走越遠了。
法蘭克福學派最有名的理論家之一、“批判理論”和新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貝馬斯,面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各種新情況,試圖從“交往行為”理論出發重建唯物史觀,從而為當代資本主義開出濟世良方。他大膽指出:“人們并沒有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無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都沒有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在工人運動的歷史中,人們也沒有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因此,我不能把歷史唯物主義看做是啟迪學,而看做理論,即看做一種社會進化論。”[12](p.104)于是,在社會基礎的問題上,哈貝馬斯否認“社會勞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用“交往行為”取而代之,將其作為貫穿人類社會的基礎;在社會發展動力系統的問題上,哈貝馬斯反對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和“階級斗爭”作為社會發展的動力,用“學習機制”取而代之,將其作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在社會形態劃分的問題上,哈貝馬斯否定了以“生產方式”把社會歷史區分為五種或者六種形態的觀點,用“組織原則”把社會劃分為“新石器社會”、“早期的高度文化”、“高度發達的文化”以及“現代社會”四種形態。哈貝馬斯對唯物史觀的“重建”在基本理論路線上走的是從意識到實踐的唯心主義路線,堅持的是意識決定實踐的哲學基本原則,他所“重建”的理論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理論。哈貝馬斯對唯物史觀的這種“重建”,明顯是對唯物史觀的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曲解,對唯物史觀基本原則的顛覆與消解。
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推動者拉克勞和墨菲聲稱他們的“后馬克思主義”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甚至是一個比馬克思主義更高級的新形態。他們認為馬克思的經典理論中摻雜著幾乎不能成立的一系列認識論假設,面對不斷變化的當代世界,傳統馬克思主義陷入僵局。他們認為傳統的唯物史觀不靈了,傳統的社會主義也不行了。他們在考察了領導權概念的譜系之后,極力主張話語領導權,提出了他們的話語領導權理論。他們認為,話語是社會的生活形式,領導權需要一種總體化的話語邏輯,因此,他們將領導權概念建立在話語理論的基礎之上,社會概念被理解為話語空間。他們還把話語權視為當代社會主義的新策略,認定社會主義并非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趨勢和必然結果,而是社會主義的話語獲得認可。這就徹底告別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客觀性和歷史必然性的邏輯。同時,話語領導權理論也徹底否定了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念。他們解構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否認了由客觀的經濟地位、階級利益所決定的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他們拒斥“狹隘的”工人主義的社會主義概念。他們反對將社會主義理解成一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具有新的生產方式的社會。他們拒斥社會主義革命概念,認為社會主義并不是同過去的革命性決裂。他們拒斥“國家主義式”的社會主義。[4]( pp.245-250)他們還把“階級”從經濟基礎這一分析框架上抽離出來并使其碎片化,以達到其在“資本主義民主”的前提下實現激進多元民主政治的構想。他們的“后馬克思主義”在對唯物史觀的經濟主義的政治模式解構中,消解了“階級”這一革命主體,這明顯是對唯物史觀的嚴重誤讀與消解。
四、堅持與發展唯物史觀:我們的態度和使命
以上分析了唯物史觀在“西馬”和“后馬”那里的命運。總的來說,隨著時代的變遷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新發展,“西馬”或“后馬”的思想家們既能或多或少地回到或者試圖回到馬克思文本中繼承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又提出各自的新觀點進行理論創新。應該說,“西馬”早期代表人物與唯物史觀走得更近,理解得更科學,甚至能對經典理論進行有益的創新和補充,但“西馬”后期所涌現的思想與唯物史觀就越走越遠了。“后馬”不是一個統一的學派,各個后馬克思主義者往往分屬于不同的哲學流派,他們立場各異,觀點獨特,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也大相徑庭。但總體上,“后馬”對唯物史觀的態度主要是消解與顛覆,其理論“創新”也基本上與唯物史觀相背離。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學術界對“西馬”與“后馬”的理解不同,劃分標準不同,代表人物的理解也不同。比如,有學者甚至把“后馬”追溯到盧卡奇、葛蘭西那里,也有的學者對詹姆遜是不是“后馬”的代表人物也有分歧和爭論。本文所理解的“西馬”與“后馬”不考慮類似的爭議,而是采用學界普遍認可的對“西馬”和“后馬”的劃分和理解,從而得出本文的上述結論。
關于對唯物史觀的態度,我們必須用堅持和發展的態度、嚴謹科學的態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范式。同時,隨著時代的變化,我們也應該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加以革新和發展,這也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一種使命。
[參 考 文 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匈]喬治·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M].張西平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3]張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西方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解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4]鐵省林,房德玖.國外馬克思主義概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
[5][德]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M].王南湜,榮新海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6][意]葛蘭西.獄中札記[M].葆煦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美]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8]周凡.后馬克思主義導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9]俞吾金,陳學明.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西方馬克思主義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10][法]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11]張一兵.分延馬克思:被解構了的精神遺產——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的文本學解讀[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1).
[12][德]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修訂版)[M].郭官義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丁振中:蘇州大學博士研究生;楊思基: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責任編輯 張桂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