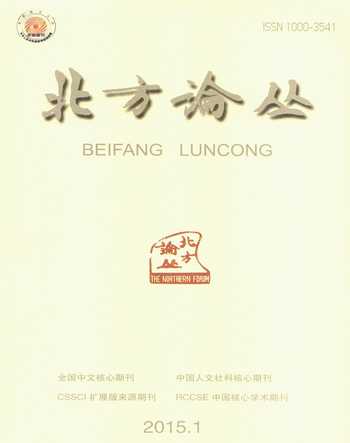論元代延祐科舉的意義
李文勝
[摘 要]延祐科舉的恢復令廣大士人歡欣鼓舞,改變了從吏進的入仕方式,對于館閣文風的成熟有著重要影響。延祐首科得人之盛,引發(fā)了極大的示范效應,引導著天下學風與文風的走向。元代游士盛行,某種意義上說是取消科舉后,文士入仕無門造成的奇特現(xiàn)象,成為元代一道獨特的風景。延祐科舉拯救了新生代文人的科舉夢,同時也避免了他們重復老一代文士的遺憾,對于廣大文人心態(tài)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并進而改變了元代中期以后的文學面貌。
[關鍵詞]延祐科舉;館閣文風;游士;吏進
[中圖分類號]K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5)01-0073-07
元代文人津津樂道的皇帝有兩個:一個是世祖忽必烈,另一個則是仁宗。在元人文獻中屢屢提及二位帝王,是因為世祖混一區(qū)宇,進行漢化,將蒙古國建成了一個有模有樣的中原王朝,為元代長治久安打下了基礎;仁宗皇帝則頒布科舉,震驚朝野。科舉在文人心中的地位是其他途徑無法替代的。
自隋代科舉實行以來,文人對科舉就有著特殊的情懷,將其視為入仕正途,宋代名為夢魁的儒士很多,渴望科舉奪魁,反映出士人深厚的科舉情懷。如南宋名人胡夢魁和徐夢魁,著名詩人方逢辰本名也叫夢魁,中進士后宋理宗親自更改為逢辰,“初名夢魁,淳祐十年舉進士第一,理宗御筆改今名,故字曰君錫。”[1](p.269)“昔楊次公于叔明兄弟以文學知名,皆以父任為京官,不得進由科第,終有不釋然者。”[2](p.487)延祐科舉的恢復令廣大士人歡欣鼓舞,從此改變儒士需從吏進的方式,對于館閣文風的成熟有著重要影響。延祐首科得人之盛,延祐科舉的恢復對于廣大文人心態(tài)的影響是巨大的。
一、元代科舉與游士
元初因取消了科舉,士人入仕之途徑被堵死,嚴重打擊了士人的理想,這與宋代尚儒的學風形成巨大的反差,“里選廢,士不得不游。”[3](p.353)于是游士一時興起,北走京師,“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巖氓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之想。彼誠郁積久而欲肆其揚揚者也,然皆不能無所誘焉。”[4](p.72)游的目的性很強,“游,足廣所聞,以致其道;道成矣,又足致美名厚位。推己有以公乎眾,此古今類然。不則沒踵鄉(xiāng)塵,襲染庸下。”[5](pp.530-531)“游”既是實現(xiàn)理想的手段,也是一種生存方式,終極目的都是官本位。“京師,士大夫之天池也。”[6](p.253)京師在士人眼中是龍池之地,這里人文薈萃,是元朝的政治經(jīng)濟中心,在這里可以結交館閣重臣,推薦自己進入仕途,尤其是在元初科舉廢除后,士人仕進無門情況下,他們不肯屈伸為吏,南北混一后,道路暢通無阻,南人北上成了一股時代風尚,一時間游士激增,而詩文成為他們打通入仕途徑的一張亮麗的名片,他們?yōu)槭硕危持约旱脑娢牟贿h萬里,奔赴京師尋找館閣大佬推薦自己。
在元初“游”是一種存在的狀態(tài),是讀書人失去科舉后畸形的生存方式,不得已而為之,基本都是為利而游。“自田不井,舉選不鄉(xiāng)里,而士之有志斯世者,始不得不托于游。”[7](p.185)大量游士出現(xiàn)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元代游士盛行,某種意義上是科舉取消后,入仕無門造成的奇特現(xiàn)象,成為元代一道奇特的風景。游士的多少與科舉是否舉行有著密切的關系,“自宋科廢而游士多,自延祐科復而游士少,數(shù)年科暫廢,而游士復起矣。蓋士負其才氣,必欲見用于世,不用于科,則欲用于游,此人情之所同。”[8](p.58)士人極其強烈的入仕愿望是游士盛行的主要原因。游士基本都是底層文人,且多為南人,為了生存不得已而為之,“游”是極其艱難的事情,南人離京師較遠,路途遙遠并沒有阻礙入仕的熱情,是不甘于隱沒才華,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體現(xiàn)。元代至元、元貞、大德、至大年間是南人北上的高峰期。
游士在元代開科以后仍然存在,是科舉取士狹窄造成的結果,科舉開始以后,吏進雖然有所下降,官品最高定位從七品,但吏進在開科后依然存在,有元一代取士不過1 200人,入仕不暢是主要原因。“國家未設科舉,始舍學校,無所于仕,故嘗多而壅。十年來,舊制既復,士出身有途,而其壅益倍,何耶?或謂貢士數(shù)狹不足容。”[9](p.43)
游是一種生存的需要,有需求才會有行動,行動受動機的驅使。“宋承唐舊,巖居逸士,見于聘征,游者益恥”[10](p.198),宋代以游為恥,與元代恰恰相反。原因是宋代取士制度完善,山林人士也積極征聘,世無閑士,有才必用。而元代因科舉廢除,有才無用,于是通過“游”的方式達到有用于世。
“范先生者,諱梈,字德機,臨江清江人也……年三十余,辭家北游,賣卜燕市,見者皆敬異之,相語曰:此必非賣卜者也。已而為董中丞所知,召置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由是名動京師,遂薦為左衛(wèi)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浦城楊載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余亦與之游。”[11](p.363)范梈游京師是很成功的,在無重要人脈的推薦下,自己北游京師尋找機會,以經(jīng)商掩人耳目,實則為遇伯樂,以客游于董中丞館下,授業(yè)諸弟子,名聲遠揚,終于被諸館閣大佬推薦至臺閣。
在科舉不開的年代,使得文人有了館閣仕宦經(jīng)歷,圓了他們的人生夢。客觀上促進了館閣文風的成熟。因此,科廢時代“游”的意義重大。
二、延祐科舉與館閣文風
延祐科舉像一根指揮棒,引導著天下學風與文風的走向,“自科舉廢,而天下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為農則為工為商,自科舉復,而天下武臣氓隸之子弟,皆為士為儒。”[11](p.383)元王朝延祐科舉意義非同尋常。“國家設貢舉,陶天下以經(jīng)術,余三十年,文當日益昌。”[12](p.125)延祐科舉對文風改變意義重大。
延祐科舉的恢復客觀上促進了士風的轉變,使得此前“宗唐得古”的潮流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在人心向學的士風下,館閣文風成熟了,詩學結出了碩果趨于雅正。“我元延祐以來,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趨于雅正,詩丕變而近于古。”[9](p.445)“圣元科詔頒,士亦未嘗廢詩學,而詩皆趨于雅正。”[9](p.443)元人認為,仁宗時代是太平盛世,“論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13](p.92)文人盛世心態(tài)反映到文風中,使得此時文風中的治世之音益濃。歐陽玄描述了元代館閣文風嬗變經(jīng)過,“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強,下者萎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于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唱,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9](p.456)延祐文風在科舉的影響下除掉靡麗之習,為文皆雄深渾厚,文益粹然。
科舉恢復以后,館閣入仕途徑走向了正規(guī)化,“以科舉取士,猶盛于多門而進。”[14](pp.4084-4090)伴隨著取士制度完善,從根本上保證了封建時代所需要的政治、文化素養(yǎng),無論辦事效率,還是影響力都超越吏員,處理問題更加合理公正,因為儒士飽讀詩書,儒家文化仁義禮樂深入其內心,在儒家的號召下為官清廉,浩然正氣者居多,從源頭上保證了館閣文人的文化素質的正統(tǒng)性。這在延祐科舉首科取得的進士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今揚于王庭,尚多首科之人。”[15](p.235)如張起巖、黃溍、楊景行、許有壬、歐陽玄、馬祖常等,這就是延祐科舉的社會意義。
“我國家延祐初詔科舉,今二十年,馬伯庸為御史中丞,許可用為中書參政,歐陽元功為翰林學士,張夢臣為奎章學士,科舉之士,臺省館閣往往有之,不為不盛矣。”[16](p.311)元王朝延祐首開科舉,“所取士多為名臣。”[14](pp.4171-4173)延祐首科進士均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處理問題公平、效率高,從實際出發(fā),不迷信巫術,具有儒家的正義感,因此,聲名鵲起張起巖“滹沱河水為真定害,起巖論封河神為侯爵,而移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14](pp.4199-4203)歐陽玄“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為平翻。”[14](pp.4196-4199)干文傅“王遂伏辜”[14](pp.4253-4255),黃溍“溍訪得其情,以正盜宜傳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14](pp.4187-4189)“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所去,民皆立石頌之。”[14](p.4366)充分顯示了延祐科舉取士的意義,是對吏進的否定。作為官員必備的文化素養(yǎng)是從政的基礎,他們營造了一個政治清明的時代,無論是對國家,還是館閣都是有益的。
元代長期不能實行科舉的主要原因是蒙古上層利益的問題,擔心科舉實行后有大批南人進入上層,會對其核心利益造成威脅,故長期遭到蒙古貴族的反對。程鉅夫指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蓋嘗有旨行貢舉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諄切,而妄人則陰沮之,應故事而集議,凡幾作輟矣。”[17](p.121)妄人指蒙古貴族。忽必烈漢化決心很徹底,建官制,定禮儀,建學校,尊孔子,唯獨沒開科舉,歸根結底是因為科舉不符合蒙古族利益,忽必烈本身也不認同,“科舉虛誕,朕所不取。”[18](p.455)忽必烈認為,吏可以代替儒,這與蒙古族一貫重視實用有關。
到仁宗時代用左右榜解決了該問題。仁宗深厭吏弊,重開科舉的主要原因是看到了儒家的重要性,及吏弊造成的負面影響。“仁宗皇帝自居潛宮,及其即位,乃出獨斷,設進士科以取士。”[19](p.135)“仁宗初出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劃出之。”[14](pp.4084-4090)說明仁宗是位仁君,所以,元人文獻里多次提及仁宗恢復科舉的大事。“仁宗皇帝之圖治也,謂入仕多歧,不甚于學,病治為甚……復限吏秩,廣儒用。”[12](p.32)這是對元初入仕多途,吏進為主的矯正,從仁宗開始取士制度才走上正軌,館閣學風自然就會在此時成熟,入館途徑的正規(guī)化是基本保證,這不能不說是大元漢化史中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
元初士風低迷,仕進無門是主要原因,學無所用,“士而抱利器,屈下僚,如轅下駒,受牽縶于庸妄之手,不得一展足為千里試。”[12](p.765)“余昔未仕時,見士之懷才抱藝,有志四方,白首而未遂者,往往悲歌慷慨,悵然負其平生,不勝往日之悔。”[20](p.147)不開科舉使得無仕進之門的儒士心灰意冷,甚至對現(xiàn)實絕望。士有志于四方,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士子的抱負。由此可見延祐科舉的恢復有著不尋常的意義。
科舉的恢復使得文風為之一變,對于改變整個社會的學風有著重要意義。士風大振,如久旱逢甘霖的感覺,社會的學風為之一變。“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于朱子之說。”[13](p.49)“延祐初,有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21](p.323)“昔宋季年,文氣萎靡不振。國家既一四海,文治日興,柳城姚公、清河元公相繼以古文倡,海內之士蓋有聞風而作興者,彥粟亦其人哉!當延祐時,朝廷設科,方務以文取士,大江之南,士之求售于有司者,恒千百人。”[22](p.85)科舉對于士人的巨大吸引力可見一斑,客觀上推動了文風的轉變。天下學風在科舉的引誘下為之一變,元詩四大家之一的揭溪斯曾說元仁宗(延祐)以后的詩風“學者復靡然去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23](p.280)“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24](p.75) “延祐初元仁宗皇帝詔天下以科舉取士,士氣復振。”[25](p.106)
延祐開科意義重大,以程朱理學文科考內容是歷代所無,一改前代詩詞文賦為科考內容的歷史,科舉考試內容的重大變化,必然影響著文風的走向。形成了重根底,不尚空言的文風,文風據(jù)理,考據(jù)精確,矯正了南宋末年科舉文風的流弊。這與仁宗皇帝頒布的科舉詔有極大的關系, 仁宗科舉詔中說:“浮華過實,朕所不取。”[14](p.2017)科舉的指揮棒把文風引向了質實,注重根底實學,客觀上糾正了宋末文風弊端。
延祐科舉吸引了眾多西域少數(shù)民族參加科舉,因為元代實行的是左右榜制度。左榜是漢人南人,右榜是蒙古色目人。蒙古族以右為貴,這種設置方式體現(xiàn)了蒙古族利益至上原則。左右榜的設立是經(jīng)過充分論證考量的,對于平衡蒙古族利益,維護蒙古族特權起到一定的作用。右榜客觀上促進了少數(shù)民族漢化,重開科舉,廣大士人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少數(shù)民族的參與程度是空前的。
“延祐初,詔舉進士三百人會試,春官百五十人。或朔方、于闐、大康居諸土之士,咸囊書橐筆,聯(lián)裳造庭而待問于有司,于時可謂盛矣。”[26](p.403)加速了西域民族的漢化,對于促進民族大融合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也是當初設立左右榜的人沒有想到的結果。
右榜出了很多人才,如延祐首科的馬祖常,從進士直接進入館閣,與很多南人北人交往,切磋文藝,對于館閣文風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馬祖常“其文精贍鴻麗,一洗柔曼卑冗之習。其詩才力富健……稱其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后生爭效慕之,文章為之一變。與會稽袁桷、蜀郡虞集、東平王構更迭唱和,如金石相宣,而文益奇。蓋大德、延祐以后,為元文之極盛,而主持風氣,則祖常等數(shù)人為之巨擘云。”[27](p.4296)后來的薩都剌、余闕、泰不華等都是進士出身,對于元詩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些都是延祐科舉的意義。
雖然科舉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元代儒士的入仕問題,取士的規(guī)模也遠遠不能和唐宋明清相比,但延祐科舉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推動了元代文風的大變革,此時文治達到元代的高潮,天下無事,政治清明,經(jīng)學取士使得文風為之一變,入館閣又多了一個最重要的途徑,館閣文風伴隨著延祐科舉考試的舉行而成熟了,所以,延祐科舉自然成為元代前后期文風的分界線。鄧紹基主編的《元代文學史》把延祐作為元代詩文發(fā)展的分界線,并認為延祐科舉以后的成就超過了此前,并提出了依據(jù):“元詩發(fā)展以仁宗延祐年間為界,可分為前后兩期,延祐以前宗唐得古詩風興起到旺盛,延祐以后宗唐得古潮流繼續(xù)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后期成就超過前期。”[28](p.370)延祐科舉的意義是非凡的,促進了學風向好,人才輩出,激發(fā)士人積極性,特別是對于館閣文風的成熟尤為重要,沒有恢復科舉的話,元代館閣文風的成熟尚需時日。
三、科舉與吏
元初科舉廢除,下層士人郁悶,欲仕無門,士人生存面臨嚴重的危機,使讀書人對讀書失去了吸引力,底層士人士風大沮,“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zhí)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14](p.2017)
此時文人要想入仕,十之八九需以吏進,自古以來讀書人就有高貴的理想,追求完美的人格,“學而優(yōu)則仕”帶有強烈的功利性,那種“金榜題名時”的自豪感和優(yōu)越感使得士人鄙視小吏,“師道尊,吏人役也。由師道視人役,可不較而明……而寧以儒進。”[29](p.424)文人鄙視吏,主要是傳統(tǒng)觀念,“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讀書人的優(yōu)越感在作祟,在他們眼里,儒與吏不是平起平坐的,儒吏兩途,儒優(yōu)于吏,他們看中的是學官,而不是執(zhí)行仆役的走徒。唐宋以來,士人不以進士入仕以為不美,“然唐之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不以為美。迄宋之盛,尤加重焉。”[30](p.460)“為士而由進士發(fā)身,天下之清流也。”[31](p.128)
“唐宋以科策取士,有不由科第出者,則共嗤鄙之。”[3](p.453)士人自唐宋以來視進士為正途,具有無可替代性,元人對吏的態(tài)度于此不無關系。在當時文人心中為吏是不幸的事,儒與吏界限分明,“石塘先生以前代儒宗……蓋有守有為,不幸為吏也。”[5](p.216)“暨圣元肇興混一區(qū)夏,廢而不設,然儒者進取之階率多循資而進,雖有茂才之科,多為有力者之所鉤致。故懷才抱藝之士老死衡門不得以盡其志。”[32](p.412)可見元初科廢對士人的打擊之大。
在宋代地位很高的文人因元初科廢,而一落千丈,他們內心產(chǎn)生了巨大的反差,儒士的優(yōu)越感遭到了狠狠的撞擊,士風沮喪,連小吏都瞧不上讀書人。“然而,小夫賤吏亦皆以儒為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旦往侯于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為也……夫以士之賢無所遇而淹于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33](pp.133-134)。由此可見,當時士風極壞,文人心情抑郁,對整個元初大環(huán)境的學風與文風是極為不利的,館閣文風也難逃一劫,沒有優(yōu)良的學風做基礎,何談館閣文風的形成。
這些下層文人必須面對生存的窘境,為了養(yǎng)家糊口,部分文人屈服于現(xiàn)實去從事自己鄙視的賤吏,一來可以解決生存問題,二來靠積年累月可以混個一官半職,畢竟讀書人的終極目的就是官本位的,這是儒家思想中的一部分。“當元盛時取士之途甚狹,士大夫不由科舉,惟從吏而已,積月累時,求一身榮耳。”[34](p.327)“我國家初定中土,取士之制未遑,仕者悉皆吏進。”[22](p.351)士人仕途狹窄,吏進成為最主要的入仕方式,不過通過吏進也比較艱難,需要靠長時間等待,小吏入仕是主流,“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為未也,再下令后是增多至百有二十月。”[35](p.379)剛開始吏必須經(jīng)過90個月才可以入品,后來改為120個月,10年時間始入品,相當不容易,“胥吏輩自執(zhí)役幾轉而得祿,少不下二十年始出官。”[36](p.227)文人心態(tài)可想而知。被迫從吏“時科舉已廢,士舍其所業(yè)而就吏役者,吾見亦多矣。”[37](p.58)“貢舉未行時,士之欲隨世就功名者倀倀靡戾,不得不折而歸于在官之府吏。”[38](p.428)這都是科舉廢除帶來的一系列影響。為吏者內心很悲哀,“仕者循資格,累歲月,青年委質,白首下僚者,蓋多有之,幸門不開,請纓無路。”[37](p.94)導致士風頹敗。
元代隱逸成風與科舉不開有密切的關系。“至于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yōu)。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則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于并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敝,一至于此!”[39](pp.216-217)優(yōu)秀的文人隱沒山林,而吏進入仕阻礙了館閣文風的形成。“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yè),志則郁矣,酤酒載嚴,詩禍叵測,何以紓其愁乎?”[40](pp.77-78)而元初儒與吏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儒士無任何優(yōu)勢而言,這就是元初底層文人生活的危機。元代科舉不開,吏擠占了儒應該有的位置,儒當吏用,儒與吏處于同一位置,儒根本沒有優(yōu)勢而言,儒喪失了應有的地位,儒士心態(tài)可想而知。
儒士的憤懣就是受蒙元舊習俗壓迫的表征。元吏要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才可出仕,即使出仕也是很可悲的事情。這與唐宋科舉入仕的文人的積極性形成鮮明對比。元開科前士風低落到低谷,雖有大一統(tǒng)的盛世雄心,那是館閣高層文人的心態(tài),底層文人整體處于以吏仕進的痛苦選擇中,他們鄙視吏。儒把學放在首位,“學而優(yōu)則仕,仕而優(yōu)則學”,仕與學互為條件。要出仕必須要學,學的目的就是為了仕,所謂幼而學,壯而行就是這個道理。元代吏員仕而不學,皆為俗吏,刀筆之徒,敗壞士風,影響社會穩(wěn)定。儒學而無用,仕途無門,這就是元初社會現(xiàn)實。儒與吏的矛盾很深。“成宗皇帝數(shù)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 [41](p.384) ,直至仁宗恢復科舉,才標志著儒士地位高于吏員,有了一個徹底的變化。這也是一直以來儒士的夢想,所以,科舉恢復時文人奔走相告,喜上眉梢。這標志著元朝統(tǒng)治階級有了一個徹底的變化,經(jīng)歷了太久,實屬不易。
“仁宗皇帝勵精圖治,痛懲其弊而一新之。由吏出身者,限以從七,不使秩高權重,得以縱恣。設立科舉,取人以德行為首,試藝以經(jīng)數(shù)為先,求賢之方,視古無愧。但科舉未行之時,以吏取人,實學之士,亦未免由此而進,一概限之,不無同滯……但科舉未行之前,儒皆為吏。其貪虐鄙俚之徒,限之固宜,而廉慎儒雅之才,恐遂倂棄。”[12](p.42)仁宗皇帝恢復科舉的目的很明確,主要是因為他看到了吏進弊端極大,他們貪財卑鄙,縱恣驕奢,所以,下定決心開科舉,選用儒士,限制吏員最高做到從七品。延祐開科后,仕進方式改變,儒士地位提高,儒優(yōu)于吏。士人眼里儒比吏貴,地位不是平等的,可元代初期社會現(xiàn)實是儒須以吏進,有些士人迫于現(xiàn)實壓力,不得不選擇自己鄙視的吏,這是一種無奈,對于士風與文風是沒有好處的,“千里以入仕由刀筆自愧,則惑之甚矣!”[2](p.484)“但科舉未行之前,儒皆為吏。”[12](p.42)延祐科舉對于改變士人入仕途徑意義重大。再也不用以吏入仕了。
元初科舉未開,入仕多途,元初任官職的途徑很不正規(guī),根本不能保證官員的基本素質,這也是造成元代短命的原因之一,吏進的官員腐敗嚴重,文化素質不高,辦事有失公平,民憤較多。由此可見,延祐科舉解決了眾多的問題,意義重大。
四、科舉興廢與文人心態(tài)
延祐開科對廣大士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如清人顧嗣立所說:“自科舉之興,諸部弟子,類多感勵奮發(fā),以讀書稽古為事。”[42](p.1729) 科舉的恢復意味著儒士地位的提高,有了入仕的門路,不用再屈膝為吏,學有所用對于廣大儒士來說是頭等大事。李孟作為延祐首科知貢舉,其《初科知貢舉》詩云:“百年場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京師。豹管敢窺天下士,龍頭誰占日邊名。寬容極口論時事,衣被終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頭應不負平生。”[43](p.199)南宋遺老趙文,延祐二年開科時,以75歲高齡參加了科舉,“猶攘臂環(huán)盱,不自謂老矣。然終不得以死,死時年七十有七矣。”[44](p.527)
“學而優(yōu)則仕”的儒家理想又一次回歸,士人歡欣鼓舞,對仁宗心存感激,仁宗也為文人津津樂道,成為心目中的神君,“而朝廷設進士科以取士,文風大興,人謂神君實主之。”[15](p.488)讀書人以“金榜題名”為人生之美,元初科舉的廢除,堵死了讀書人的晉身和生存之路。很多文人一輩子盼望開科舉,科舉就是他們的生命,但是,很多儒生一輩子也沒有遇見開科舉的到來,留下了終身的遺憾,甚至死不瞑目。“故吾之少也,慨焉思自奮于科目,而場屋事遽廢。逮國朝,復以科目取天下士,而吾老矣。”[21](p.311)“世遷科舉事廢,公乃以軍謀仕,時平無事,不得究所蘊,今科舉復,則已老矣,其命也!”[45](p.363)所以,延祐科舉對“新生代”有著非常深刻的意義。
“科未興時,各棄學歸利……以俊民甫之才之美,而生不偶,年壯而科舉廢,科復而身已老。”[38](p.568)“國朝延祐初科復而君老矣。”[38](p.580)士人以入仕為榮,科廢對他們來說猶如人生道路大塌方,心情極為沮喪。“既而學益昌,恨不見科舉。”[25](p.111)“以吾初有志功名,恨不在科舉時,死數(shù)月而科舉興,窮達雖有命,亦可哀矣。”[25](p.114) 這些文人的科舉夢一輩子也沒有實現(xiàn),機遇對于每一位士人來說都極為重要,沒有機遇,他們的心等于死亡了,所以,延祐科舉拯救了“新生代”文人的科舉夢,同時也避免了他們重復老一代文士留下了遺憾,意義不同尋常。
“建叔好尚文雅,少習進士詩賦,藝成而科廢。”[38](p.470) “諱應桂……最后與今翰林承旨程鉅夫同門。業(yè)成而科廢。”[38](p.532)“少習舉子業(yè),藝成而科廢。”[38](p.660)文士是因為科舉的廢除,導致自己辛辛苦苦研習的舉子業(yè)才華,荒廢無所用世,造成他們心情郁悶痛苦,嚴重影響了當時的士風和文風。“未三十,宋亡。然科廢,猶三十年不廢程文……科廢恨早,科興恨老。”[8](p.629)科舉是讀書人的生命,在他們心中的位置無可替代,所以,元初科廢,對于文人是個毀滅性的打擊。元初科舉的廢除,士文人心情沮喪到極點,人們被迫放棄熱愛的舉業(yè),以各種方式存在著。從事其他行業(yè),以滿足生存的需要。人們對科舉廢除一事的態(tài)度千差萬別。有些儒士失去科舉機遇后從事佛學,“國初,科舉廢,世族子弟,孤潔秀拔,率從釋老游。”[46](p.490)“宋亡科廢,不獲試。晚好佛老書。”[38](p.616)有些儒士科廢后致力于理學研究,“至宋亡,科舉廢,乃更沉潛性命之學。”[9](p.716)有些士人終身不改儒服,以此表達對自己的尊重,以不改儒家衣冠表白自己的身份,“貢舉既廢,巍冠侈袂終其身。”[38](p.432)有些儒士科廢后不肯從事吏,仍艱難地安慰自己,在儒士生存都成問題的年代,仍然以儒者身份從事教諭,“時代更,貢舉廢,君負長伎,自好不厭,鄉(xiāng)里競延致教弟子。”[38](p.483)有些書生科廢后大力寫詩,“進士科既廢,乃肆其力于詩。”[38](p.534)禾川顏省原,早有志于學,習《詩經(jīng)》為舉子業(yè),廩廩有嚮進意,不幸遭世亂離,科目廢,無以展其業(yè),遂折入聲韻,以吟詠其情性,而發(fā)抒其英華。”[47](p.428)有些儒士隱居山林,“君諱泰來,字大可,世居撫之臨川……延祐初,科目法行,君即以《春秋》授。一再試有司不偶,乃嘆曰:命也。遂退隱,不求聞達。”[37](p.491)有些士人徹底放棄了仕進的理想,“進士科既廢,無復仕進想。”[38](p.527)
然而,有些文人在科舉廢除看不到復興的情況下,依然堅持研習科舉業(yè),教子孫不要放棄科舉,并預言科舉某一天一定會恢復,“科廢四十年,教子若孫勿棄舊學。”[38](p.455) “其后藝精而科廢,每戒諸少,謂:文事它日必興,勿以不為時用而荒棄所業(yè)。”[38](p.581)這些士人的行為引起當時很多人的不理解,以為他們過于迂腐,延祐科舉的復興,證明了這些文人的預見性。
“宋末科舉之學甚盛,國亡科罷,而業(yè)之者亦廢……皇慶延祐,儒科復。于時舊學者已忘其步武,新學者未得其門庭,而君獨擅所長……君之先識定見莫不嘆服焉。”[38](p.594)“貢舉已廢,君教子明經(jīng)不輟,或笑其迂。及儒科復,而君之子孫克副時需,始服君遠識。”[38](p.606)延祐科復,人們又佩服這些儒生見識長遠,眼光獨特。“宋祚迄,儒科廢,猶以舊舉子業(yè)訓子。逮延祐復行取士制,子若孫皆能試藝,若前知然。”[38](p.640)科舉家族的巨大影響力,勤奮好學的家風營造了良好的學風,家族早在宋代就研習科舉,視科舉為儒士正途,對科舉有著極其特殊的感情,所以,元初科廢,也沒有阻擋他們研習科舉的腳步。 “君諱會,字伯會,姓汪氏,徽之婺源苻村里人,世業(yè)儒……是時國家定江南未久,士失其業(yè),而君家故貧……方科舉之未行也,學者以辭章相尚……及科舉行,始欲奮筆以取功名。”[48](p.477)科舉對士人一直存在著巨大的吸引力。“科舉興,教二孫以取應。”[38](p.619)
堅持的原因是出于對科舉的熱愛和執(zhí)著,使部分文人等到了科舉的恢復,即使已經(jīng)身老,但給子孫后代打下了科舉入仕的堅實基礎。“當宋亡科廢,教子孫不廢學,故科興而子孫世科亦不絕,于是世為通家。”[8](p.634)“潁川陳貴道,篤意科舉之學,人皆以為迂。及延祐科興,士茫然無知規(guī)矩之所在,貴道獨擅倕班之手,人又皆以為有先見之識。”[25](p.212)“宋亡科廢,猶有季門從學之人,貢舉既行,其徒浸盛。”[49](p.392)一種對科舉的特殊情感,使他們堅持在前途暗淡的年代繼續(xù)研習科舉,他們完全拋棄功利觀念,把研習科舉作為一種精神寄托,一種對儒家情懷的特殊表達,是延祐科舉的恢復成全了這部分執(zhí)著的文人,圓了他們的科舉夢,延祐科舉的意義之重大,由此可窺一斑。
有些人生在延祐科舉之時,可惜因病早逝,以未能參加科舉取得功名,留下終身遺憾。“十歲聞科舉行,即大喜,忘晝夜,廢寢食蒐獵經(jīng)史,旁入捷出,務為無所不知。聞有學出己上,便往與交,聞有大人先生,便往質其所疑……嘔血死,將死嘆曰:吾生不在科舉后,沒不在科舉前,命也。”[11](p.544)
科舉的恢復對文人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余友林君子章,世家子也。林優(yōu)而學敏,科舉復興,遂刻志絕去家務,將攜其季子文負笈尋師,志則遠矣。”[29](p.206)及時去拜師學習有關科舉考試的內容和方法,以期進入仕途。“初,延祐甲寅科興,一時海內之士,爭自濯磨以效用。”[29](p.760)“國家始開科舉,出其門者鼓篋場屋將數(shù)十人。”[41](p.605)他們期于用世的心里是極其強烈的,可惜時不我待,封建時代文人博取功名最有效的途徑就是科舉入仕,科舉的廢除等于把他們推向了死亡的邊緣。朝夕盼望科舉的恢復,有些文人盼了一輩子,最終也沒有等到科舉恢復的日子。所以,延祐科舉的恢復,雖然取士人數(shù)不能和歷代相比,但意義非同尋常。
人數(shù)眾多的漢人與蒙古色目人均等名額,漢人落榜人數(shù)之多可想而知,自延祐二年(1315年)取士至元亡,共16科,得進士不過1 200人,而考生人數(shù)遠遠多于此數(shù)倍。元代科舉歧視南人,存在不公正現(xiàn)象。“考官得新安王伯恂之卷,驚且喜曰:此天下奇才也,宜置第一……同列有謂:王君南人,不宜居第一。欲屈置第二,且虛第二名以待。考者曰:吾儕較藝,以文第其高下,豈分南北耶!欲屈置第二,寧棄不取耳。爭論累日,終無定見。揭曉期迫,主文乃取他卷以足之,王君竟不在取。”[16](p.317)有的文人長期科舉一直不中如王冕、吳萊、李存、周霆震等,有的文人沒開科舉前一直沒機會,后來開科舉才中進士如楊載,或者一直不中,以及多次參加才獲得進士如薩都剌。
士子地位居四民之首,不肯屈居下僚,延祐科舉對文人心態(tài)影響是必然的事,科舉順利的人對延祐科舉持肯定態(tài)度,熱烈歌頌科舉恢復,如歐陽玄、許有壬對延祐科舉表示了熱烈的贊美和由衷的肯定,對仁宗詔頒科舉懷感恩之情,而下第文人心情恰恰相反。元代廢除科舉后,薩都剌這樣滿腹經(jīng)綸的,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無法步入仕途,家里窮困,人口眾多,為了生存開始學習經(jīng)商,結果窮困潦倒,連買酒的錢都沒有了。延祐元年(1313年)下詔恢復科舉后,薩都剌看到了久違的希望,于泰定四年(1327年)以三甲進士及第,此時終于實現(xiàn)了“宮花壓帽金牌重”的壯志,又有對君王的感激心理,“小臣涓滴皆君賜”。《醉歌行》頗能反映薩都剌的心態(tài):
“曹生金谷韓信餓,古人不獨詩人窮。今朝有酒且共醉,明日一飲由天公。紅樓弟子年二十,飲酒食肉書不識。嗟余識字事轉多,家口相煎百憂集。乃知聰明能誤身,不知愚魯全天真。百年簡憲曾何畏,一日禮法能殺人。賢愚千載同一朽,我為君歌君拍手。流芳前行遣興不必論,且盡尊前一壺酒。”
此詩寫于未開科舉前,作者被迫經(jīng)商謀生,此時詩人社會地位極其低下,生存十分艱難。反映了讀書人士去仕進機會以后的悲慘境遇。全詩充滿了對社會的憤怒,韓信當年在楚漢戰(zhàn)爭中立了大功,被封為淮陰侯,卻不懂經(jīng)商之術,經(jīng)常挨餓,詩人以韓信自比,英雄沒有用武之地的無奈與悲憤。對科舉不開無仕進機會表示不滿。“簡憲”指朝廷頒布的法令,“一日禮法能殺人”指元代廢除科舉使士子失去進身機會,對統(tǒng)治階級的憎恨之情,“紅樓弟子年二十,飲酒食肉書不識。嗟余識字事轉多,家口相煎百憂集”,對比富人不識字卻衣食無憂,自己滿腹才華卻百口相煎,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這首詩寫出了科舉堵塞對讀書人的影響之大,詩人深刻感受到社會的不公平,仕途絕跡,科舉不開士子們悲慘的生活境遇,內心極度痛苦,表達了郁悶悲慘的心情。
薩都剌《述懷》:“客身去住與心違,誤執(zhí)漁竿下釣磯。好客不來門戶俗,老親相別信音稀。青春背我堂堂去,黃葉無情片片飛。遙望家山搔短發(fā),故園酒熟蟹螯肥。”此詩寫于未開科舉前,為了生存放棄書本去經(jīng)商時的心境。是元代科舉對文人心態(tài)影響的真實反映,理想不能實現(xiàn),仕途淹蹇而青春平庸、碌碌無為的失落感,寫出了遠離家鄉(xiāng)漂泊在外的心境。《題黃贊府齋中十詠》寄托了對有用之才不為當局所用的悲憤心情,《焦桐》一首中“中官方煮鶴,終得舍夫君”,指統(tǒng)治者不識人才、扼殺人才。“材高初偶得,昔古更誰聞?天海空遺操,冰霜見裂紋。”比喻手法形象地表達了英雄無用武之地,當局埋沒人才,表達了不開科舉壓抑悲憤的心情。由此可見延祐科舉對士子的心態(tài)有著多么深刻的影響,讀書人追求功名、要求改變地位,一旦科舉廢除對他們影響是巨大的。
元代李存也是科舉不暢的代表,“好為古文辭,通醫(yī)術。既而游于上饒陳立大之門。延祐開科,一試不第,即決計隱居。三以高蹈丘園薦,不應,秘書李孝光舉以自代,當事者將以翰苑處之,不果。”[42](p.1666)李存作為延祐科舉下第詩人,追求功名受阻,反映到他的詩文創(chuàng)作里,可見當年科舉競爭之激烈。《下第南歸別俞伯貞》:“驅車出都門,別酒忽在手。去國古所悲,況復失良友。芃芃丘中麥,郁郁道旁柳。揮手從此辭,煙云黯回首。”此詩寫出了李存科舉落榜后失望難過的心情,“煙云黯回首”科舉下第對前途一片渺茫,悵惘感縈繞心頭,可見延祐科舉對廣大士人的重要意義。
周霆震也是元代落第文人的代表,“科舉行,再試不利,乃杜門授經(jīng),專意古文辭,尤為申齋,桂隱二君所識賞。”[42](p.2174)周霆震下第客觀上造就了他的古文辭成就,也是科舉對他的影響。
由上可見,延祐科舉的恢復對熱衷于功名的文人心態(tài)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雖然取士不多,數(shù)量不能和歷代相比,但人才之盛,質量之高是不爭的事實,對元代中后期文學社會各方面都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延祐科舉的意義是深遠的,影響是巨大的,在元代文學文化史上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參 考 文 獻]
[1]萬斯同.宋季忠義錄 [A].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叢刊:29冊[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2]李修生主編.全元文:25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3]李修生主編.全元文:17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4]李修生主編.全元文:12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5]李修生主編.全元文:51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6]李修生主編.全元文:50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7]李修生主編.全元文:11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8]李修生主編.全元文:21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9]李修生主編.全元文:34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10]李修生主編.全元文:23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11]李修生主編.全元文:28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12]李修生主編.全元文:38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13]李修生主編.全元文:29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14]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5]李修生主編.全元文:26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16]李修生主編.全元文:46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17]程鉅夫.雪樓集[A].文淵閣四庫全書1202冊[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8]許衡.魯齋遺書[A].文淵閣四庫全書1198冊[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9]蘇天爵.滋溪文稿[M].北京:中華書局1997.
[20]李修生主編.全元文:39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21]李修生主編.全元文:30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22]李修生主編.全元文:40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23]揭徯斯.揭溪斯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4]歐陽玄.圭齋文集[A].文淵閣四庫全書1210冊 [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25]李修生主編.全元文:22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26]李修生主編.全元文:32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27]紀昀總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8]鄧紹基.元代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29]李修生主編.全元文:60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30]李修生主編.全元文:43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31]李修生主編.全元文:47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32]朱晞顏.瓢泉吟稿·卷四·送張信甫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1213冊[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33]李修生主編.全元文:49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34]李修生主編.全元文:59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35]李修生主編.全元文:9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36]許有壬.至正集(卷三二)送馮照磨序[A]. 文淵閣四庫全書1211冊[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37]李修生主編.全元文:48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38]李修生主編.全元文:15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39]李修生主編.全元文:55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40]李修生主編.全元文:56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41]李修生主編.全元文:27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42]顧嗣立.元詩選·初集·泰不華小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7.
[43]顧嗣立.元詩選(二集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7.
[44]李修生主編.全元文:16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45]程端學.積齋集·卷五·元故從仕郎杭州路稅課提舉杜君墓志銘 [A].文淵閣四庫全書1212冊[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46]李修生主編全元文:33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47]李修生主編全元文:45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48]李修生主編全元文:31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49]李修生主編全元文:14冊[Z].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作者系中山大學講師,歷文學博士)
[責任編輯 張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