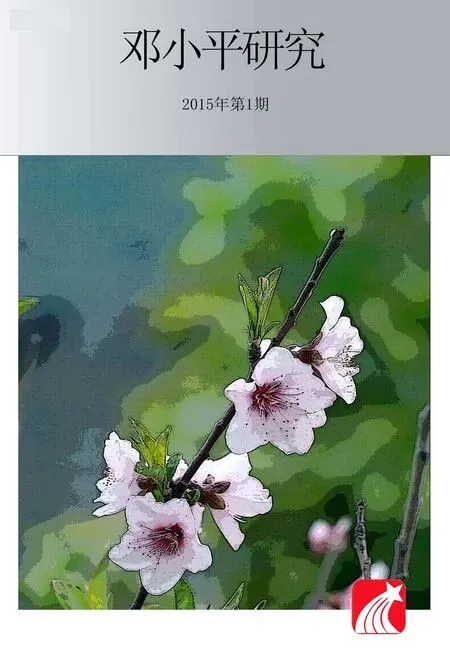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變お
吳子牛??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全景式展現了1976~1984年間,曾經歷政治上“三落三起”的鄧小平帶領黨和人民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沖破重重阻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刻畫了以鄧小平、葉劍英、陳云、李先念等為代表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帶領國家結束十年動亂、實行改革開放、走向民族復興的壯舉。
作為一名導演,很榮幸能參與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的創作,因為自己親身經歷了這個時代。我曾是一名初67級的中學生,經歷了全程“文化大革命”,1969年1月17日,作為全國首批插隊落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76年北京天安門的“四五運動”波及整個中國,我在四川也間接地參加了這場運動。恢復高考后,我于1978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成為了一名“新時代”的大學生。《歷史轉中的鄧小平》這部大劇描繪的1976~1984年正是這個令人難忘的、驚心動魄、波瀾壯闊、可歌可泣、可喜可賀的“新時代”,它不僅是中國的“新時代”——“鄧小平時代”,也是中國人民的“新時代”——改變了中國命運,改變了中國人民命運的時代!我為能夠將這一段恢弘壯麗的歷史搬上熒幕而激動,因為它不僅是一段歷史或故事,也是一份我們這代人對于這個時代深刻的情感記憶,也可以說是我們的致青春。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了我,觸動了我,甚至是撞擊了我,時至今日,中國改革開放的每一個腳步,每一次跨越,時代的呼吸,人民的心跳,都歷歷在目,聲聲回響。我希望把這些記憶,這些情感,把那個時代的愛與恨,喜和樂,傷痛和眼淚,細語與呼喊統統與我們這部電視劇要描繪的時代與變革融為一體,同步交響。
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歷史題材”,而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現改革開放,是一部“當代人寫當代史”的深刻的現實主義作品,是一部史詩般的鴻篇巨制。和所有的“重大題材”一樣,它具備很強的政治性,政策性……但我同時也認為:這一次,和以往“重大題材”不一樣的是一定要有鮮活的人物,動人的故事以及深刻的思想和感情。我要求自己盡可能,調動一切可用的藝術手段,盡全力拍成一部具有相當震撼力以及藝術感染力極強的影視作品。
長期以來,在我國“重大題材”、“紅色題材”的影視創作中,甚至在其他藝術形式的創作中,都已被“仰視”,“文獻片”或“紀錄片”式的直奔主題被格式化了,很多作品基本都是大同小異,千篇一律。細細分析,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這里面也不乏“樣板戲”的一些余毒。必須指出這是我們今天創作《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的第一個障礙。一部文藝作品如果沒有受眾的思考和感情介入,創作者與受眾如果沒有交流,沒有互動,那么,這部作品就一定會失敗。因此,我們必須打破這種舊有的格局,努力尋求人物塑造,思想意義的表達與敘事手法和角度的匹配,尋求風格樣式服務于人物與思想等等方面的突破和創新。 我在1984年寫過一篇文章,是我第二部電影《喋血黑谷》的藝術總結,文章叫做“在失重中尋找平衡”。那篇文章在《當代電影》、《電影通訊》、《北京電影學院學報》刊登。那部片子是個驚險樣式。作為一名電影學院剛剛畢業的充滿理想、激情的導演,突然接到廠里的任務要我拍一部驚險樣式的電影,你怎么去處理它,怎么拍得和別人不一樣。實際上,這次我遇到的情況跟三十年前是一模一樣的,要拍這樣一部“高大上”的主旋律電視劇,并且是這么宏大的國家題材。怎樣才能讓它好看,讓觀眾喜歡,引起大家共鳴,這些都是擺在我面前的課題,通過思考,我認為在創作中,要尋求多種風格樣式的綜合,尋求各種流派的整合。這樣才能夠把藝術創作的各種元素圓潤有機地綜合在一起,千方百計讓這部電視劇生動、好看、深刻,抓人、吸引人、感染人。這部電視劇是一部正劇,通過對小平同志的刻畫,對國家和人民命運的描繪,為國家形象服務,為改革開放和時代服務,為中國的未來服務。如果這部電視劇沒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曲折動人的情節,細膩飽滿的感情,深刻的思想,波瀾壯闊的時代印象,鮮活豐滿的人物形象,那我們藝術上的一切追求都要泡湯。所以,在這部電視劇的敘述上,結構上,樣式上,凡是對這部電視劇有利的藝術元素都要用上,比如驚險樣式:第一集就非常驚險刺激,粉碎“四人幫”之夜,一定要讓觀眾看得喘不過氣。充分運用驚險樣式的手段,各種創作元素的渲染中和,比如風雨雷電的渲染,短促快捷的多角度多景別鏡頭運用,犀利的場面調度設計,這些都是驚險片的風格。當然,這部劇也有很多溫暖寫意的愛情戲的段落,如:小平同志全家搬家那場戲,當他看到自己和家人如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使他回憶起革命年代他和卓琳在延安相知相識的感人情景,這些都濃濃地表現出他對卓琳的愛,對孩子、孫子們的愛,這都是典型文藝愛情片的風格。電視劇里還有喜劇和悲劇的元素,如:田志遠和曹慧,他們倆的感情和命運就具有悲喜劇色彩,一開始就是悲劇,兩口子由于政見不合離了婚,但彼此又痛苦和糾結地愛著對方,跟那個時代的苦難是同步的。后來隨著劇情的深入,就出現“白頭翁”、“田源他哥”、“曹慧燙大波浪頭”等具有喜劇元素的橋段,一直到他們幸福的復婚等等。這些處理都是本部電視劇所需要的多種元素綜合和不同風格流派的整合。
這一切手段和方法作用于這部劇的創作,是為了讓它更吸引人,更感動人,更有力,更震撼,這么做的目的,亦是為塑造小平同志服務。塑造好小平同志是本劇創作的一大課題,我堅持一點:“讓雕塑活起來”,讓偉大人物走下神壇,真實,生動,自然地生活和穿行在每一段歷史篇章中,貼近人民,融入生活,與此同時,作為創作者或是作為觀眾都盡可能地相信我們精心營造的時代氛圍,歷史環境,使小平同志能得以和我們一道,或是我們以及觀眾能得以和小平同志一道,盡可能真實地生活在那個時代,那段歷史中。我們在敘事角度上、在表現手法上、在戲劇結構上、在鏡頭運用上、在語言環境中……讓我們代表觀眾的視角,千方百計地貼近小平同志,與他老人家“零距離”地接觸,在劇中很多場合,很多事件中,體察他的喜怒哀樂,聆聽他的心跳,體會他的愛與恨,體察他的感情……當我們以及觀眾與他心心相印時,當我們因為劇中的事件,國家與人民的命運而共同呼吸時,我們便能摸到時代的脈搏,身臨其境,與小平同志一道憤怒,一道感動,一道激動……這是我們去追求的效應和結果。一個舉重若輕、深思熟慮、一言九鼎、大氣磅礴的國家領導人,同時也是一個慈祥幽默、充滿大愛的平凡老人。在“解放知識分子”、“恢復高考”、“兩個估計”、“兩個凡是”、“中美建交”、“中英談判”、“深圳特區”等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他愛憎分明,堅決果斷,毫不留情;但對普通百姓,民間疾苦,卻有著“悲天憫人”的情懷;在家里,對妻子和孩子們卻是一個樸實平常的丈夫和父親,真實可愛,偉大又平凡。因此,我們要千方百計讓小平同志走出神話,破除迷信,讓小平同志在熒幕上真正生動和鮮活起來,永遠活在人民心底里。
作為導演,對于本片的創作傾入了很多感情,我全程經歷了那個時代。比如高考,劇中人物田源的經歷和我表哥的情況是相似的,1977年高考因為家庭出身問題沒有錄取,1978年再次高考,成為地區的文科狀元,但仍未進入他心儀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最終被勉強錄取到西南師范大學。我和劇中的夏建國收到錄取通知書的情景也很相似,打開通知書那一刻他在陜北塬上奔跑吶喊,我在四川的江邊上一個猛子扎進江中讓自己冷卻下來,這種情感的記憶是非常強烈的。小平同志的出場是端著一盆熱水給高位截癱的大兒子擦背作為影片的開始,這種處理是對十年“文化大革命”強烈的控訴。在這“十年”當中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國家干部、知識分子、普通的老百姓均受到迫害,還有很多人被奪走了生命。這是歷史的事實,誰都抹殺不了。當時小平同志本人的處境和他大兒子在“文革”時的遭遇,觀眾是非常熟悉的。為什么我一定堅持要把這場戲放在電視劇的第一場,把小平同志“放在”胡同里一個平凡老頭的角度;是一個家庭里普通的父親,正在悉心照顧自己傷殘的兒子……這絕對不是煽情,而是控訴。“文化大革命”時期我的父母也受到了沖擊,我姐姐因此生了病。小平同志給兒子擦背的情景,跟我父母照顧我姐姐的情況是一樣的。小平同志和當時千千萬萬的受害者一樣要去面對和照顧自己的孩子。這些情節具有強烈的帶入感,因為它是當時無數普通老百姓家里真實發生和存在的。所以他的出場如果沒有對這種苦難時代強烈的控訴,就不可能有全面撥亂反正,更不可能有改革開放。這些場面都是我刻意想要表現的,也必須要這么去處理。由這些創作理念呈現出的場景和段落在這部電視劇里比比皆是。比如,小平同志與參加全國科教座談會那些受盡迫害的知識分子們,比如,小平同志去廣東農村時那“三只鴨子”的故事……
創作這部電視劇我一直心系一個原則:必須把握好一對辯證關系,即:再現與表現,這是藝術美學問題,也是創作哲學問題,更是《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這部劇必須去研究的完美結合和統一的創作需要。所謂再現,就是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歷史原貌,盡可能準確地還原1976~1984年的時代氣氛和歷史變革的時代環境變遷,它體現在畫面中所有的影像元素中,大到建筑,小到化、服、道、時代的音響、環境的聲音……以及衣飾的細節,陳設道具的考證,哪怕是一張紙、一支筆、一枚郵票、不勝枚舉!通過我們的制作讓今天觀眾看到那個時代中國面貌的變化,人民的生活變化和人物命運的起伏。“表現”就是要把人民的恩愛情仇,人民的思想,通過再現的基礎去表現出來。這是觀眾對時代的情緒記憶,要喚起50后、60后、70后對那個時代的回憶,需要很多藝術手段來表現,我運用了20多首時代歌曲,作為背景聲音處理,這些歌曲全是那個時代情緒和感情的記憶,比如:《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人民公社社員之歌》、《大慶石油工人之歌》,劇中人物拉手風琴唱的三套車和很多蘇俄歌曲,朝鮮電影《賣花姑娘》,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插曲,包括劇中后面出現的羅文、羅大佑、鄧麗君、包括彭麗媛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讓觀眾看著那個時代慢慢地漸變,慢慢地浮出亮色。產生我們特定場次戲劇要求的環境氣氛,和人物塑造必須的物質氣氛。“一部沒有氣氛的電視劇,如同一盤沒有放鹽的菜,寡然無味”。可見氣氛的營造是多么重要,但這僅僅是基礎,僅僅是我們為表現小平同志,表現時代,表現各種大大小小的事件,表現各種情感和各種思想的需要,前者是為后者服務的,再現是為表現服務的,“唯能立意,方能造景”。從一開篇就要把觀眾帶入1976年10月的那個夜晚,只有真實地再現那段歷史,才有可能讓我們的故事生動,精彩地講敘下去,并最大限度地吸引觀眾,震撼觀眾的心靈,才能生動地表現小平同志偉大的歷史功績和他卓越的貢獻。
這部電視劇還有一個重要的創作重點就是在寫好領袖人物的同時,一定要寫好時代,寫好人民,一定要寫他們的命運。如果不把人民的命運寫好,就寫不好時代的變化,寫不好時代,就寫不好小平同志的豐功偉績。他們彼此息息相關,不能分割。創作中所有的篇幅、比例、筆觸,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渾圓的主題來表現小平同志,也只有這樣才能把這個戲拍得好看、扎實、深刻、有思想。
一部好劇的誕生,除了一個好的創作集體、好的故事之外,應該還有一個強大的制作團隊,這個制作團隊包括制片團隊、有創作誠意的投資方和創作人員一起共同去完成一個使命。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一心一意、同心同德以赤誠感人,全組上下思想感情、創作態度,對國家的感情、對民族的感情、對老百姓的感情都是真摯的,充滿激情的。只有這樣,這部片子才能打動人,我想我們這部電視劇做到了這一點,在這里我要表示真摯的感謝。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是一部中國的主旋律影視作品。在這部作品中,我們努力突出中國人民的家國情懷和對祖國的深情大愛,以及在風起云涌的時代中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道路的強大精神力量。八年的歲月,是歷經艱難,偉大光榮的改革伊始。在鄧小平和無數鮮活生動的人民身上,看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大轉折。改革開放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次新的革命。這部戲按媒體的話來說是大國大劇。如何講好國家的故事,如何讓更多的觀眾喜愛這部劇,關注國家的命運,需要我們打破過去主旋律作品單一的講述形式,打破文獻式的、紀錄片式的、雕像式的套路。在藝術形式上需要進行各類藝術風格樣式的整合,進行各種藝術類型的綜合,調動一切可行的藝術手段為主題服務,使我們的故事變得更加精彩好看,更加動人,更有感情,更能與觀眾心心相印,產生互動,與劇中人一同流淚、歡笑、激動、思考……從而一道憧憬更加美好的明天,去追求更偉大的夢想。
(責任編輯 廖子夏 謝靜 王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