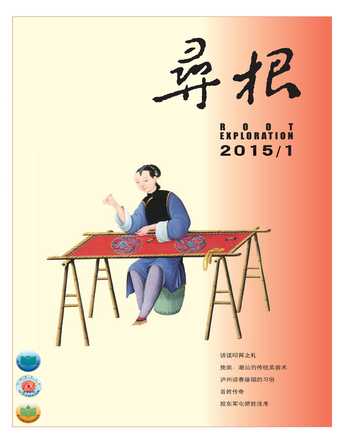兩宋茶文化流變初識
郭韻潔
茶興于唐而盛于宋,兩宋時期(960~1279年)在中國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靖康之難后,宋室南渡,兩宋之際中國歷史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同樣為眾所周知。然綜觀學界關于宋代茶文化的研究,絕大多數將北宋、南宋作為一個整體討論,或以北宋為主體展開,鮮有縱向探索其歷史嬗變者。那么,茶文化在北宋、南宋之間的流變軌跡究竟如何,有哪些沿襲與變革、傳承與創新,對于中國茶文化的歷史走向產生了什么影響,就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中心重合:產業中心與文化中心
夏、商、周三代以降,中國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始終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并沿著西安一洛陽一開封軸心緩緩向東移動;六朝以來,江南地區漸次開發,經濟重心已開始向東南微微傾斜;安史之亂以后,江南經濟已顯后來居上之勢;北宋江南文化也已與中原文化旗鼓相當;1127年的靖康之難,繁華的東京被洗劫一空,“中原人士扶攜南渡幾千萬人”,從而給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南移“以最后的推動”。接下來的南宋時期,政治中心移至臨安(今杭州),全國經濟重心完成了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歷史性轉移,傳統中國的經濟形態自此逐漸從自然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從內陸經濟轉向海陸型經濟,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發展進程中具有路標性意義的重大轉折。與此相應,自從東晉以后開始的全國文化中心南移的運動也得以完成,杭州蘇州南京構成的南北向文化軸心取代了長安洛陽開封東西向文化軸心。正如劉子健先生所說:“此后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為模式,以江浙一帶為重點,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文化。”
在中華文明空間轉換大勢之下觀照中國茶文化的歷史流變,我們也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啟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基于茶樹生長的環境要求,茶葉生產與飲茶風氣的中心是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廣大地區,也就是說茶產業的中心是在江南地區。而自中唐時代“茶道大行”,陸羽《茶經》“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器、命其煮”,開啟了中國茶業的文化之門,形成了以煎飲法為特征的中國茶文化史的第一個高峰。經五代至北宋,北苑建茶崛起,“龍團鳳餅,名冠天下”,“縉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浴膏澤,熏陶德化”,“采擇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盛造其極”(趙佶《大觀茶論》),形成了以點茶、分茶、斗茶為特征的中國茶文化史的第二個高峰,也可以稱為巔峰。兩次茶文化發展的中心區都不在江南的茶產業中心,而是在并不適宜茶葉生產的京師,也就是當時全國的文化中心區域,這種茶產業中心與文化中心的疏離狀態,是中國茶文化發展史上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這種現象的存在是封建中央集權統治的產物。首先是源于任土作貢的貢茶制度,上品佳茗皆貢獻朝廷,正所謂“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盧仝:《茶歌》),“……陵煙觸露不停探,官家赤印連帖催……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啖春山摧……”(李郢:《茶山貢焙歌》)。京師集中了全國最好的茶葉,唐元和十二年(817年)五月,內庫一次就拿出三十萬斤茶葉。北宋繼承南唐舊制,在北苑置官園官焙,設官專司向皇室貢茶之事,歲貢高達216000斤,其他“諸路貢新茶者凡三十余州,越數千里,有歲中再三至者”(《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九)。其次是高度集權下的行政運作的極致發揮,為京師積聚了廣泛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皇室的熱心倡導和身體力行、官府的大力推動、文人的極力闡揚、民眾的廣泛參與,使得宋茶的品質極度精致化,也大大提升了茶的文化形象,拓展了茶的文化內涵,拉動了茶的社會消費。也正因為如此,這種超經濟的力量也極大地消解了茶葉產業中心與文化中心相疏離的現象所帶來的負面作用或消極影響,成就了唐宋茶文化的輝煌。
當然,這種茶產業中心與文化中心長期疏離的狀態或現象,畢竟不符合茶葉經濟發展的規律,也不可避免地會給中國茶文化的歷史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因緣際會,南宋時期隨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的完成,臨安成了三位一體的茶業核心區。首先,“中朝人物悉會于行在”,“四方士民商賈輻輳”,促使杭州得以攜京師重地、經濟重心、文化紹興、茶產興盛多重優勢,成為茶文化復興的得天獨厚的中心區域。其次,延續北宋上層社會茶文化的廟堂風致的同時,適應商品經濟發展和市民文化興起的歷史潮流,推動了江南茶文化的士林風雅和民間風俗、廟堂風致與民間意趣的雅俗融合,是觀照南宋乃至此后中國茶文化發展的一條重要路徑。
雅俗交融:廟堂風致與民間意趣
關于宋代的文化特征,學術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宋詞、宋文、宋畫、宋代文玩以及宋代理學,構成了一個精致遼闊而又森嚴的貴族世界,而在這個世界之外,另有一種文化形態崛起,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人頭攢動的瓦舍勾欄中成長起來的野俗而生動的市民文化”(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這就關涉中國文化史上最為常見的一個命題——雅俗之辨,也就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思維結構,二者的關系并不局限于兩種文化、兩個階層之間的區分,重要的是二者之間更為復雜的互動和融合。中國茶文化的發展亦當作如是觀。
飲茶之興,自是源自民間生產生活;而提升為生活藝術、審美情趣和精神文化,則由于文士僧家的總結闡揚。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選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沿至北宋,以宮廷、士林為代表的茶之雅文化融合三教,兼通百藝,臻于極致,而以市民階層為代表的茶之俗文化也空前興起,顯示出勃勃生機。就前者而言,“天下之士,厲志清白,競為閑暇修索之玩”,北苑貢茶窮極精致,點茶、分茶、斗茶技藝出神入化,茶書編撰蔚然成風,茶與詩詞、書法、繪畫等藝術形式的有機結合,“試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雙蕊嚼黃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群豪競斗美”,“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成為“盛世之清尚”。就后者而言,商品經濟發展和打破坊市制度,市民階層的興起和市民文化的勃興,茶坊酒肆、瓦舍勾欄的繁榮,流動茶攤、茶擔的興起,以至“賓主設禮,非茶不交”,“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的客來敬茶習俗,居家飲茶和以茶睦鄰、茶入婚俗等,茶文化已經深入到了城鄉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民間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
如果說北宋茶的雅文化登峰造極而俗文化初見端倪的話,那么到了南宋時期,茶文化則經歷著此消彼長、從分野到融合的嬗變。南宋雖偏安江南,但其疆域仍基本包含了適宜栽茶生態區,加上茶馬貿易、榷場及走私貿易之需,茶葉生產持續增長,產量在1.65億~2億宋斤之間。北苑貢茶的制度、品名、規模雖仍沿襲北宋之舊,如熊克所謂“閱近所貢仍舊,其先后次序亦同,惟躋龍團勝雪于白茶之上,及無興國巖、小龍、小鳳”。但囿于客觀形勢,也不時加以裁減、蠲免,如高宗就曾罷北苑貢茶三分之一。孝宗以后,北苑貢茶可能裁損更甚,或雖有舊規,而多不敷額了。況且貢茶制作成本高昂、價值嚴重偏離、違背自然物性也影響了這種極端精致化的茶藝的持續發展和普及;社會的動蕩和人們心理焦灼也使得茶藝“慢慢從高貴的藝術殿堂降落,漸漸平凡化”.南宋茶書編撰的銳減就是一個明證。與此相反,以都城臨安為代表的城市商品經濟繁榮已遠遠超過北宋東京,“視京師其過十倍矣”,社會風氣好新慕異,奢靡相尚,民間茶文化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就其標志之一的茶坊而言,《東京夢華錄》雖記載有李四分茶坊、薛家分茶坊、從行裹角茶坊、山子茶坊、丁家素茶坊等,《清明上河圖》也展現了汴河兩岸的茶坊,但還是在敘述街道、展示街景時附帶提到,較之《夢粱錄》《都城紀勝》等文獻專設“茶肆”“茶坊”之目,不僅列名繁多,“處處各有茶坊”,而且分類更細,如茶樓教坊、行業“市頭”、“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以及娛樂場所之花茶坊、水茶坊、歌館、書場等,經營方式也靈活多樣。京師之外的其他城鄉,茶館的普及程度已遠遠超過了北宋。民間茶文化的普及也同時在不斷簡化著極端精致化的品飲技藝,消解著精英階層茶文化的技術含量和質量標準,從而逐步彌合茶文化雅俗之辨,走向融合發展的自然之途。
廟堂風致的盛極轉衰,民間意趣的發揚光大,代表著茶文化發展的歷史走向。雅俗融合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文人階層,他們是飲茶進入文化藝術天地的主要推動力,也是民間風俗效仿和模擬的對象。此前,文人階層更多的是通過上貢朝廷而影響朝野、推廣茶道;此后,則是追求生活技藝、藝術審美、精神愉悅的和諧統一,從而成為茶之雅文化的代表,進而影響四民、美化生活。明清以降的茶文化發展即是這種雅俗融合的體現。
飲法轉型:團餅煎點與散茶沖泡
從茶之品飲技藝而言,以蒸青制餅、煮茶清飲為特征的唐代煎茶法,以精制團餅、煮水點湯為特征的宋代點茶法,以及以散茶沖泡為特征的明代瀹茶法,代表著茶藝發展的三個階段。宋代正處于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南宋時期是從團餅煎點方法向散茶沖泡飲用方法轉型的過渡時期。
歷史地看,三個階段的劃分是相對而言的。早在以制餅煎煮為主導形式的唐代,也間有散茶飲法,如陸希聲《茗坡》詩所謂“惜取新芽施摘煎”,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所謂“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余”是也。宋代“茶有二類,日片茶,日散茶”,“臘茶(即片茶)出于劍建,草茶(即散茶)盛于兩浙”。洪州雙井茶號稱“草茶第一”,杭州的白云茶、香林茶、寶云茶、垂云茶也都是蒸青或炒青散茶,品飲時碾磨成末,以沸水沖點。黃庭堅《雙井茶送子瞻》所謂“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即是。
南宋以后,隨著以北苑貢茶為代表的團餅茶藝漸趨式微,草茶、散茶的制作和品飲方式在民間逐步普及開來,從兩浙、江右擴展到更多的茶區。正如南宋趙彥衛《云麓漫鈔》所謂:“今人不復為餅。”馬端臨《文獻通考·征榷考》也說:“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龍團,舊法;散者則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后,茶漸以不蒸為貴矣。”當今負有盛名的西湖龍井茶,宋代尚未知名,至元初虞集《次韻鄧善之游山中》日:“徘徊龍井上,云氣起晴晝……但見瓢中清,翠影落群岫。烹煎黃金芽,不取谷雨后。”可見元代已經基本完成從餅茶到散茶的主次轉換。明初朱元璋下詔罷團餅茶,“惟令采芽茶以進”,只是順應了餅茶制法、飲法的式微和散茶加工品飲風尚興起的歷史潮流,將這種方式推廣于宮廷,進而影響于朝野而已。
散茶沖泡也有一個從研末沖瀹到撮茶沖泡的演變過程。至明朝中葉,“今世惟閩廣間用末茶,而葉茶之用遍于中國,而外夷亦然,世不復知有末茶矣”(丘浚:《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九)。這種轉型和創新,不僅日趨簡便,而且“天趣悉備”,極大地推動了茶文化在民間的廣泛傳播,并終結了建茶的一枝獨秀,開啟了萬紫千紅的茶業發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