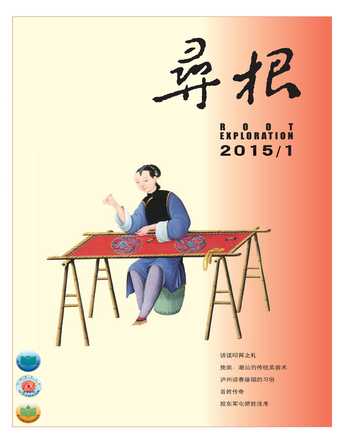羊脂玉與燕脂表玉
楊森
和田(古代稱于闐)美玉以白、潤為上品,現今民間好玉者動輒稱和田極品白玉為羊脂玉,但專業玩玉者通常則稱之為白玉,只字不提羊脂玉,否則就覺得是本行道的新手而非行家里手。但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第17號窟出土的五代時期的一份寫本文書中,已有羊脂玉這種類似的稱呼了。明代高濂《遵生八箋》“論古玉器”條云:“玉以甘黃為上,羊惜(脂)次之。”“今人賤黃而貴白,以見少也。”明代尚未以“羊脂”色玉為極品白玉,反而是低于甘黃色的二等玉。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五代寫卷P.2992V《兄大王(沙州歸義軍節度留后)某(曹元深)致弟甘州回鶻順化可汗狀》第19、20、21、22行:“今遣內親從都頭賈/榮實等謝/賀輕信,上好燕脂表玉境卜壹團重捌斤、白綿/綾伍匹。”該文書是五代敦煌地方政權曹氏歸義軍節度使曹元深(約939—944年執政)派遣到甘州回鶻去的使節攜帶八斤重的上等玉石等禮物,向順化可汗道謝、祝賀的一份信函和禮物清單。當時的甘州回鶻少數民族政權勢力比較強大,所以敦煌的曹氏地方政權要與他們進行友好相處,送重禮是必需的,后以兄弟相稱。此處的“燕脂表玉”,似乎是現代民間玩家特指和田的“羊脂玉”。這里“表”,當指玉石的表面。“境卜”,應釋讀為“鏡”字,當是指像鏡子一樣平整的意思,但法國學者哈密頓先生仔細觀摩該寫卷之“境”字旁一小“卜”字,認為是“該字應涂去”。敦煌文書中關于“卜”字是刪除的符號的例證有許多,如P.4640V《己未年辛酉年歸義軍衙內破用紙布歷》有“王建鐸隊武卜儛額子”,“武”字旁加小“卜”字,“武”字也是衍文。在一個字的旁邊加小“卜”字,是中古時期文人、書手對書寫的錯別字和多余字刪除的習慣做法。即使不需要涂掉該“境”字,也可以解釋它就是外表呈胭脂色且很平整的一塊玉團。之所以寫作“燕脂”,有可能是二字音近,將“羊脂”寫作“燕脂”也未可知。“燕脂”,古時也寫作“燕支”,原本應寫作“胭脂”,是指紅色的顏料或泛指紅色。因而此處的“上好燕脂表玉境卜壹團”,筆者猜測可能是指表面帶有紅顏色,即玉石的表皮上附著有褐紅或棗紅色、氧化后的鐵銹紅顏色等,或者就是對表皮帶紅色的籽料的特殊稱呼。《收藏》雜志2005年12月號刊登的俄羅斯籽料獲金獎的“觀音山子”,外皮就是相當艷麗的鐵銹紅色,可與胭脂色相媲美。再者,“脂”字還隱約含有油脂、發潤的意思,因為白玉既白又潤才更加寶貴,也才能命名為“羊脂玉”。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28載:元朝宰相“伯顏嘗至于闐國,于其國中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脈絡”。文中的“色如截肪”,即指如同切斷的羊等動物的白色脂肪,故而可以猜測元代發現的唐宋時代甚至更早時期的古玉佛屬于極品玉料的制品——白玉或羊脂玉。當時大多數向朝廷進貢和饋贈給重要人物的禮品玉,必然是類似的上等玉石,加之該敦煌文書中的“燕脂表玉”僅有八斤重,筆者認為它理應為山流水玉或者推斷它就是籽料,就是很潤并有油脂感的白玉——羊脂玉,只是外皮有鐵銹紅色。
敦煌出土的晚唐于闐文文書P.2741是于闐國“金國”使臣上報給于闐朝廷的報告即“使臣奏稿”,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于聞人攜帶有六百斤玉,作為進貢天朝宮廷的禮物。天朝使節收到了沙州張大慶的一封信,他后來在黨項人的護送下逃到了突厥人之中。”這是所見大批量進貢中原朝廷玉石的文獻記載。到五代和宋、遼時期,曹氏歸義軍政權進貢中原王朝和友邦的禮品中多數都是上等玉石。從一些史料記載看,五代、宋時期是于闐向中原王朝和友邦進貢、饋贈美玉的繁盛時期。如《冊府元龜》卷972載: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沙州曹議金進玉三團、硇砂、羚羊波斯錦、茸褐、白氍、牛黃、金星礬等”。《新五代史·四夷》載:“天福三年(938年),于闐國王李圣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郁金、牦牛尾、玉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冊圣天為大寶于闐國王。”“匡鄴等至于闐,圣天頗責誚之,以邀誓約,匡鄴等還。圣天又遣都督劉再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這是于闐國在五代、宋時期進獻玉石重量最大的一次。《宋史》卷490載:于闐“天福中其王李圣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來貢。高祖命供奉官張鄴持節冊圣天為大寶于闐國王。建隆二年十二月圣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為柙,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冊府元龜》《宋會要輯稿》《宋史》等文獻中,有關于闐國貢送美玉的記載還有多處。在敦煌莫高窟第244窟的甬道北壁底層西向第二身下部五代男孩供養人畫像旁有“德從子/德太子”題記。該甬道上的供養人畫像于闐太子“德從”是少年形象,可能是作為使節的成年德從太子經敦煌前往京城朝貢時,在敦煌滯留期間補畫補寫的。《宋史》卷490“于闐”條載:乾德“四年(966年),又遣其子德從來貢方物”。《續資治通鑒長編》卷7載:“乾德四年二月,于闐國王遣其子德從來貢方物。”這兩條史料所記為同一件事,證明敦煌壁畫上的這位“德從”宋初時的確是作為使者前往汴梁朝貢。
莫高窟第444窟東壁門上部中央“見寶塔品”南側有宋代于闐太子供養人題記“南無釋迦牟尼佛說妙法華經大寶于闐國皇太子從連供養”,北側有“南無多寶佛為聽法故來此法會大寶于闐國皇太子琮原供養”。P.3184V《齋文一篇》后題:“甲子年(964年)八月七日早聞太子三人來到佛堂內將法華經第四卷”;P.4792《壬申年、庚申年記事》有小字“壬申年五月廿日太子從原、從德二人寫字書記耳”。由于于闐太子有長期駐扎敦煌的,所以敦煌文書記載曹氏歸義軍衙署還為他們建有“太子宅”和“太子莊”。敦煌地方政權使節也向中原朝廷進貢玉石,《冊府元龜》卷972載:后唐長興三年(932年)“沙州貢馬七十五匹、玉三十六團”。《遼史》卷70屬國表載:遼圣宗統和二十四年(1006年)六月“沙州敦煌王曹壽遣使進大食馬及美玉”。沙州地方政權和其他地方政權、部族向中原朝廷所進貢的玉石,大部分可以說是來自干闐。這是因為:第一,五代、宋時期于闐國和沙州歸義軍有聯姻關系,經常互有使節走訪,于闐還有太子、公主、宰相等常駐敦煌,貴重禮品就是玉石。第二,敦煌(沙州)是西域通往中原的絲綢之路孔道,各國各政權的使節、商隊、僧人等來往穿行在這條路線上,敦煌歷來是國際商貿的重鎮所在,各種物品匯集于此,獲得于闐玉石也是便利的。第三,據敦煌文書資料我們知道,于闐、沙州、甘州等地均有使節、商隊、僧人等經絲綢之路輾轉到敦煌輸送貨物至內地及京城等處。
史料記載古代敦煌周邊地區也有一定數量的昆侖山系的玉石出產。敦煌晚唐時期文書P.4640《沙州釋門素法律窟銘》、S.530《大唐沙州釋門素法律義辯和尚修功德記碑》就直接稱敦煌為“玉塞敦煌”,況且敦煌附近早在漢武帝時就置有后來名聞遐邇的所謂“玉門關”,意思就是西域輸入玉石的關口。敦煌本地的玉石出產,多少也會增加敦煌周邊數個地方政權向中原朝廷進貢玉石的數量和次數,雖然玉石的質量不如于闐,但也聊勝于無。敦煌在中晚唐時被當地人稱為“玉塞”,當與本地產玉和于闐玉石等出入的“玉門關”關口均有關系。
敦煌文書中的這件“上好燕脂表玉”玉料尚未加工成形,屬于原石,故此文書稱“壹團”,但是唐五代時期敦煌本地的確也有“玉匠”行業存在。據敦煌五代寫卷P.2641《丁未年(947年)六月都頭知宴設使宋國清等諸色破用歷狀并判憑》第一份賬目第8、9行:“支玉匠平慶子等二人,共面柒/斗。”同卷第二份賬目第20行:“玉匠面叁斗伍升。”又,宋代寫本S.1366《歸義軍衙內面油破用歷》第48行:“支玉匠二人一日食。”敦煌的“玉匠”,敦煌文書顯示在晚唐、五代就已經是眾多工匠中的一種了,實際玉匠的產生可能還要更早些,因為敦煌地區是于闐玉石向中原輸送的重要通道。敦煌在中古時期也算絲綢之路上玉石雕琢的重要場所。然而晚唐、五代、宋時期敦煌的玉匠中還未見到當時屬于高級別匠人稱號——“博士”,敦煌的“某某匠”地位和水平要低于高級工匠“博士”,可以猜測敦煌玉匠的水平應是低于中原京城地區的。從史料中每每看到所進貢的玉石多數是以數“團”、幾十“團”和百“團”記錄的,說明進貢的多是原石材料,還不是雕琢的成品。但在敦煌向中原王朝和向其他政權進貢的美玉飾件中諸如腰帶飾等,或許有敦煌玉匠等雕琢作品的存在。如《冊府元龜》卷169帝王部·納貢獻記錄:同光四年(926年)“二月,沙州曹義(議)全(金)進和市馬百匹、羚羊角、石岡(硇)砂、牦牛尾,又進皇后白玉符、金青符、白玉獅子指環、金剛杵”。此“皇后白玉符”“白玉獅子指環”可能就是敦煌玉匠所為,而這兩件進貢的玉石符和指環都在前面書有“白玉”二字,也可證明它們均是上等美玉,但可能不太潤,而且無法與“燕脂表玉”媲美。至于玉石結構內含棉絮狀方為良玉的特點也罕見有史料記載。《冊府元龜》卷972載:后唐長興五年(934年)正月,“回鶻可汗仁美遣都督石海金來朝貢良馬百駟、白玉百團,謝冊命也”。這二條史料所記錄的沙州(敦煌)、甘州回鶻“白玉”制品,是朝廷史官所用的官方稱謂,而當時民間對上等美玉的稱呼可能很雜,但民間用“白玉”的稱謂反而罕見。
敦煌五代文書中的“上好燕脂表玉”,或許可以說明當今民間的所謂和田(于闐)“羊脂玉”稱謂有其來源,并非臆造的名稱,而是源自“燕脂表玉”的稱呼或者古代的習慣叫法和俗稱,加之讀音相近、字形也有相近之處。明代文人高濂較早使用“羊脂”稱呼第二等的玉石,似乎也有所本,但此名稱也可能僅限于明代玩玉的上層人士中使用,后來才漸漸流傳到民間。所以現今將成色名貴的第一等白玉俗稱為“羊脂玉”,也并非是假造的名詞和說的外行話,況且現在學術界也在學術論文中使用“脂玉”之名了,但卻是與“白玉”和“青玉”并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