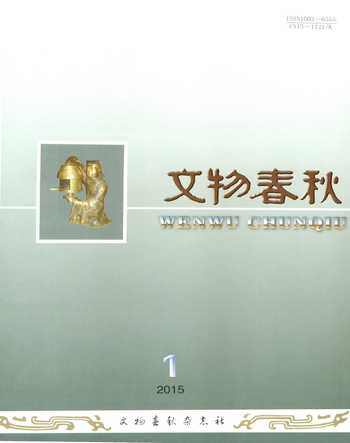曇石山遺址出土紡輪研究(上)
吳衛
【關鍵詞】福建;曇石山遺址;紡輪;閩江下游流域;史前文化
【摘 要】本文通過對福建省曇石山遺址及閩江下游流域同類型遺址中出土的紡輪進行觀察和比較分析,總結了曇石山遺址出土紡輪的基本特征,對其制作方法、技術和工具進行了闡釋,探討了各時期不同型式紡輪的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當地的史前紡織水平,最后對紡輪紋飾和紡輪隨葬現象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和分析,并探索了其文化內涵。
曇石山遺址位于福建省閩侯縣甘蔗鎮曇石村,系一處緊鄰閩江的條形山崗,面積3萬多平方米。自1954年被首度發現至今,考古工作者先后對該遺址進行了十次規模不等的考古發掘。研究表明,曇石山遺址的文化層內涵極為豐富,從早到晚可分為曇石山下層時期(5500B.P—5000B.P)、曇石山文化時期(5000B.P—4000B.P)、黃瓜山時期(4000B.P—3500B.P)和黃土侖時期(3500B.P—3000B.P)[1],是研究福建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閩江下游流域史前文化序列最完整的一處遺址。
在曇石山遺址的歷次發掘出土了為數眾多的紡輪,根據已發表的發掘報告統計有307件。這些紡輪型式多樣,大小不一,既有出自地層的,也有出自墓葬的,部分紡輪還帶有紋飾或彩繪。系統地對這些紡輪進行統計和分析,有助于探索以曇石山遺址為代表的閩江下游流域史前紡織的面貌;而對紡輪紋飾及隨葬現象的考察,也有助于了解紡輪作為紡織工具之外所承載的其他社會功能。
一、紡輪的歷史、功用及意義
紡輪,也被稱為紡專、縛盤、紡砣等。作為一種紡織工具,紡輪須與拈桿結合方可使用,二者結合即被稱為紡錘、縛或線砣。由于拈桿多為竹、木質,難以保存,所以罕見帶拈桿的紡輪出土。紡輪出現于新石器時代,據目前公開發表的考古文獻,在我國使用紡輪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約8000年前。早期的紡輪以破碎陶器的碎片磨制、鉆孔制成。例如河北武安縣磁山遺址出土的11件紡輪,均系陶片磨制而成,經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約7355至7255年左右[2];河南新鄭縣裴李崗1979年發掘出土2件陶紡輪,也由陶片制成,經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約7445至7145年左右[3]。大約在距今7000年左右,燒制的紡輪開始出現。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曾發現兩件帶刻劃紋的燒制陶紡輪,距今約7000至6500年[4]。福建省境內目前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是平潭殼丘頭遺址,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約6500至5500年,在1985年至1986年進行的首次發掘中,共出土8件陶紡輪,均系燒制[5]。
關于紡輪的使用方法,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認為,我國紡輪的用法可分為懸垂式和支撐式兩種。懸垂式用法根據紡輪在拈桿的位置不同又分為兩種:紡輪在拈桿下部的稱為底輪或低輪紡錘,紡輪在拈桿上部的稱為頂輪或高輪紡錘。支撐式紡錘的拈桿和紡輪都比較粗大,不宜懸掛起來紡紗,故只能支撐于地面進行作業[6]。在曇石山遺址出土的紡輪尺寸最大不超過7厘米,故使用時應采用懸垂式,其具體用法是:將拈桿固定于紡輪中孔,然后提吊起來,捻動拈桿下端,紡輪依靠自身質量和慣性力在旋轉中將纖維牽伸并加拈。拈桿頂端的鉤子用于定拈,可使加拈的線縷不致松散。績到一定長度時纏繞到拈軸上,一定數量后將纏在拈桿上的坯線取下。之后將坯線合股,完成線、繩的制作[7]。
新石器時代是人類走向定居生活和農業文明的重要時期,紡輪在這一時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人們開始定居,紡輪便出現在重要工具中,我們能夠確定,農業的發明和紡錘作為一種文化因素的出現,兩者是有密切關系的。”[8]可以說,紡輪是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重要標志之一。
二、紡輪質地、型式和制作方法
制作紡輪的材料較多,有石質、玉質、陶質、木質、骨質等,但曇石山遺址出土的紡輪均為陶質。根據截面形狀的不同,這些紡輪可分為7型(圖一)[9]:
Ⅰ型 上下兩面平整且直徑相等,截面呈長方形,邊線呈豎直或略帶弧形。該型又可分為兩個亞型:
Ⅰa型 邊線豎直,與底邊成直角,截面為規整的長方形;
Ⅰb型 邊線略帶弧度,剖面形似盤鼓。
Ⅱ型 上下兩面平整,截面呈倒置的等腰梯形。根據厚度的差異,該型可分為四個亞型:
Ⅱa型 截面呈倒置的扁平等腰梯形;
Ⅱb型 截面呈倒置的厚等腰梯形;
Ⅱc型 截面呈倒置的等腰梯形,但上邊不平直,呈向內凹陷的弧線;
Ⅱd型 截面呈倒置的等腰梯形,但左右邊線向內凹。
Ⅲ型 上下兩面平整,截面呈六邊形。根據上半部與下半部邊線長短的差異,該型可分為兩個亞型:
Ⅲa型 截面呈上半部與下半部邊線基本等長的六邊形;
Ⅲb型 截面呈下半部邊線較上半部長的六邊形。
Ⅳ型 上下兩面平整,截面呈帶束腰的倒置等腰梯形。根據其上邊彎折情況的差異,此型可分為兩個亞型:
Ⅳa型 截面呈帶束腰的倒置等腰梯形,上邊無彎折;
Ⅳb型 截面呈帶束腰的倒置等腰梯形,但上邊有向下彎折。
Ⅴ型 截面近似菱形,根據其邊線弧度的差異,可分為兩個亞型:
Ⅴa型 上下兩面鼓起似兩個削去頂端的圓錐形,邊線呈直線且四邊長度相等,截面近似標準的菱形;
Ⅴb型 上下兩面鼓起似兩個覆缽形,邊線呈弧線且四邊長度相等,截面似橄欖形。
Ⅵ型 一面平整或微凹,另一面則鼓起,截面呈覆缽形,根據其厚薄差異,可分為兩個亞型:
Ⅵa型 較厚,截面呈弧度較大的覆缽形;
Ⅵb型 較薄,截面呈較扁、近似三角形的覆缽形。
Ⅶ型 系陶片打磨成圓形,中間穿孔制成,截面為長方形。
根據對出土陶制紡輪的觀察,應有兩種制作方法:第一種為利用現成的陶片加以磨制成圓形后鉆孔而成;第二種為手工捏制成陶坯,再經修整、鉆孔后燒制而成。
對陶坯的修整包括兩個步驟:首先是對平面部分的修整,其次是對邊沿的修整。對平面的修整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手捏平,另一種則是用某種類似刀片的工具刮削而成。這種工具可能用竹、木、石、骨等制成。竹、木質工具易腐朽,難以保存下來,但石質和骨質工具還是有跡可循的。殼丘頭遺址出土的兩件骨匕值得注意:編號H11∶2的骨匕,長10.6厘米,寬1.5厘米,厚0.2厘米(圖二);編號T205⑤∶4的骨匕,長15.8厘米,寬1.4厘米,厚0.2厘米[10]。這兩件骨匕質地輕薄,不論是作為武器還是用于切割肉類或植物均不適用,很有可能是用于包括紡輪在內的陶器修整。對邊沿的修整亦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純手制,但這種方法有可能造成紡輪的變形(圖三,1);另一種則顯然采用了輪制工具,紡輪形狀及面上裝飾的同心圓紋飾呈完美的圓形(圖三,2)。
鉆孔方式有單面和雙面兩種。單面鉆孔即使用鉆孔工具從陶坯的一面直接鉆通至另一面,其截面有兩種情況:一種孔徑上下相同,鉆孔截面呈長方形;另一種則一面孔徑較大,截面呈梯形。雙面鉆孔即使用圓錐狀鉆孔工具先從紡輪陶坯的一面鉆透,再從另一面鉆透處鉆入同樣深度,使得兩面鉆孔大小基本相同,截面呈亞腰形。曇石山遺址出土紡輪中這兩種鉆孔方式均有采用:由磨制陶片制成的Ⅶ型紡輪均采用雙面鉆孔(圖四,1、2),燒制紡輪則多采用單面鉆孔,只有極少數采取雙面鉆孔方法。推測因Ⅶ型紡輪系用現成的陶片磨制而成,因其質地比較脆硬,若采取單面鉆孔方式易導致陶片開裂,故采用雙面鉆孔的辦法。至于燒制紡輪中采取雙面鉆孔的原因則與其使用的工具有關。有研究者根據陶制紡輪上的鉆孔痕跡將鉆孔工具分為三大類,一是錐狀工具,二是直接使用拈桿,三是空心管狀工具。前二者會在鉆孔四周留下微凹或微凸的痕跡(圖四,3、4、7),第三種則不存在這種痕跡(圖四,5)[11]。對曇石山遺址出土紡輪的觀察可印證這一說法。但這里要補充說明的是:有別于燒制紡輪直接用工具刺透來鉆孔的辦法,Ⅶ型紡輪由于是在陶片上鉆孔,故使用的工具應為石質,比較尖銳且帶棱邊,如尖端呈銳角的石片或石錐,其方法是在紡輪上旋轉鉆透,因此在其兩面鉆孔外圍都會留下明顯的鉆痕。
在曇石山遺址歷次發掘中并未發現紡輪的鉆孔工具,推測原因應有三點:一、這類工具多為竹、木質,難以保存至今;二、這類工具便于就地取材,任意細長且較堅硬的物品稍作加工即可使用,無須特別制備,某些紡輪的鉆孔呈現不規則圓形的現象也反映了當時使用鉆孔工具的隨意性;三、鑒于曇石山遺址出土的部分貝器和陶器上也存在鉆孔現象,不排除這些鉆孔工具是可以與紡輪的鉆孔共用的。
在曇石山遺址出土的紡輪中,有一部分紡輪的鉆孔位置偏離圓心較明顯,而另一部分紡輪的鉆孔則與圓心的位置比較吻合。這一現象引出了一個問題:當時對紡輪鉆孔是如何定位的?顯然,對于鉆孔偏離圓心較多的這部分紡輪,推測應當是目測定位(圖四,6、7)。而鉆孔比較符合圓心位置的紡輪,不排除有的是目測定位,但大部分應有某種輔助辦法,比如在紡輪的一面對稱勾畫出“十”字或“人”字形線條,亦或是三條交叉成“
三、各時期的分布情況
對曇石山遺址文化內涵的界定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期,在1964至1965年期間進行的第六次發掘報告確定了對曇石山下層時期和曇石山文化時期的認識,但對上層的劃分尚不明確,直至1996年進行第八次發掘之后,結合1989年對寧德市霞浦縣黃瓜山遺址[12]的發掘情況,將曇石山遺址上層進一步劃分為黃瓜山時期和黃土侖時期,從而最終明確了曇石山遺址的文化內涵。曇石山遺址的前五次發掘規模都較小,出土紡輪數量也很少,因此在本節討論中所選取的樣本,除曇石山下層時期為第六次至第十次發掘出土的之外,曇石山文化時期到黃土侖時期的樣本均為第八次到第十次發掘出土的紡輪。
根據對曇石山遺址各時期出土的紡輪形制和數量分布情況的觀察(表一),可歸納出以下三個現象:
1.曇石山下層時期出土的紡輪數量較少,從類型來看,以陶片磨制的Ⅶ型紡輪數量占多數。此型紡輪在曇石山文化時期仍有一定數量在使用,到黃瓜山時期僅見1件,黃土侖時期則不見該型紡輪。
2.從數量來看,曇石山文化時期的紡輪出土量最大。從黃瓜山時期開始,紡輪的出土數量明顯下降,到黃土侖時期更是急劇減少。
3.從形制來看,Ⅱ、Ⅲ兩型數量居多,占比在60%以上,而Ⅰ、Ⅵ兩型數量極少。
對上述現象筆者試作以下分析:
首先,曇石山下層時期是福建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早期代表,這一時期的遺址數量稀少,目前發現該時期的遺址,除曇石山遺址外,僅有平潭殼丘頭遺址、金門富國墩遺址[13]、馬祖熾坪隴遺址[14]以及閩侯白沙溪頭遺址[15]等幾處。這些遺址出土的陶器多為夾砂粗陶,燒制火候較低,出土石器僅刃部磨制,打制痕跡明顯,這反映了這一時期閩江下游流域史前人類人口較為稀少,且生產力低下的特點。由陶片磨制的紡輪制作比較粗糙,被認為是陶紡輪的初期形式,也印證了這一時期文化較為原始的觀點。
其次,曇石山文化時期出土紡輪數量最多,說明該時期紡輪得到了大量使用。這一時期是福建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一個繁盛期,目前發現的遺址數量和分布情況都印證了這一點。包含這一時期文化遺存的遺址已發現有10余處,分布范圍也從閩江口一帶擴展到閩清縣、福清市等地。但有趣的是,從黃瓜山時期起,曇石山遺址出土紡輪的數量明顯下降,到黃土侖時期則可用稀少來形容。為考察這是個別現象還是普遍現象,本文參考了閩侯縣莊邊山遺址[16]、溪頭遺址、古洋遺址[17]、黃土侖遺址[18],福州市羅漢山遺址[19]以及福清市東張遺址[20]的紡輪出土情況。
從表二可見,黃土侖遺址、古洋遺址、羅漢山遺址不見曇石山文化時期的地層,溪頭遺址、黃土侖遺址、古洋遺址以及羅漢山遺址不見黃瓜山時期的地層,莊邊山遺址不見黃土侖時期的地層,因此也不存在相應時期紡輪的出土。
莊邊山遺址和東張遺址均有黃瓜山時期的紡輪出土,且均存在曇石山文化時期的紡輪出土較少,黃瓜山時期紡輪的出土量大增的現象。而黃土侖時期各遺址紡輪出土數量普遍減少,其中作為這一時期典型遺址的黃土侖遺址僅出土了2件,溪頭遺址和東張遺址則較前期顯著減少。
通過上述比較,本文認為,雖然曇石山遺址出土的紡輪數量在黃瓜山時期和黃土侖時期均有所下降,但其原因是有差異的。在黃瓜山時期,除曇石山遺址外,其他遺址的出土數量均較此前一個時期顯著增加,因此曇石山遺址的數量減少應屬個別現象。而在黃土侖時期,包括曇石山遺址在內的各遺址出土數量均出現顯著甚至急劇下降,則是一種普遍現象。
再次,Ⅱ、Ⅲ型紡輪的數量在出土紡輪中占據較大比例,說明這兩型紡輪在當時使用廣泛。
最后,從制作工藝上看,Ⅰ型紡輪是最簡單的:只要將陶泥搓成長條后切割、鉆孔,制成陶坯,然后燒制即可,十分適合規模化的制造。但是在曇石山遺址出土的紡輪中,Ⅰ型數量卻極少。此外,出土各型紡輪的尺寸也各不相同,這表明這些紡輪應系手工單個制作,并不存在規模化制作的現象。
(未完待續)
————————
[1]福建博物院:《閩侯曇石山遺址第八次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07—108頁。
[2]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3期。
[3]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1979年裴李崗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1期。
[4]林華東:《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5][10]福建博物院:《2004年殼丘頭遺址發掘報告》,《福建文博》2009年1期。
[6]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卷5一9手紡卷,劍橋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72頁。
[7]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
[8]德·利普斯著,汪寧生譯:《事物的起源》,貴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2頁。
[9]a.華東文物工作隊福建組,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探掘報告》,《考古學報》總第10期;b.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四次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12期;c.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廈門大學考古實習隊:《福建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五次發掘簡報》,《考古》1964年12期;d.福建省博物館:《閩侯曇石山遺址第六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6年1期;e. 福建省博物館:《福建閩侯縣曇石山遺址發掘新收獲》,《考古》1983
年12期;f.同[1];g.福建省曇石山遺址博物館:《閩侯曇石山遺址2004年考古發掘簡報》,《福建文博》2010年1期;h. 福建省曇石山遺址博物館:《2009年曇石山遺址考古發掘簡報》,《福建文博》2013年2期。
[11]王迪:《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山東地區紡輪淺析》,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48頁。
[12]福建省博物館:《福建霞浦黃瓜山遺址發掘報告》,《福建文博》1994年1期。
[13]韓起:《臺灣省原始社會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3期。
[14]陳仲玉:《談馬祖熾坪隴史前遺址的文化》,載《百越文化研究——中國百越民族史學會第十二次年會暨百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
[15]a.福建省博物館:《福建閩侯白沙溪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次發掘簡報》,《考古》1980年4期; b.福建省博物館:《閩侯溪頭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4期。
[16]福建省博物館:《閩侯莊邊山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8年2期。
[17]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福建閩侯古洋平崗先秦遺存的發掘》,載《東南考古研究》第三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
[18] 福建省博物館:《福建閩侯黃土侖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4期。
[19]羅漢山遺址發掘報告尚未發布,本文所引數據來自對發掘記錄的整理。
[20]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福建福清東張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1965年2期。
[21]溪頭遺址上層(黃土侖時期)堆積擾亂情況較嚴重,出土的器物中不僅有黃土侖時期的,還摻雜部分曇石山文化時期的,根據對上層出土紡輪的陶質判斷,在15件紡輪中,11件為泥質陶,4件為灰硬陶。硬陶為黃土侖時期陶器的典型特點之一,且其他各處遺址出土的該時期陶紡輪均為硬陶。故本文將這4件計入黃土侖時期,而將其余11件計入曇石山文化時期。
[22]東張遺址上層也存在擾亂現象,部分中層時期(黃瓜山時期)的器物摻雜其中,但報告中未詳細說明出土紡輪的陶質,故無法進行區分。但可以肯定的是,東張遺址上層(黃土侖時期)的紡輪數量是少于報告中統計的74件的。
〔責任編輯: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