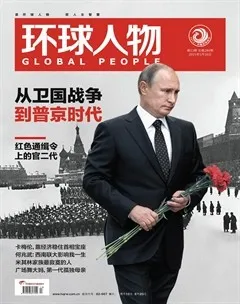我親歷的衛國戰爭
莫斯科戰士:
“老天也要消滅德國侵略者”
1941年11月7日,莫斯科,紅場,悲壯之地。
這是銘刻在紅場歷史上最特殊的一次閱兵。城外,百萬德軍圍城,蘇軍只有幾十個步兵師勉力防御;城內,德機持續轟炸,蘇軍強力攔截,各國外交人員紛紛撤離。
天還沒有完全亮,斯大林登上了閱兵臺,他決定與莫斯科共存亡。在講話中,他號召莫斯科軍民與他一起,堅守此城。數十萬紅軍官兵志氣高昂地走過紅場,和所有的閱兵不同,他們沒有終點,他們直接開赴戰場。
這也是紅場上最短的一次閱兵,前后僅用了25分鐘,但它改變的是整個二戰。25分鐘后,蘇聯各地掀起參軍熱潮,從遠東和西伯利亞趕來的援軍也奔向前線,蘇軍在莫斯科的兵力迅速上升到110萬人。12月,反攻開始了。第二年4月20日,蘇軍以70萬人傷亡和被俘的代價,把德軍趕到了莫斯科城外100至350公里處,首次打破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希特勒的“閃電戰”破產了。
1945年5月9日,莫斯科,紅場,狂歡之地。
納粹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經過1418天苦戰,犧牲了2700萬兒女的蘇聯人涌進紅場,狂喜吶喊,擁吻起舞,在巨大的苦難過后迸發出巨大的歡呼。那是一個國家經歷了漫長的、未知終點的生死劫難,終于抵達彼岸時的痛徹激情。
6月24日,前方的戰士回到紅場,回到他們出發的地方,用一場新的閱兵宣告勝利和新生。其中200名士兵倒持著戰爭中繳獲的200面納粹軍旗走過檢閱臺,把旗子拋在紅場一側的列寧墓前,以此向祖國致敬。
為了紀念在莫斯科保衛戰中陣亡的將士,莫斯科城外建起了一座高大的紀念碑。2015年5月8日,晴空萬里,91歲的老兵馬爾欽科·格奧爾吉耶維奇來到紀念碑前,悼念曾和他并肩保衛莫斯科、最終長眠在這片土地上的戰友們。隨后,他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起這座城市的傷痛時刻——
1941年6月22日,德軍入侵蘇聯,當時我17歲,讀9年級。那天中午12點,莫洛托夫發表廣播講話,號召全國人民抗擊德軍。我和同學們聽到這一消息,都很氣憤,跟著大人們走上街頭,要求參軍上前線。
一周后,我們就拿到了武器,有槍也有炮,大家有的當了步兵,有的當了炮兵,還有的當了裝甲兵或騎兵。我成了一名步兵,加入了莫斯科民兵第二十一步兵師。
7月7日,部隊開拔了。我們向著距莫斯科西南方向近400公里的斯摩棱斯克前線進發,那里是通往莫斯科的重要據點。
我在學校里曾接受過很好的軍事訓練,體能和軍事技術都比較過硬。但在斯摩棱斯克戰役中,我看到身邊的戰友一個個倒下,心里確實害怕。我只能告訴自己害怕是沒有用的,必須經歷它,適應它。
在一次戰斗中,我和德軍直接遭遇了。在戰友的掩護下,我干掉了3個前來偷襲的德軍士兵。但在撤退時,我一不小心掉進了沼澤地,幸虧旁邊的戰友把手中的槍伸了過來,我抓住槍管才爬出來。就是這位戰友,兩天后被德軍的炮彈炸死了。我非常懷念他,每年都要到紀念碑前給他獻花。
9月中旬,德軍繞過了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逼近,我就隨部隊撤往莫斯科南郊,駐扎在距離市中心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投入莫斯科保衛戰。
德軍入侵之前,莫斯科是個坐落在森林中的花園城市,地鐵已經通了6年,基礎設施十分現代化。納粹的鐵蹄改變了這一切。為了備戰,莫斯科市數百萬居民同仇敵愾,在城內外構筑了層層疊疊的防御工事和縱橫交錯的戰壕。
德軍揚言要在10天內拿下莫斯科。10月2日起,德國180萬大軍從西、北、南三面向莫斯科發起進攻,其中西北方向的攻勢最強勁,一度打到距離克里姆林宮僅32公里的波良納。德國陸軍元帥博克登上那里的一座塔樓,用望遠鏡眺望,激動地說:“我終于看到克里姆林宮的房頂了!”
當時戰況非常慘烈。有的團一次戰斗下來,只剩下幾十個人甚至幾個人。我們這一批學生兵,原來有1萬多人,戰后僅剩1000多人。我常常翻看我們班9年級時拍的合照,那些同學有的犧牲了,有的失蹤了。還有很多莫斯科家庭是全家多人上前線,有的父子犧牲在同一個戰壕里。我們家也是好幾個人上前線,我的哥哥就在莫斯科保衛戰中犧牲了。
全國各地的兵力都被調集來保衛莫斯科。有的地方對德軍形成內外夾擊,這也是對莫斯科形成多層防御。我要向你們介紹我的一位戰友庫茲明科·尼基季奇,他今年93歲了。當年他所在的第十六集團軍三二四步兵師就駐扎在莫斯科西南200多公里的地方,與我們駐扎在近郊的部隊內外配合,夾擊德軍。

有一次,庫茲明科去查哨,沒有帶槍,只帶了一把馬刀。在回師部的路上,他無意中發現了一小股企圖偷襲師部的德軍。這時,他已來不及去報告,就抽出馬刀,高喊著“德國兵來了”,向敵人沖了過去。他這一喊給自己的部隊報了信,哨兵聽到喊聲,鳴槍報警。這股德軍一看大事不妙,調頭逃走了。庫茲明科的機智勇敢讓三二四師避免了一次災難。
還有一次,第十六集團軍制定了一個攻擊德軍的秘密行動,要求他們師的九十七團配合,但電話和無線電都聯系不上。師長把聯絡任務交給了庫茲明科,讓他親自去傳達。但九十七團和師部被德軍隔開了,要想完成任務,必須穿越德軍防區。庫茲明科只帶了兩名士兵就出發了。在一條水溝旁,他們被德軍發現了。突圍過程中,一名士兵中彈,倒在了水溝里。他和另一名士兵眼看就要穿過德軍防區了,一枚炮彈在他們身后炸響。庫茲明科回頭一看,另一名士兵也倒在血泊中,頭都沒了。他自己的腰部也被彈片擊中,但他堅持趕到了九十七團,傳達了軍部指令。后來,九十七團執行的突擊行動很成功,消滅了2000多名德軍士兵。庫茲明科也因此得到了一枚勛章。
在莫斯科軍民的頑強抵抗下,德軍的“閃電”行動一次次被遏制,變成了持久戰。歷時近7個月,德軍最終敗退。
當然,我們能夠勝利,也離不開天時地利的因素。德軍原計劃在嚴寒到來之前拿下莫斯科,但被我們拖住了。天氣一冷,德軍缺少防寒衣物,運輸車輛的油料也不抗凍,大批武器和裝備癱瘓。而我們既有防凍抗寒的棉衣、皮靴,又有挖好的戰壕可以御寒。天氣越冷,雙方戰斗力的懸殊就越大。可以說,連老天也要消滅德國侵略者。
攻入柏林將領:
“只有前進,沒有后退”
1945年4月26日,德國,柏林,決勝之地。
蘇聯紅軍發起了最后的進攻,成排的喀秋莎火箭炮一起發射,它們的目標——柏林市中心。
4月27日,紅軍打進柏林市區。4月28日,紅軍到達了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廣場。就在這一天夜里,希特勒在他15米深的地堡里,口述了兩份遺囑:一份任命海軍上將鄧尼茨為他的“繼承人”,一份決定與他17年來的情人愛娃·布勞恩結婚。4月30日下午,地堡里的希特勒將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愛娃服毒身亡。就在這一天,蘇聯紅軍把勝利的紅旗插上了德國國會大廈的圓頂。5月7日,鄧尼茨宣布德國無條件投降。
5月8日深夜12時,柏林郊外的卡爾斯霍爾斯特,在蘇軍元帥朱可夫主持下,德方代表與蘇、美、英、法軍隊的代表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投降書從5月9日零時開始生效。由于時差,蘇聯當時已是5月9日凌晨,美、英、法等國還是5月8日下午和夜間。后來,西方國家把5月8日定為歐洲勝利日,蘇聯的勝利日是5月9日。
還有什么方式比閱兵更能表達戰勝者的心情呢?5月4日,蘇軍柏林衛戍區部隊在勃蘭登堡門和國會大廈旁舉行了閱兵式。當時柏林的街道上還冒著煙,蘇軍的軍服上仍沾滿灰塵,但齊步行進在廢墟旁的將士們氣宇昂揚。
9月7日,蘇、美、英、法四大盟國舉行了聯合閱兵式。蘇聯是主角,于是其他三國有意低調處理。盟軍在這次閱兵式上表現出的貌合神離,被認為是冷戰悄然展開的標志之一。當然,這是后話了。


柏林的這些歷史性時刻,蘇軍將領崔可夫帶著傷一一見證了。3年中,他從斯大林格勒打到了柏林。他率領的部隊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的一支鐵軍。這場發生在1942年到1943年的戰役是整個二戰的轉折點,此戰后,蘇軍開始掌握主動權。70年后的這個5月,崔可夫的孫子尼古拉在自家的別墅里,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了祖父的光輝歲月——
1942年春天,我們取得了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但德國的攻勢并未減弱,他們制定了夏季進攻計劃,企圖在南線集中兵力,攻克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區,奪取石油資源,占領伏爾加河下游。
1942年6月,德軍開始進攻伏爾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蘇軍決心死守。9月,祖父臨危受命,出任第六十二集團軍司令官,率軍駐扎在伏爾加河西岸。他向上級表達了決心:“我發誓,絕不離開斯大林格勒,我將采取一切辦法堅守。要么守住城市,要么戰死在這里!”
祖父是一個進攻型的指揮官,在他的字典里只有前進,沒有后退。一次祖父視察軍營,發現一個師長把指揮部設在了相對安全的河東岸,于是怒不可遏,一拳就把師長打倒在地。由于祖父穿著大衣,師長的警衛員不知來人是誰,立即撲了上去,打倒了祖父。這時,祖父大衣里的軍銜露了出來,警衛員發現是位將軍,知道闖了禍,趕緊請罪。正常情況下,襲擊司令官是要被槍斃的。但祖父覺得,戰爭期間應好好保存力量,不能輕易殺死一名戰士。他站起來拍了拍那名士兵,說了聲“好好干”。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以巷戰激烈聞名于世。1942年底,德軍發起最后一次猛攻,第六十二集團軍被切成3段。街道和廣場都變成了殘酷的戰場。祖父指揮部隊以建筑物為據點,阻擊敵人。他把指揮部設在陣地上,不后退半步,大大鼓舞了官兵的士氣。有一次,祖父看到一名戰士受傷,上前詢問:“感覺怎么樣?”戰士只說了一句話:“我是六十二軍的。”別的什么也沒說。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以蘇軍勝利而結束。兩個月后,第六十二集團軍改編為近衛第八集團軍,祖父率軍繼續向西進發,先后參加了庫爾斯克、頓巴斯、頓涅茨克等戰役,以及解放敖德薩要塞的戰斗。敖德薩解放當天,莫斯科還鳴禮炮慶祝這一勝利。此后,第八集團軍編入朱可夫元帥領導的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作為主力解放白俄羅斯,后又攻克波蘭、東普魯士,一路向柏林打去。
說起來,祖父還是第一個得知希特勒自殺的蘇軍將領。5月1日凌晨,德國陸軍總參謀長克萊勃斯鉆出掩體,前往祖父的指揮部,商談停火事宜。克萊勃斯神神秘秘地對祖父說:“我告訴您一件絕對機密的事,您是我通報的第一位外國人——希特勒已于昨天自殺了。”祖父不動聲色,淡淡地回答:“這消息我們已經知道了。”但他立即到另一個房間給朱可夫元帥打電話匯報。十幾分鐘后,斯大林發出指示:“德軍只能無條件投降,不能進行任何談判。”克萊勃斯只好悻悻地回去了。第二天,克萊勃斯聲稱要投降,讓祖父過去。沒想到祖父在那里突然遭到德軍強硬分子槍擊,腿部中彈,幸虧有衛兵拼死相救。1955年,祖父被授予元帥軍銜。
祖父當初是從中國被調回蘇聯參加衛國戰爭的。他1900年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家境貧寒,12歲就輟學前往圣彼得堡(1924年至1992年稱為列寧格勒)謀生。1922年,祖父進入紅軍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后改為伏龍芝軍事學院),在東方系中國部深造,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學習漢語。1926年,他以學院實習生、外交隨員的身份第一次到了中國。次年,祖父畢業,被再次派往中國,當了兩年軍事顧問。
1940年,已侵占了大半個中國的日本,在北上進攻蘇聯和南下同英美開戰之間舉棋不定。這種情況下,熟悉中國情況的祖父再次被派往中國。斯大林對他說:“你在中國的任務是幫助中國軍隊拖住日軍的一條腿,絕不能讓日軍北上。如果日軍北上,德軍又從西面入侵,我們就會陷入兩面作戰的境地。”

祖父還給國民政府送過一份厚禮,包括150架戰斗機、100架轟炸機、300門大炮、500輛卡車等裝備。但不久,“皖南事變”爆發,祖父很震驚。他在會見國民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時問:“你們是不是在和新四軍的沖突中使用了我國提供的武器?”何應欽含糊其辭。祖父表示,如果中國發生內戰,將很難再得到蘇聯援助。當時,祖父領導的顧問團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著蘇聯援助物資的分配。“皖南事變”使國民政府陷入外交被動,不得不表示停止對共產黨發動軍事行動。在這件事情上,祖父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后來,祖父當過蘇聯國防部副部長、陸軍總司令等職,1982年去世。
列寧格勒女英雄:
“我是步兵團的女兒”
1945年5月9日,蘇聯加盟共和國拉脫維亞首府里加,歡呼之地。
一名當時的小學生牢記那天的情形:凌晨時分,熟睡中的她被喧鬧聲吵醒。在自家的廚房里,她看到身為軍人的父親和許多戰友坐在餐桌旁。父親對她說:“高興點,我的女兒。希特勒徹底完了,我們勝利了!”父親身邊的一位士兵眼含熱淚地說:“小姑娘,戰爭終于結束了!”天一亮,她和哥哥來到大街上,看見到處是歡呼的人群,“勝利”“萬歲”的呼喊不斷響起。傍晚,她看到一支蘇聯紅軍部隊經過里加市中心。行進中的士兵們雖然疲憊,衣服和靴子沾滿塵土,但精神飽滿,臉上掛著笑容。路邊的人們把采來的野丁香送到士兵手中,并歡快地拍著他們的肩膀。
時間倒回到4年前。1941年6月,德國突然入侵蘇聯,作為蘇聯西側、緊挨波羅的海的加盟共和國,拉脫維亞較早被德軍占領。兩個多月后,德軍開始圍攻列寧格勒,希特勒叫囂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發祥地列寧格勒從地球上抹掉”。
此后的872天里,蘇軍和德軍在列寧格勒反復爭奪,最終蘇軍擊敗了圍攻的德軍,沿著德軍入侵時的路線開始反攻。從列寧格勒方向出發的蘇軍收復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其中一部分作為北線部隊,繼續向波蘭和德國本土進攻。
5月9日那一天,當里加的小學生捧著野丁香歡迎蘇軍時,女英雄伊萬諾娃·濟納達伊·康斯坦丁諾夫娜就行進在隊伍里。如今已87歲高齡的她,向《環球人物》記者講述了從列寧格勒到里加的戰斗故事——
1928年,我就出生在列寧格勒,父親是一名紅軍軍官,母親是一名坦克手。1941年,我還不到14歲時,德國人來了,父母都上了前線,只剩我和奶奶在家里。那年8月,父親被德國飛機炸死了。當時我就發誓,一定要上戰場為父親報仇。
第二年春天,我還是個少先隊員,就找了一枚共青團團徽戴在胸前,想冒充團員入伍。不過,我個子太矮,年紀又小,沒得到批準。但我告訴大人們,我非去不可。有一天,我看到一輛開往前線的裝彈藥的卡車停在路邊,就偷偷鉆了進去。卡車開到前線,士兵們卸貨時突然發現車上有個小姑娘,吃了一驚。前線的軍官本來想勸我回家,或者到兒童院干點活,但我堅持一定要到前線打德國鬼子,給父親報仇。最終,我留在了步兵團,當了通信兵。
在列寧格勒的一次戰斗中,我們的電話線被炸斷了,團長先后派了兩個戰士去接線,都犧牲了。我就說:“我個子小,容易隱蔽,派我去吧。”團長實在不忍心,可又沒有辦法,一把抱住我說:“孩子,你去吧。但你一定要記住,既要完成任務,也要活著回來!”在電話線被炸斷的地方,我找到電話線的一頭,卻怎么也找不到另一頭。找了好半天,我看見那一頭線在犧牲的戰友手里。掰開他的手時,我還能感到他的體溫……回來的路上,我看到有一名戰友身負重傷,走不了路,就把他也背了回來。
因為我的父親犧牲了,大家就叫我“步兵團的女兒”。另一次戰斗中,我和4名戰友在瞭望臺里被德國人包圍了。指揮官說:“敵人靠近了,你們什么時候開槍不用聽我的命令。但最后一顆子彈必須留給自己,我們不投降,也不當俘虜。”我那時才15歲,連男朋友都沒交過,心想如果真這么死了,真是不甘心。幸運的是,我們最后被前來增援的戰友救了出來。
還有一次,我們設置了包圍圈,在包圍圈里挖了戰壕,打算誘敵深入。戰斗開始后,我和幾名戰友故意暴露在敵人視野里,果然有20多輛德國坦克朝我們開來。等敵人進了包圍圈,我們趕緊跳進戰壕向部隊發信號,報告敵人位置。部隊很快發起進攻,打了一場勝仗。我因此受到了嘉獎。
1944年,我們打退了列寧格勒的敵人,但沒什么時間慶祝,部隊就向波羅的海方向開進。我們部隊進攻拉脫維亞,在拉脫維亞首府里加我遇到了一名空軍戰友,我們步兵團和他們空軍部隊聯合攻打里加。我們對彼此的印象很好,約定如果戰爭結束了,我們都還活著,就結婚。
1945年5月初,我們解放了拉脫維亞全境。我當時還想打進柏林呢,但上級的命令是留下駐守。不過他們空軍部隊去了柏林,我母親也開著坦克打到了柏林市區。他們都參加了在柏林的四國聯合閱兵。
后來每年5月9日,我和丈夫都會參加紅場閱兵。10年前,在勝利60周年時,我的丈夫去世了。今年,我一個人站在紅場的觀禮臺上,懷念著他和所有戰友。
奧斯維辛幸存者:
“我每天都能看到死去同伴的臉”
1945年5月9日,波蘭,奧斯維辛城,平靜之地。
他們的歡慶時刻來得更早,1945年初,蘇聯紅軍已經基本解放了波蘭。二戰期間,納粹在德國本土及占領區設立了超過1萬個各種類型的集中營,1100多萬平民和戰俘慘死其中。奧斯維辛集中營是最著名的一個。
1939年9月,德國占領波蘭,兩三個月后,納粹軍官看中了交通便利的南部小城奧斯維辛,下令建造集中營。1942年,納粹通過了“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此后,約110萬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殺害,其中90%是猶太人。這里成了“死亡工廠”。
然而,直到被蘇軍解放之前,這座集中營竟然鮮為人知。
1945年1月,蘇軍進攻奧斯維辛城。一支紅軍部隊在城外的樹林中行進,突然間眼前的樹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地圖上并未標示的一大片建筑物,而且沒有一個人影,安靜得有些詭異。蘇軍士兵滿懷疑惑,砸開了大門的鐵鎖。帶隊的蘇軍上校格羅馬茨基回憶:“我們剛進去的時候,看不到一個人。在向前沖了大約200米之后,突然幾百個穿著囚服的人哭喊著拼命向我們跑來,緊緊地抱住我們不放。一位婦女甚至拿出了她藏起來的一點糖果,硬塞進我們手里。我見過無數戰友犧牲,卻都不如這個場面讓我揪心。”
原來,蘇軍開始進攻奧斯維辛后,集中營的納粹看守紛紛撤離。被關押在集中營里的人們并不知道外面的情況,直到看見砸門而入的蘇軍身穿的并不是納粹制服,他們才知道自己得救了。7000多名幸存者成了那一歷史時刻的見證人。
今年4月26日,正當歐洲各國籌備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時,在波蘭南部古城克拉科夫,95歲的猶澤夫·帕欽斯基與世長辭。作為第一批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到戰爭結束依然奇跡般活著的人,他是“幸運的”;但他又是不幸的,終其一生都活在集中營的悲慘夢魘中。就在去世前不久,猶澤夫還接受了記者們的采訪——
1939年,德國侵占波蘭,我參加了抵抗戰斗,但被俘虜了。后來,我僥幸從戰俘營逃出來,想到法國參軍,繼續戰斗。我走到捷克斯洛伐克時被德軍抓住,又被送回波蘭的監獄。1940年6月14日是我一生也無法忘記的一天。德國監獄長把挑選出的728名犯人趕上了火車,20歲的我就在其中。
雖然我們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在火車上每個人都有座位,我還以為要被送去某個地方勞動。幾個小時后,火車到了克拉科夫,火車站的場景讓我很難受:德國人唱著、跳著、歡呼著——法國投降了!我原本還想去法國參軍,結果巴黎卻淪陷了。火車駛出克拉科夫后,再次停下來時就是奧斯維辛,不見了歡呼的人群,只有幾個兇惡的黨衛軍士兵等著我們。搜過身后,一個黨衛軍軍官大聲訓話:“告訴你們,這里不是療養院,是集中營。在這里最長可以活3個月,猶太人和牧師最多活6周。出去的路只有一條,就是焚尸房的煙囪!”
訓話結束后,我們每人拿到一張卡片,在上面填寫姓名、職業、嘴里鑲的金牙數,還有家族病史。每個人都有編號,我是121號。后來關押的人越來越多,為了便于管理,黨衛軍就把編號刺在我們身上。

奧斯維辛的幸存者大多是像我這樣第一批進來的人。原因很簡單,集中營成立之初,很多“管理崗位”空缺,黨衛軍只能在犯人里選一些。我被分配到為黨衛軍服務的美容用品店,每天從倉庫取貨,還要打掃衛生。很諷刺的是,我每天都要打掃四五次集中營大門——大門上寫著“勞動帶來自由”。除了商店,在集中營的食堂、藥店和醫院工作的犯人也有更多幸存的可能。因為這些崗位上的犯人更容易得到德國人的“尊重”,也能偷點吃的。但要特別小心,千萬不能惹惱了德國人。
后來,我得到了一個給納粹指揮官胡斯理發的工作。前任理發師是個同情犯人的德國人,偷偷地給犯人東西。黨衛軍發現后把他關進了禁閉室。我擔任臨時理發師后,胡斯比較滿意,所以就長期留任了。不過,我被禁止和黨衛軍軍官交談。替他們理發的幾年里,我不敢和他們說一句話。
1944年底,有個消息在囚犯中悄悄傳開:蘇軍離奧斯維辛越來越近了。1945年元旦過后,飛機頻繁飛過集中營上空,再后來,我們甚至隱約聽到了炮聲。大家都憧憬著離開集中營的日子,我甚至偷偷做著回家的準備。但突然有一天,我和幾十個犯人被轉押到奧地利毛特豪森集中營。那里關押過20萬人,有10萬人被迫害致死。在毛特豪森集中營,我又熬了4個月。直到5月5日,美國軍隊開進了集中營,我自由了。
我和幾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聯系上了。他們告訴我,在我們被轉押離開后不久,蘇軍解放了奧斯維辛。那天,雪下得很大,他們隱約看到遠處有很多人穿著白色的迷彩軍服。他們以為這是被納粹運來的新囚犯,所以都待在囚房里不敢動。但是等這些人走進來之后,他們看出是軍人,而且不是納粹軍人!他們興奮得像瘋子一樣跑了過去,不停地擁抱、親吻他們。蘇軍掏出身上的餅干和巧克力分給了他們,稱呼他們為“幸存者”。
后來,我讀了大學,畢業后在一座小鎮上教書,離奧斯維辛只有100公里。這幾十年,我雖然過著正常人的生活,卻始終忘不了集中營里的日子。我每天都能看到死去同伴的臉:他們被送進毒氣室時的驚恐,被饑餓和病痛折磨致死前的痛苦……這些畫面無時無刻不在我眼前浮現,怎么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