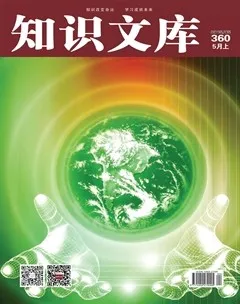歷史學家:一戰華工是無意識的歷史推動者
馬驪,法國歷史學家、漢學家,法國濱海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政治哲學史、宮廷比較史、一戰華工史。著作有《朱元璋的政權與哲學》等。2010年5月,在濱海大學主持了歐洲首次關于一戰華工的國際學術會議。2015年1月,《一戰華工在法國》中文版出版。
一戰期間,十幾萬華工懷抱“發財致富”的夢想奔赴法國與英國,為一戰出賣苦力。一戰結束后,只有幾千華工找到工作,繼續留在法國,絕大多數華工回到老家,另有一萬多人埋骨他鄉。這段歷史,不僅被歐洲人遺忘,在中國也少有人知。
作為一名華裔法國學者,馬驪研究一戰華工顯然并非完全出自個人的學術興趣。2002年,她到法國濱海大學任教,發現附近有大片的華工墓地。由此,她進入了這一學術研究領域。2010年5月,她主持了歐洲首次關于一戰華工的國際學術會議,最近出版的《一戰華工在法國》,便是這次會議的成果。
研究 華工大多懷抱“發財夢”參加一戰
新書收錄了馬驪研究華工招募及輸送的文章。1914年7月,“一戰”爆發,原先估計會速戰速決,卻變得漫長而慘烈,協約國一方的法國、英國面臨嚴重的人力短缺問題,戰線缺人,后方也急需勞力。“從1915年起,招募中國勞動力的問題已經被擺到議事日程上。”文中,馬驪寫道。
與此同時,各主要交戰國在中國占有租借地和勢力范圍,迫使中國做出選擇。1914年8月,“日本艦隊已開始出現在德國租借地膠州灣海岸之外”,鑒于時局,中國不得不放棄中立政策,最終加入協約國向德國宣戰。作為社會名流,梁啟超亦在其中奔走,主張參戰,希求在“國際上開一新紀元”。
武裝參戰的提議被否決后,“以工代兵”成為“最好的做法”。在包括教會的組織動員下,英國、法國共招募14萬華工,他們來自十多個省份,其中山東勞工備受青睞,因為身體強壯,“可以干重活”。這些人多是貧困或無地農民,且基本上是文盲,應招赴法,他們懷抱著同一個夢想—“發財致富”。提到出國時的感觸,山東勞工樊明修說:“下了太平洋,想起老爹娘;三百大洋賣了命,至死不能回家鄉。”
去法國前,有的招募方與華工簽訂了合同,條款中有包括“不得參與任何跟戰爭有關的工程建設”、“有義務保護中國勞工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等。但是,華工的雙腳一踏上法國的領土,合同就地淪為一紙空文,未被遵守;他們主要做搬運、挖戰壕、埋葬死者甚至清理炸彈的工作,艱巨而危險。“對華工實行軍事管理,如果他們犯了紀律,可能會被槍斃—不應該對工人這樣干。”馬驪感嘆。
這過程中,赴法“勤工儉學”學生對華工展開援助,同時華工對這些知識分子也產生了積極影響。正是在法國,學生們從華工身上真正了解到中國底層人物的生存狀態。“當時一般以為他們愚昧、簡單,并不是這樣,他們會抗議,會保護自己的利益,讓人看到了‘群眾’的力量”,華工影響了這些學生的政治取向,有的成為共產主義活躍分子。鄧小平、周恩來、陳毅等,曾與華工有過接觸,或者一起在工廠干過活。“新中國出于這些人之手,我覺得華工對他們的影響很大。”馬驪說。
“一戰”結束后,數千華工繼續居留法國,成為第一批中國移民,大多數選擇回到故土,有一萬多人埋骨他鄉。
走訪 回國后重操舊業集體沉默
2010年8月底,馬驪前往山東淄博,走訪華工后代,在周村—當年一戰華工的一個招工點,她的研究得到了佐證。留在法國的華工大多數做了工人,回到老家的華工,除一些人“成為工會頭子”之外,絕大多數都重操舊業,“賣燒餅或者紡織,大多又做回了農民”。他們在法國獲得的工薪,要么用來賭博玩樂,要么給了家里。“有人說,回來之后爺爺帶了很多金條,我覺得是夸張的。”馬驪說。
淄博當地事先聯系了一些華工后代,馬驪訪談了四十多家,發現一個共同點:“他們的遭遇都一樣,為家庭去法國打工,回來以后,大多數人的錢財仍然用于家庭。”與此同時,馬驪去華工后代的村子里敲門,隨機走訪,發現了細節上的差異,比如“沒有帶金條回來,沒有帶法國女人回來”,但再次證實了上述發現。
另一個共同點,則是集體的沉默,“對于在法國的經歷,只說是‘打仗啦’,喝了酒后偶爾說飛機、大炮轟轟響,至于生活、工作,他們不細說,大多時候一句不說”。馬驪認為,“這段經歷給他們造成了很大創傷。”
孫干是一戰華工的代表,去法國之前,他接受新式教育,成為一名小學教師。和其他奔赴法國的華工不同,他并非迫于生計,而是受到“教育救國”理想的驅使。“孫干在他的筆記里寫著,他覺得法國女子非常獨立,能頂‘半邊天’,在工廠能做男人的活計,包括那些技術性的活計。”馬驪說。回國后,孫干和妻子共同辦了一所女子學校。
孫干撰寫的筆記題為“歐戰華工記”,約10萬字,以親歷者的眼光記述一戰華工,是極其重要的史料,但長期湮沒于民間,直到2009年才首度內部發行。馬驪在山東走訪時,有人帶來一個孫干的筆記本,試圖賣給她。“要的是歐元,不是要人民幣,因為他知道我是從法國來的。”馬驪哈哈大笑。
除了筆記本,還有人賣湯匙、胸章等—“一看就知道是華工的用品,但我不會買”,馬驪希望政府或民間機構能夠搜集這些資料。
交鋒 并非“文明的交融”
孫干開辦的女子學校很快被叫停,不僅如此,政府還下達了禁令,嚴禁開辦女子學校。傳統的力量如夜幕一般,瞬間吞沒了這星星之火。
還有一些歸國華工產生了學習西方的愿望,并付諸實踐。張宗方自制西式抽水機、播種機,李榮坤不讓自己的三個女兒纏足,還送她們上學,甚至有人受西方社會主義影響,認為中國的土地應該公有,對父輩分給自己的田地不予接管。還有人組織了工會,試圖為工人爭取權利。
有學者認為,一戰華工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如學者、中國和“一戰”關系研究專家徐國琦稱之為“文明的交融”。“根本沒有,沒有什么中西交流,這簡直是妄想!”馬驪駁斥了這一觀點:“畢竟是一場戰爭,這沒有文明可言。”在她看來,一戰華工只是一群“小人物”,回到國內,仍然是“無聲無息的人”,很快被遺忘。
“……相對于一個歷經數千年而固化的古老生活方式來說,還遠不足以開一代風氣之先,釀成一場社會變革。所以隨著時光的流逝,歸國華工帶來的新奇與影響不能不歸于沉寂,以至于我們今天必須努力加以鉤沉,才能勉強打撈出些許碎片。”探討一戰華工的歸國境遇時,研究者張巖寫道。
“一戰”結束,華工的故事已講完,但作為一個群體,被推著登上了歷史舞臺。在巴黎和會上,14萬華工以工代兵援助英法對德戰爭,是中國作為戰勝國出席的重要因素,卻沒有享受到戰勝國應得的利益,反而成為餐桌上刀叉相加的犧牲品—德國在山東的租界被劃給了日本。國內隨后爆發“五四運動”,最初是一場愛國運動,后來發展為呼吁追求民主、科學,共產主義活躍分子參與進來,此后一發不可收。“華工在他們自己不知道的情況下,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馬驪說。
1988年,法國政府第一次為一戰華工豎立紀念碑—由華僑集資而成。英國、法國、美國、比利時包括中國的學者先后投入研究,在多場國際會議的推動下,“一戰華工”似乎漸成熱門話題。馬驪也感覺自己成為了一個自己討厭的“明星”,紀錄片導演、電影制片人紛紛找上門。
“我希望把注意力放在華工身上,他們被忘記太久了。”馬驪搖搖頭。在歷史研究之外的更廣大的范圍,遺忘仍在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