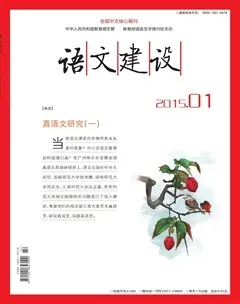也談議論文寫作怎樣去淺表化
議論文寫作訓練與發展學生思維的復雜關系曾吸引了語文界持久的探討熱情。日前,上海市延安中學白麗老師的一堂“把學生的思維引向深入”的寫作實踐課,以及鄭桂華老師據此闡發的一些操作性意見,對語文界如何改進學生的議論文寫作以促進學生思維發展,無疑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筆者深入研讀其教學案例特別是相關評價,除了對鄭老師提出的教學策略基本認同外,也對她引出第一個教學策略的問題診斷,持有不同看法,所以特撰文探討,希望能推進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
一
鄭老師的問題診斷,其實是對白老師作文講評課上一個說法的進一步發揮。[1]白老師曾就一段材料要求學生撰寫自選角度、自擬題目的議論文,該材料是:
一位名叫索克曼的基督教牧師說:“當我們是少數時,可以測試自己的勇氣;當我們是多數時,可以測試自己的寬容。”
然而,面對學生上交的作文,白老師發現不少學生作文是從中單獨抽取了“勇氣”“寬容”等詞語來擬題并展開論述的,比如《呼喚寬容》等類似的擬題,就是圍繞該詞語的一般含義寫就的文章。這當然有問題。對此,教師在隨后的講評課上通過展示學生作文審題頗有偏差的幾個實例,組織他們討論。學生認為這些作文寫得并不好,理由概括起來有三點:
沒有新意;寫偏了,沒有扣住關鍵;材料的完整意思是“當我們是多數時,可以測試自己的寬容”,而這幾個片段所講的“寬容”都不是當主人公身處“多數”時,與“多數”無關。
這些理由說得似乎很在理,但畢竟有點事后諸葛亮的味道,所以教師就讓學生回憶一下,他們當時寫這篇文章進入審題環節時,有沒有注意到“多數”“少數”這幾個關鍵詞?
學生的回答大意是:讀到了,也想過,之所以沒有寫出來,是因為“一寫就變了”。據此,教師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判斷:
(同學)心里很想寫,但就是寫不出來,或者一寫就跑題了。看來今天我們有一個發現:不少同學忽略與“勇氣”匹配的“少數”,并不是沒有看到,很可能是缺少一種“分析技術”,沒有把想到的表達出來,才造成了議論比較淺。
在對這堂課的相關評議部分,鄭老師認同白老師的看法,認為這確實只是“技術”處理問題,不宜用作文水平和能力的標準來下判斷。她還以“把該說的話說出來”作為深化議論的第一個策略。鄭老師的主要理由是,不輕易用“偏題”這樣的詞下判斷,是照顧到學生寫作時的積極心理,給學生繼續改進自己的作文提供發展機會,這是以先進的學生觀、學習觀為支撐的。這一看法我基本同意,但是,如果因此認為學生作文的偏題常常不是因為審題不清,而是“沒有把該說的話說出來”,就未必恰當,因為恰恰是對于“該”與“不該”的認識,學生有些模糊不清。既然對這一基本問題判斷不盡到位,由此她進一步提出,在寫作過程中,學生不能集中注意力,忽略了材料中一些要素,只要重點用到她所提出的幾個一般性的思考建議,就能對問題有所彌補。在我看來,這也未必能奏效。即以鄭老師提出的第一個思考點來說:
針對這則材料,我的觀點是什么,如果把材料(或題目)中那些沒有提到或被重視的詞語與我確定的關鍵詞聯系起來,我的觀點或主旨有什么變化。
其實,這樣的建議還嫌太籠統,無法解決白老師作文課上學生面臨的問題。因為從教師和學生的現場交流看,學生恰恰是發現,將材料中被學生忽略的關鍵詞例如“多數”“少數”等詞語,與其確定的關鍵詞“寬容”“勇氣”聯系起來,“一寫就變了”。正因為學生害怕這個“變”,害怕吸納了材料中的另一些詞與其習慣的思維取向會發生碰撞,才有意無意放棄了這一更具整體意義的主旨把握。
這樣,關鍵不是判斷“我的觀點或主旨”有沒有變化或者有什么變化,而是需要判斷,當變化發生后,文章究竟是扣題了還是偏題了,議論究竟是深化了還是淺化了。白老師課上說學生沒有把想到的話表達出來,而在鄭老師的評議中,直接提出“把該說的話說出來”這一建議。這樣表述,當然在邏輯上比白老師的說法更嚴密,因為并不是想到而不說的話都是該說的,但如何在該說和不該說的話之間做出區分,把學生易于忽視的重要問題揭示出來,這才是我們需要引導學生思考的。如果提出的策略確實有效,就不應該放過學生眼前的問題,把問題推到將來,只是泛泛地說“這需要在平時的寫作訓練中技術性地解決”。關注學生的思維流程,將學生思考過程中面臨的具體問題納入作文教學的策略,而不是簡單化、套路化地提出一些以不變應萬變的策略,才是先進的學生觀、學習觀的落實,也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基本哲學方法的體現。因此,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對學生作文忽略的部分加以重新審視,以揭示問題的關鍵所在。
二
就我思考所及,如果把教師提供的材料用關鍵詞提煉,那么可以大致形成這樣一種思考的層級關系,在常規與反常規的不同思考層級中,把立意逐漸引向全面和深入。見下表:
誠如白老師所言,學生審題中較常規的失誤,是抽取“寬容”或者“勇氣”作為文章主旨來展開議論,從而導致審題失之偏頗;較好的一種審題方式,是能把寬容和勇氣作為一組對比關系來思考。不過,如果嚴格按照邏輯推演,寬容和勇氣其實是構不成直接對立關系的,在提供的材料中可以得出這樣的邏輯推演:在大多數是寬容的語境中,少數者的勇氣是無法檢測的;反過來說,少數者的勇氣,也無法在寬容的環境中揭示。因此只有把寬容和勇氣置于各自不同對應的背景中,才能形成匹配,這就引出了較為全面的所處境況與心靈態度的對應關系。
我不知任教的白老師和評議的鄭老師有沒有思考過,如果學生想到的關鍵詞比較全面,而當寫下來又趨于片面時,為何絕大多數把題目寫偏或者說對材料斷章取義的學生,寫下的總是“寬容”“勇氣”等一些描述主觀態度的關鍵詞,卻較少略去“寬容”而把“多數”“少數”這些詞作為主旨性的立意寫下來呢?如果學生從審題時的所想以及到落筆時的所寫這一轉變過程發生了一些遺漏和忽視,似乎總習慣于保留部分而忽視整體,為什么大家都趨同性地保留了這部分而不是那部分呢?這種忽視的趨同性,究竟意味著他們怎樣的思維特點呢?以我之見,或許這跟學生習慣于思考一種比較具體的定性的概念有關,也是跟學生易于從人的主觀態度(這當然更容易確立主旨,更容易把概念中已明確的態度與作文立意進行對接)、從其自身而不是從他們所處的境況與前提條件中切入問題思考有相當關系。這樣,學生后來在作文講評課討論時,除開回答立意發生偏差的理由是審題時自覺地怕變化或者落筆時不自覺中發生了變化外,他們對那些審題偏頗的判斷理由也很有意思。第一條理由不是偏題的問題,而是“沒有新意”。其所謂的“沒有新意”,恰恰意味著那些作文是對自己思維習慣的固守。從教師描述作文的實際狀況看,也證明了從主觀態度本身切入問題的思考比較普遍,這正是學生的一種思維定式,或者說是思維的一種惰性。在這樣的普遍狀況下,我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同是從局部切入主旨,比如從“多數和少數”的關系中切入思考,看似沒有把握材料的基本觀點,不是一種全面的理解,但恰恰有了學生常規的思維習慣構成的語境為前提,反而更容易獲得主旨的深刻性的突破。于是,反常規的思考角度,就能從平庸的“沒有新意”的作文中脫穎而出。這種思維突破,當然有自覺與不自覺的基本差異,學生能夠確立自覺的態度,與教師的引導有很大關系。然而,我們還可以更深入一步來思考,材料舉出的兩種背景,其實都具有一種假定,既假設了人所處的不同狀況,也假設了在任何不同的狀況中,都有檢驗、表現自身正能量的機會。這樣,具體的“多數”或“少數”的境況,毋寧顯示了更具本質意義的主觀態度如何在客觀境遇中積極應對的問題。理解“當……時,可以測試……”一組句法關系的普遍適用性,就成了理解一個可以把具體對象不斷替換的深層次思維結構關系,原來只是從社會的、心理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確立主旨,就有了向哲學思維邁進的可能。
鄭老師無論是提出“把該說的說出來”的第一個思考策略,還是提出“設置一個思維起點”的第二個策略,都有把思考引入與作者自身、與社會現實這樣的主客兩方面關系的具體建議。這當然是我們展開思維的兩個著力點,作為思考的取向當然沒有問題,但對解決學生作文中已經暴露出來的特定的具體問題,特別是要從確定思維的起點中找出他們議論的去淺表化路徑,似乎還有待我們的再思考。如何確定思維的起點,本來就是一個饒有趣味的深刻問題,我雖然抱有興趣,但尚無能力做深入探討。這里僅想提出一點:當學生開始對材料思考,或者說啟動思維時,一種由學生思維定式營造的問題語境,成了最生動、最靈活的思考對象,怎樣引導學生牢牢抓準這一問題作為思維的起點來進一步深入分析,自覺反思其與材料的互動的邏輯過程,也許是議論文寫作去淺表化的一條值得嘗試的路徑。換言之,對能寫出一篇深刻作文的學生來說,思維的起點本身是待定的,是由學生自己的具體問題所引發并且據此來設定的。
參考文獻
[1]白麗.把學生的思路引向深入[J].中學語文教學,2014(9);鄭桂華.議論文寫作怎樣去淺表化[J].中學語文教學,2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