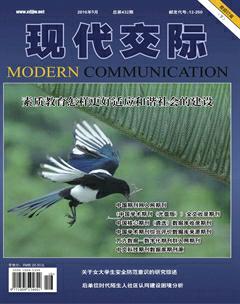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的開展及相關問題闡述
朱麗瓊
[摘要]隨著信息技術和電子期刊數據庫的開發和應用,以前傳統的期刊管理模式和服務模式已經不能被人們接受。而且,在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中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本文對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措施進行了認真的分析。
[關鍵詞]高校圖書館 期刊管理 開展
[中圖分類號]H3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0-0146-02
期刊是一種在規定時間內連續出版的印刷品,是高校圖書館中信息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高校進行教學、科研以及大學生素質教學的重要文獻,在高校的教育中是不可缺少的。因為期刊具有信息量較大、內容更新快以及報道及時的特點,所以在高校圖書館中非常受師生的歡迎。因此,做好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對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措施進行了分析。
一、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人員整體素質不足
在目前的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中,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不足,而且知識的結構比較單一,專業水平也有所欠缺。另外,大部分的工作人員都缺少圖書情報方面的基礎知識和能力以及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等,也沒有很好的外語水平,缺少較強的計算機能力,因此,他們只能做一些最基礎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展開期刊文獻信息的服務工作,以及跟不上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的步伐。因此,一定要通過各種渠道,利用切實有效的方法提高圖書館期刊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使其適應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的需要,從而確保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的良好發展。
(二)缺少健全的管理體制,服務方式單一
在高校的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中,還是采用傳統的圖書“采、編、典”的管理方式,也就是期刊的采訪、編目、流通以及典藏一系列的管理體制,但是這種只適合印刷型的文獻,而且是要在室內查閱的,不能實施外借。這種以文獻為主的管理方式充分展示出了封閉型圖書館以典藏為主的特點。隨著信息技術不斷發展,傳統的期刊管理方式已經跟不上發展的步伐,顯示了一定的滯后性,其中主要表現為服務工作和讀者需求之間出現脫離的現象。另外,印刷型的期刊服務是一種比較單一和落后的服務方式,只能用在一般情況下的閱覽,在當今的社會中已經逐漸被淘汰。隨著電子期刊的出現,讀者對期刊的要求也越來越大,傳統的期刊管理已經不能適合需求,因此,一定要進行創新和改變。[1]
(三)存在期刊征訂不合理、重復建設期刊資源的現象
在目前的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中,存在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期刊資源的配置不合理,電子期刊文獻和印刷型期刊文獻的比例不是十分協調。經過相關的統計發現,在2015年我國高校圖書館電子版的期刊要比印刷型的期刊高出十幾倍。而且,隨著各大高校的經費不斷緊張,在印刷型期刊文獻上不斷縮減費用,卻不斷加大對電子文獻的資金投入。在期刊的建設方面也存在著重復建設的現象,主要體現在印刷型期刊和電子期刊出現重復。對于全國而言,同一個城市、同一個區域的各大高校圖書館網絡期刊資源基本上是相同的,存在著非常嚴重的重復建設情況,從而導致了資源浪費的現象。
(四)讀者的需求和館藏結構之間存在矛盾
在高校的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中,因為期刊出版的數量和學科的種類都比較多,所以怎樣才能找到既符合高校發展又符合大學生興趣愛好的期刊,這是圖書館期刊管理人員最應該考慮的問題。一般情況下,高校圖書館期刊的制定都是由相關的人員擔任的,所以可能會受到工作人員的素質、個人興趣以及主觀觀念的影響,在進行期刊制定時可能會產生一定的局限性。一些高校在進行圖書館期刊制定時過于注重體現高校的專業,而忽略了學生的愛好,從而降低了學生的閱讀熱情,也減少了圖書館期刊的使用率;但是,也有一些高校只是一味的追尋學生的愛好,而忽略了圖書館期刊的專業性,導致館藏的結構不是特別完善。
二、提高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的措施
(一)提高圖書館期刊管理人員的專業水平和服務意識
對于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來說,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是管理工作順利開展的關鍵,因此,期刊管理人員應該改變傳統的管理方式,積極提高自身的專業水平和服務意識。首先,圖書館期刊管理人員應該具有高尚的品德和專業的技能,并且要具有綜合方面的素養。對于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而言,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是保障期刊管理工作的基礎,期刊管理人員一定要具有很高的職業道德和職業修養,并且要熱愛期刊管理工作,具有較強的奉獻精神,利用自身專業的技能和水平確保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2]其次,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人員還應該具有較強的服務意識,只有這樣才能給讀者帶來更好的服務。因此,高校圖書館應該積極培養管理人員的服務意識,提倡以服務為榮、以服務為樂的服務精神,遵守讀者至上的原則。管理人員不僅要主動了解讀者的愛好和需求,還應該為讀者建立信息資源的反饋體系,充分采取讀者的意見,給讀者帶來更加人性化的服務。另外,管理人員對讀者要有充足的耐心和愛心,做到平易近人、善解人意,給人們帶來可親性和可信賴性。并且還要提倡微笑服務和快樂服務,用文明的語言、和諧的態度為讀者進行服務,讓他們感受到心靈上的溫暖。
(二)建立健全的規章制度
通過長期的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實踐,我們可以充分認識到健全的規章制度在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高校的圖書館是師生獲取信息的重要場所,為了能夠充分保證服務的環境和質量,一定要建立健全的規章制度,對其進行科學合理的管理。比如,可以制定相關的行為規范,“讀者文明條例”以及“圖書室規則”等,從而來規范讀者的行為;還可以制定“圖書館管理人員規范條例”和“圖書館工作準則”,來約束圖書館期刊管理人員的行為,加強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
要想促進圖書館期刊的有效管理,一定要制定相應的管理制度,因為規章制度是圖書館實現期刊有效管理的依據和途徑。另外,并不是制定了規章制度就無所事事,還要充分學習和履行這些規章制度,從而規范管理人員和讀者的行為,使其達到有章可循、有章可依、違章必究的目的。再有,還應該針對工作人員的業績制定評價方案,對于那些愛崗敬業、貢獻大的工作人員一定要給予適當的獎勵,同時,針對那些投機取巧、不懂學習、服務態度差的工作人員也要適當地給予懲罰,從而促進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順利進行。[3]
(三)注重期刊的采購和制定,從而形成特色館藏
首先,要實現供需的合理和一致。目前,在各大高校中都有其特色專業和學科,作為高校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知識產所,圖書館一定要緊緊跟隨高校的需求和特點。具體來說,就是圖書館期刊管理人員要和高校中的領導進行合作,征求其意見,可以通過發布目錄、召開座談會的形式來確定期刊的采購和制定。而且,征求意見的表格要設計得科學合理,最好是在校園網上進行公布,方便廣大師生及時關注和填寫,從而加快期刊的采購速度。對于一些科研成果比較豐富的教師,可以與他們進行單獨的談話,積極聽取他們的意見,制定符合需求的期刊。另外,期刊結構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增訂揮著是改訂,都要和高校的領導、教師以及學生進行研究,促進他們的參與性,從而實現供需一致的目標。
其次,一定要防止出現重復浪費的情況,要充分了解各種期刊的內容,避免出現重復采購的現象,要進行詳細的咨詢,之后再進行期刊的制定。
最后,積極探索新的期刊種類,按照實際的需求進行選擇,做到與時俱進,在期刊館藏中加入新鮮的知識力量。
(四)科學管理圖書館期刊,確保期刊的流通
所謂期刊的流通,就是高校圖書館中刊物的平常流通以及管理等,這在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最能體現出期刊管理的效果。目前,我國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在發展,因此,讀者對期刊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圖書館已經不再是一個收藏期刊的地方,而是由靜態的管理變成了動態的服務,也就是積極主動地為讀者提供服務,幫助他們找到自己喜愛的期刊。實際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加快期刊的流通性,充分發揮期刊的使用率和使用效果,從而使高校圖書館期刊資源實現其真正的價值,實現知識的傳播。[4]
要想充分發揮期刊的作用,首先要實現期刊的流通性,對其進行科學的管理。第一,制定規范的期刊管理制度。這主要是針對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的管理人員而制定的,在期刊管理部門上班的人員一定要有較強的責任心,并且按照指定的規章制度進行工作。第二,合理安排圖書館的期刊,實現科學的排架。在進行高校圖書館的期刊管理時,期刊的排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讀者在進入圖書館之后,第一眼就會觀察到期刊的布局情況,而且,科學合理的布局會給讀者帶來閱讀便利。因此,期刊管理人員要按照規定的類別進行擺放,避免出現混亂的情況。第三,要制定期刊的目錄,隨時隨地為讀者提供幫助,還要及時更新期刊的種類。第四,做好期刊的宣傳工作,讓讀者能夠在第一時間了解到期刊情況,從而選擇適合自己的期刊進行閱讀。第五,經常對學生進行教育工作。通常情況下,期刊的損壞是各大高校非常頭疼的事情,因為這對期刊的制定和流通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因此,圖書館期刊管理人員對學生進行講解,使其愛護好圖書館中的期刊,做到文明閱讀。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高校的圖書館是一個對學生進行終身教育的場所,每個讀者都可以在圖書館中獲得非常珍貴的知識,而且它也是課堂上知識的延伸。而圖書館的期刊能夠為學生提供相關的信息,幫助教師更好地進行教學。隨著信息時代的不斷發展,圖書館期刊的管理工作越來越重要,因此一定要加強圖書館期刊的管理,提高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增強服務意識,建立健全的規章制度,在期刊的選購、制定等方面應該充分按照高校的特點,從而提高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的質量。
【參考文獻】
[1]鮑遠芳.我國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與服務的現狀分析[J].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12(08):193-197.
[2]王麗平,王彩虹.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之我見[J].改革與開放,2011(08):79-80.
[3]王玉蘭.淺談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工作[J].改革與開放,2010(14):70.
[4]宋雙雙.高校圖書館期刊管理研究綜述[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15(03):159-160.
責任編輯: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