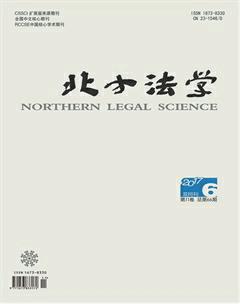道德風險真的與道德無關嗎
車亮亮
摘要:目前,學界有關道德風險這一概念的認識存在“道德論”和“非道德論”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事實上,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且均未對引發道德風險的制度問題,尤其是作為正式制度的法律制度對道德風險的影響給予足夠的重視。作為一個跨學科的概念,道德風險確實與倫理道德密切相關,但它的確不僅僅是一個倫理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倫理、經濟、法律等多領域的綜合性問題。因此,對道德風險這一概念的認知應當從跨學科的視角出發,而法倫理學作為專門研究法律和倫理道德關系的交叉性學科,可以用來分析道德風險這一概念并為其有效治理提供可行的認知路徑。
關鍵詞:道德風險倫理道德法倫理學
中圖分類號:D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7)06-0104-08
一、引論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使道德風險再次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然而,時至今日學界對道德風險這一概念仍未形成統一的認識,學者們在界定這一概念時基于各自學科立場、學術背景以及價值取向等因素的不同給出了見仁見智的解釋。在眾多有關道德風險概念的探討中,影響較大且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種觀點認為
道德風險與倫理道德密不可分,它主要是指因道德脆弱性而引發的道德失靈問題,持此觀點的主要是倫理學家;另一種觀點則認為
道德風險作為一個經濟哲學概念,并不涉及道德判斷,它主要是指市場交易中因信息不對稱引發的市場失靈問題,主要表現為隱藏信息和隱藏行動,持此觀點的主要是經濟學家
。為論述之方便,筆者將第一種觀點稱為“道德論”,相應地將第二種觀點稱為“非道德論”。基于以上兩種對道德風險的不同解釋,由此在道德風險的治理上也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路徑,持“道德論”者認為道德風險治理的根本在于
提高經濟主體的倫理道德水準以此來消除風險隱患
,而持“非道德論”者則認為道德風險治理的關鍵在于通過科學的機制設計實現激勵相容
。可以說,以上兩種對道德風險概念的解釋以及由此形成的治理路徑,基于各自不同的認知視角部分地揭示了道德風險的特質,所提治理路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然而,這種僅從倫理道德的視角來分析道德風險的認知路徑仍然有失偏頗,其中一個致命的缺陷是這一認知路徑忽視了引發道德風險的制度問題,尤其是作為正式制度的法律制度在道德風險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因為無論是激勵相容還是道德自律都只是目的,要實現這一目的還必須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規則和技術,而法律制度就是實現這一目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規則和技術。有鑒于此,筆者試圖從法倫理學法倫理學作為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之后的另一種思考,作為法學和倫理學結合的產物,它要為我們描繪的是法與道德間真實的“共生”狀態,它代表著法學在“假設”之后向現實的回歸,代表著法的理論在努力掙脫道德束縛并取得形式上的獨立后與道德的重新牽手。參見寧潔、胡旭晟:《困境及其超越:法倫理學基本問題再研究》,載《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這一全新的視角出發,來重新審視道德風險這一概念,以彌補目前學界對有關道德風險的制度問題關注之不足,從而為人們準確理解道德風險的概念并對其進行有效治理提供一種新的認知視角。
二、道德風險的緣起
道德風險(Moral Hazard)道德風險,也可翻譯為道德危險、敗德行為、道德公害或道德危機,實則表示相同的含義。在相關文獻中譯成道德風險、敗德行為的較為多見,故本文采道德風險的譯法。一詞源于海上保險,最早出現在勞合社勞合社(Lloyds),是英國最大的保險組織,總部位于英國倫敦的勞合社大樓。勞合社本身是個社團,更確切地說是一個保險市場,與紐約證券交易所相似,但只向其成員提供交易場所和有關的服務,本身并不承保業務。倫敦勞合社是從勞埃德咖啡館演變而來的,故又稱“勞埃德保險社”。1871年經議會通過法案,勞合社才正式成為一個社團組織。勞合社設計的條款和報單格式在世界保險業中有廣泛的影響,其制定的費率也是世界保險業的風向標。勞合社承保的業務包羅萬象。勞合社對保險業的發展,特別是對海上保險和再保險做出的杰出貢獻是世界公認的。參見勞合社(Lloyds)http://wwwubaocom/help/ knowledge/ln2, 2011—03—05的海上保險合同(船只和貨物保險)中,在該合同中風險被劃分為實質風險(Physical Hazard)和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其中實質風險被定義為來自海上的風險,道德風險指各種人為的風險,但其具體定義該合同并沒有給出。韓海容、張慶洪、于洋:《道德風險的經濟分析》,載《上海經濟》1998年第4期,第24頁。威克多·多爾曾指出,要精確地定義道德風險有點困難,人們經常所說的實質風險可以用費率衡量,而道德風險可以被看作保險本身的一種要素,或者和被保險人利益有關,或者和外部條件有關,它使意外事故的發生成為被保險人謀利的手段。參見梅世云:《論金融道德風險》,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頁。因此,對道德風險承保人應拒絕承保。事實上,“對19世紀的保險人而言,‘道德風險是一種不健康的、低劣的品質和利益誘惑共同作用的結果,保險人有責任將此從保險業剔除出去”。Tom Baker,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 Hazard, Texas Law Review, Vol75,1996,p240由此可見,道德風險這一概念是保險人基于對當時參與海上保險的投保人(被保險人)道德品行的質疑而提出的,表達了保險人對投保人(被保險人)不負責任行為的不滿,是對存在主觀惡意或不道德的投保人(被保險人)行為傾向的一種概括。因此,相較于實質風險,道德風險是一種無形的危險,其本義是指投保人(被保險人)的欺詐或不道德行為。1971年,著名經濟學家阿羅在《風險承擔的理論文集》(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Bearing)中指出,由于信息不對稱委托人不能對代理人進行完全的監督,當兩者利益不一致時,代理人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可能損害委托人的利益,從而提出了道德風險的經濟學概念。后來經濟學家對道德風險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從經濟學成本分擔與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對其進行了理論分析。1971年,Spence & Zeckhauser在研究保險中信息與個人行為時根據隱藏行為的時間將道德風險分為投保前的道德風險和投保后的道德風險。此后,Dionne等人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1985年阿諾特(Arnot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注意到,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導致了次優合同的產生。在以這種合同為特征的經濟中,任何兩方當事人之間合同的變化都會對社會福利產生重要影響。1991年,斯蒂格利茨(Stiglitz)和阿諾特(Arnott)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對委托代理和道德風險問題的研究表明,非市場因素會進一步加劇道德風險問題,由此得出風險與保障之間具有正相關性,即高保障的被保險人更容易因疏于防范而導致更大的危險發生。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險市場時,發現了一個道德風險的經典例證:美國一所大學學生自行車被盜比率約為10%,有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發起了一個對自行車的保險,保費為保險標的金額的15%。按常理,這幾個學生應獲得5%左右的利潤。但保險運作一段時間后,這幾個學生發現自行車被盜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之所以出現這一結果,是因為自行車投保后學生們對自行車安全的防范措施明顯減弱。在這個例子中,投保的學生由于不完全承擔自行車被盜的風險后果,因而減少了對自行車安全的防范,由此導致自行車被盜概率明顯上升,這就是道德風險。由此可見,“道德風險”指的是人們享有自己行為的收益,而將成本轉嫁給別人,從而造成他人損失的可能性。胡海鷗:《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定義考》,載《上海金融報》2003年8月5日第8版。顯然,道德風險主要發生在經濟主體獲得額外保護的情況下,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這一點相當普遍。目前,道德風險這一概念已擴展到金融學、倫理學、法學、政治學等各學科領域,其外延也日益擴大,已經從保險市場延伸到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微觀經濟分析的一個重要概念,泛指市場交易的一方難以觀測或監督到另一方的行動而導致的風險”。前引⑤,第63頁。endprint
三、道德風險的理論爭鳴
在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以“經濟人”完全理性和完全市場為基本假設,認為市場主體具有完全的認知能力和計算能力,由于他們對信息的掌握是完全的,因此在經濟活動中不存在信息不對稱、不完全和不準確的情況,自然也不存在所謂的“道德風險”。在完全信息假設之下,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市場機制能自動實現市場均衡和促進社會利益的實現,無需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僅憑市場“無形之手”就能自動實現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受古典自由放任思想和個人主義觀念的影響,傳統責任觀秉持個人責任或自己責任原則,認為個人依憑其自由選擇和完全理性能夠自行解決經濟生活中的一切問題,也能夠自行應對和化解一切風險,由此確立了“買者自慎,風險自負”的個人責任原則,以充分彰顯個人自由意志。一旦風險發生由自己解決,自己不能解決時只好自認倒霉。而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飛速發展和經濟社會化的不斷推進,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不確定因素與日俱增,個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面臨的風險程度也隨之增加,由此造成的社會經濟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甚至很多時候直接危及個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特別是在巨大的自然災害和諸如戰爭等社會災難面前,個人的力量顯得如此的渺小和不堪一擊。顯然,在巨大的“天災人禍”面前,僅靠個人的有限之力已無法解決其生存問題,更不用說“兼濟天下”、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了。在此背景下,傳統個人責任原則的弊端日益暴露,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分工高度精細和專業化發展的要求,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阻礙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反動力量。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和各種社會問題的日益暴露迫使人們反思傳統的個人責任原則,由此催生了風險共擔的社會責任原則,以分散風險和應對個人所無法解決的各種重大風險和社會問題。社會責任原則作為對傳統個人責任原則的揚棄,是對個人責任原則缺陷的彌補,是基于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和不完全市場假設而提出的一種風險應對原則。因為個人在面對諸如自然災害、戰爭、生命危險等重大不測事件之時,其應對能力十分有限,以致不得不求助于社會大眾的集體協作和團結互助。這種對社會而言的小概率事件,對個人的打擊和影響是極其嚴重的。換言之,對個人而言無法承受的風險損失,一旦分散到每個社會成員身上,對他們只是很小的損失,甚至對他們的生活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因此,倘若將個人因風險事件所遭遇的損失分攤到整個社會,用社會共同體的力量來化解個人風險,這對每一個社會成員而言是以很小的代價換取一個很大的保障。正是在此觀念的影響下,社會責任原則逐漸形成,并進一步發展出風險的社會分擔機制,保險制度由此應運而生。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保險制度是人們為應對社會經濟生活中日益增多的風險事件所作的一種制度創新,是社會責任原則在保險領域的制度體現。誠如有學者所言:“保險之旨趣,乃根據危險分散之法則,即‘相互性之原理,將集中于少數人之危險,由多數人分擔其損失,寓有‘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之至意,可謂人類社會以協同協力為基礎之各種社會經濟制度中,最為普遍而有效的一種制度。”陳云中:《保險學》,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頁。
隨著海上保險業務的開展和保險事故的頻繁發生,19世紀的保險家創造了“道德風險”這一概念,用來指稱投保人(被保險人)的欺詐或不道德行為。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對道德風險這一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道德風險被用來描述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可能導致的保險市場的低效或者經濟效率的下降,而不再指欺詐或不道德行為。在經濟學中,道德風險是指因降低了對采取防范措施或防止損失擴大的行為的激勵而導致保險損失的一種傾向。參見Kenneth J Arrow,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AM Econ REV Vol53, 1963,p941這一概念自提出以來,因其界定的模糊不清和使用范圍的不斷擴大而備受爭議。有學者指出,道德風險是法經濟學分析框架內最重要而又最不好理解的概念之一,也是用來分析福利改革、侵權責任、勞工賠償、健康政策以及其他社會責任問題的工具之一。前引⑥, p238一位美國作家指出:“道德風險的含義是,如果你容忍(慫恿)不軌行為的發生,那么你就是在助紂為虐。”前引④,第238頁。道德風險的最大危害體現在各種抑制成功而激勵失敗的政策上,因此,為了減少其社會危害經濟主體應減少對政府的依賴,并切實對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來。支持道德風險理論的經濟學家認為,保險的存在降低了投保人的成本投入和防范風險的努力,使保險人承擔了本不該承擔的超越其預期的利益損失。顯然,道德風險的存在有鼓勵人們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之嫌,反倒使經濟主體從其風險行為中獲益,不利于“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個人責任原則的落實和“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功能的充分發揮。而反對道德風險理論的學者則認為,道德風險從來都沒有成為一個直觀的、純粹的邏輯概念或科學概念,對19世紀發明這個術語的保險人而言,它是一種對非理性行為的表述。前引④,第239頁。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也認為,道德風險是“套套邏輯”,只是描述現象而并不能用來解釋現象,由此認為所謂的道德風險模型“一錢不值”。而“對道德風險的傳統經濟解釋夸大了現實中保險的激勵作用,而同時又低估了保險所帶來的社會利益。因此,道德風險經濟學雖然體系嚴密,但是錯誤地低估了保護受傷害者、病人和窮人的各種努力,以致免除了人們為促進身陷困境者境況的改善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前引④,第240頁。諾斯在1981年指出,促進經濟增長的經濟組織擅長于將收益內部化而將成本外部化,由此提高私人回報率,通過向社會其他群體強加成本而取得富有成效的經濟活動。由此可見,“道德風險已經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基本因素,甚至可以說現代資本主義正是在道德風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盡管在具體制度上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如有限責任、最后貸款人制度、產業政策等),但是基本的原理是相同的,即風險的社會化。因此,因為僅看到風險社會化的成本而忽視其潛在收益進而蔑視它,這實在是一種誤導。一旦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就很容易理解對當前亞洲金融危機道德風險的討論是多么具有誤導性”。endprint
HA-JOON CHANG, the Hazard of Moral Hazard: Untangling the Asian Crisis, World Development, Vol28,No4,2000,pp777—788
顯然,在道德風險經濟學家的眼中,社會責任似乎成了個人不負責任的委婉說法,而這顯然是對社會責任的一種嚴重誤解。過分強調道德風險的危害可能導致人們對部分需要社會關愛的特殊群體,如不幸患病的人、生活無著落者、因工受傷者利益的忽視,并可能造成社會成員對社會責任的放棄。因此,至少應當將他們的利益和需要放在與普通大眾同等重要的位置。否則,可能導致“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四處橫行,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兩極分化,進而破壞社會公正和人類團結,使人類倒退到蒙昧的野蠻時代,而這是每一個有良知的文明人都不愿看到的局面。顯然,保險制度帶給人類的好處遠比它對人類文明的負面影響要大得多,這一點只需看一看目前世界各國日益龐大的健康保險市場即可得到證明。健康保險只能表明我們看醫生更加頻繁,而并不意味著疾病的增加,因為沒有誰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賭注來換取那“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臭銅爛鐵”。在一個高度強調生命價值的社會,這一點尤其重要。人們更加頻繁地就醫,這表明至少他們有這方面的現實需求而非有意浪費社會醫療資源,與個人遭受生命危險的損失相比,這點損失是值得的,也是微不足道的。而道德風險經濟學所能告訴我們的僅僅是因為防范力量的缺失,健康保險增加人們的醫療費用支出或者增加了因身體康復而休假等活動的頻率。前引④,第242頁。但是,它并不能告訴我們這種防范力量是否存在以及在很多情況下增加醫療或其他服務的消耗是否值得。它忽視了保險帶給社會的更大利益,即經濟學家所說的“正外部性”的存在。簡言之,不管意圖多么美好,道德風險經濟學致力于使我們相信社會責任不是一件好事。反對社會責任的道德風險存在四大系統性錯誤:即將保險與再分配劃等號;假設金錢可以補償所有損害并認為投保人是可控的;忽視了制度對保險激勵的制約;忽視了正外部性的存在。前引④,第242頁。然而,保險理念與實踐界定了一個社會核心的特殊權利和各種責任。在此意義上,保險制度成為一部重要的憲法,其通過界定個人責任與社會責任的界限而有效運作。
前引④,第291頁。
綜上所述,不管人們是否認同“道德風險”這一概念,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道德風險已經引起了整個學界的廣泛關注,并形成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們重新認識社會責任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使我們清醒地看到不管是個人責任還是社會責任原則各有其局限性,它們有著各自的優勢、缺陷及其作用空間。可以說,道德風險的重大意義不在于表明保險會產生人們不愿看到的結果(這是當時人們的普遍看法),而在于對人們所竭力避免的結果進行有效的控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保險人需要做兩件事:一是拒絕承保“道德風險”,即拒絕為品質低劣者承保;二是設計出一種防范“道德風險”的保險合同,即避免保險被用心險惡之人所利用或者誘使好人干壞事。前引④,第240—241頁。總之,這些努力有助于趕走保險交易中不道德的幽靈,并為19世紀后期保險向大眾消費的轉變創造了條件。因此,筆者認為對待道德風險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在個人責任和社會責任原則的沖突中求得平衡,通過制度創新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與團結,既有效防范和應對個人所無法解決的重大風險問題,又不至于降低個人責任對人類行為的約束,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和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
四、道德風險概念的法倫理學解釋
從上文對道德風險緣起和理論爭鳴的分析中,不難發現試圖從經濟學或倫理學單一的學科視野出發,人為地將道德風險與倫理道德對立起來,并不能有效解決道德風險概念的科學界定和道德風險的治理問題。道德風險作為一個橫跨經濟學、倫理學、法學等多學科的概念,需要從一種新的認知視角出發對其進行重新解讀,在此基礎上尋求道德風險治理的可行路徑。而法倫理學作為法學和倫理學的交叉、邊緣學科,既可以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對道德風險理論進行道德批判,更重要的是還能夠從法律的角度探討引發道德風險的制度成因,從而為道德風險的有效治理提供可行的路徑、規則和技術,這也符合現代科學視域融合的發展趨勢。因此,對道德風險概念的法倫理學解釋,能夠為人們深入理解這一概念并對其進行有效治理提供一種新的認知視角。
事實上,作為一個經濟哲學概念,道德風險雖不等同于道德敗壞,但是與道德敗壞有著很大的關系。前者是一種實證描述,而后者是一種價值判斷。盧現祥:《外國“道德風險”理論》,載《經濟學動態》1996年第8期。因此,對道德風險這一概念的解釋怎么也繞不過法倫理學這一分析視角。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也不排除其偶爾有“偷懶”、“搭便車”的動機和行為,這即是經濟學家通常所說的“道德風險”。這一點亞當·斯密早在《國富論》中就有清醒的認識,他說:“要想股份公司董事們監視錢財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員那樣用意周到,那是很難做到的。有如富家管事一樣,他們往往設想,著意小節,殊非主人的光榮,一切小的計算,因此就拋置不顧了。這樣,疏忽和浪費,常為股份公司業務經營上多少難免的弊竇。”[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303頁。由于這些公司的董事們管理的是別人的錢財,基于人性的弱點其很難做到像對待自己的錢財那樣盡心盡力,于是疏忽和浪費在所難免。一般而言,“道德風險存在于下列情況:由于不確定性和不完全的、或有限制的合同使負有責任的經濟行為者不能承擔全部損失(或利益),因而他們不承受其行動的全部后果,同樣地,也不享受其行動的所有好處”。[英]約翰·伊特維爾等:《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2卷),劉登翰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88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約翰·林捷瑞恩等人將道德風險定義為:“當人們將不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全部后果時變得不太謹慎的行為傾向。”[美]約翰·林捷瑞恩、吉連·加西亞、馬修·I薩爾:《銀行穩健經營與宏觀經濟政策》,潘康等譯,中國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頁。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認為,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是導致信息市場失靈的兩大重要因素,正如他所指出:“當保險減小了個人躲避和防止風險的動力,從而扭曲了損失的原本概率時,便會發生道德風險問題。”參見[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蕭琛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頁。因此,道德風險會造成市場扭曲,導致市場失靈,進而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在保險學中,道德風險這一概念有廣狹二義。廣義的道德危險,包括積極的道德危險與消極的道德危險,而狹義的道德危險僅指積極的道德危險。所謂積極的道德危險,即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為詐取保險金而故意促使危險發生的種種行為或企圖。前引⑨,第66頁。如火災保險中的故意縱火、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死亡或傷殘等,被保險人積極追求此等危險的發生。消極的道德危險,又稱心理危險(morale hazard),指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因有保險而怠于保護或疏于施救被保險標的而造成或擴大的危險。前引⑨,第66頁。目前,道德風險問題已不局限于保險業,凡涉及到契約或合同的其他經濟領域都存在道德風險問題。endprint
常言道,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是法律的基礎。可以說,沒有任何一種法律可以脫離倫理道德的支撐而發揮作用,相反倫理道德是法的正當性的重要源泉。真正的法治不是以道德代替法律,而是將道德的力量灌注在法律人的精神氣質中,從而使他們成為公平正義的守護神。參見孫笑俠:《法律倫理的特殊性》,載《人民日報》2007年7月16日。法倫理學作為專門研究法律與道德關系的學問,主要以法和倫理道德的關系為研究對象,旨在深入探討法律的道德基礎,對現有的法律制度進行道德批判,解決現代社會發展中新出現挑戰現有倫理道德秩序的法律難題。相關論述,參見曹剛:《法倫理學如何可能:法倫理學的屬性、使命和方法》,載《求索》2004年第5期;前引①寧潔、胡旭晟文。概而言之,法倫理學的分析視角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法律的倫理道德基礎;二是法律的倫理道德批判;三是法律與倫理道德沖突的化解;四是法律人職業倫理的重塑。因此,對道德風險概念的法倫理學解釋也可以從以上四個方面來展開。首先,對道德風險這一概念的界定,既要尊重其歷史源流和本來含義,又要考慮如何對其進行有效治理的問題。從前文對道德風險概念緣起的分析中,不難發現它的本來含義是指涉投保人(被保險人)的欺詐或不道德行為,而這首先是一個倫理道德的問題,因為一個嚴守倫理準則和道德自律的人不會因為利益的誘惑而舍利忘義,甚至不惜踐踏法律、危害社會;然后才是一個需要法律解決的問題,因此從道德風險有效治理的角度看,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設計法律規則的時候首先應當為經濟主體確立倫理責任,在倫理責任和道德準則的指導下再制定具體的行為規則和風險防范措施,從而為相關規則的有效實施奠定倫理道德基礎。其次,道德風險這一概念的核心權利義務的不一致、風險與責任的不匹配以及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亟需通過對現有風險治理規則的倫理道德批判來予以改進。以法倫理學之視角來分析,道德風險的有效治理必須遵循權利義務相一致、風險與責任相匹配以及權力與責任相對等原則,經濟主體在從事經濟活動時不得以他人、國家和社會利益為代價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再次,道德風險這一表述事實上也存在模糊法律與道德界限的缺陷,因此如何通過法倫理學的分析來彌補這一缺陷,化解道德風險治理中法律與道德的沖突,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總體而言,這一難題可以通過倫理入法、過程控制、本身違法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等規則的引入來予以化解。倫理入法是通過將社會廣泛認可和自發形成的倫理準則納入現有法律體系,從而為相關規則的有效實施和解釋提供基本準則,而且在確無相關規則約束時也可用其直接判案。過程控制是通過對經濟主體經濟活動的程序設定和全程監控,將那些有形的和苗頭性的風險隱患徹底消滅在萌芽狀態,從根本上減少道德風險事件的發生。本身違法原則是反壟斷法適用的一個重要原則,“它是指法院在司法實踐中根據市場結構或行為本身來判斷是否違法,而無需考慮該行為對市場造成實質性的損害”。李昌麒主編:《經濟法學》,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頁。這一原則對遭受壟斷行為的市場主體來說非常有利,案件審理機關不必對案件作大量的調研,可以根據行為本身就認定其違法,從而給壟斷者以極大的震懾力。而道德風險行為由于其高度的隱蔽性和調查取證的困難,很難通過常規的法律原則來對其進行有效的懲治,因此可以考慮引入該原則來解決此類案件的裁判問題。無過錯責任原則,是指行為人對特定損害之發生縱無過失,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只要其行為在客觀上造成了危害后果,而不論其主觀上是否有過錯均應承擔賠償責任。將該原則引入道德風險的治理中,能夠防止行為人以主觀上無過錯為由而免除其損害賠償責任,從而改變道德風險行為受害人在權利救濟中的不利地位。最后,對道德風險概念的法倫理學分析,有利于重塑法律人的職業倫理。對一個法律人而言,客觀公平、公正無私、最大限度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是其基本的倫理責任和職業道德。從倫理道德的角度看,道德風險行為不僅具有法律上的可責難性,而且也違背了經濟主體“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倫理秩序,破壞了仁愛、公正的倫理準則和平等互利、公平交易的商業道德。而任由這樣的行為不斷發生,不僅會破壞法律的道德基礎,還會導致法律與道德關系的緊張,從而使倫理道德失去對法律制度的批判能力。一旦這種趨勢蔓延開來,也會嚴重腐蝕法律人的倫理責任和職業道德,從而在全社會形成極壞的示范效應,最終造成整個社會的倫理缺失和道德淪喪。
五、結語
總之,從法倫理學的視角觀之,要想給道德風險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一要尊重歷史,不能偏離它的本來含義,如前文所述其本意是指“欺詐或不道德行為”,這一點繞不過去;二要照顧現實,考慮道德風險概念的現代發展,特別是要積極借鑒經濟學關于道德風險的研究成果;三要考慮概念本身對其治理的影響,通過科學界定道德風險的概念,從而為其有效治理提供可行的路徑。遵循上述原則,筆者認為“道德風險”是指經濟主體在從事經濟活動的過程中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基本的經濟倫理和商業道德于不顧,以致可能作出損害他人、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簡言之,道德風險是一種典型的“見利忘義”“損人利己”行為。該定義既指出了道德風險的本質特征——非道德性(不道德性)和損人利己性,可謂是“尊重歷史”的表現,又指出道德風險行為的危害后果——損害他人、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這是基于對經濟活動的現實考慮所作的概括。同時,這一概念還表明道德風險的治理需要從經濟主體的行為入手,以科學的法律制度安排為核心,通過法律、道德、經濟等手段的綜合運用,最終實現對道德風險的有效治理。
Does the Moral Hazard really has nothing with Morality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Ethics
CHE Liang-liang
Abstract:Currently there are two opposing views on the concept of moral hazard in academic circles,namely relevant to ethic and morality and irrelevant to ethic and morality. In fact, both arguments are biased for they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institutional issues which leading to moral hazard, especially to the legal system as a formal system affecting to moral hazard. As a cross-disciplinary concept, moral hazard is indeed closely related to ethics, but not just an ethical and moral issue, it involves comprehensive ethical, economic, legal and other elements. Therefore, the cog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ral hazard should be given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as a specialized study of the legal and ethical cross-disciplinary relationship subject, legal ethics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moral hazard concept and further provide a viable and cognitive path for effective governance.
Key words:moral hazardethic and moralitylegal ethics
2017年第6期哈特與德沃金法理學中的維特根斯坦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邊沁法理學的人性論基礎研究”(15FXC053)的成果之一。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杜宴林教授、河南大學法學院鄒益民博士和獨立學者韓祥波博士都曾提出甚具價值的修改意見;倫敦大學邊沁研究中心主任斯科菲爾德教授對筆者指導最多,并基于部分英文稿指出很多錯誤。在此,一并致射。
[作者簡介]張延祥,河北經貿大學法學院教授,河北經貿大學法哲學研究中心與龍圖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法學博士。
①參見Nicola Lacey, A Life of HLA Hart: The Nightmare and the Noble Dre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