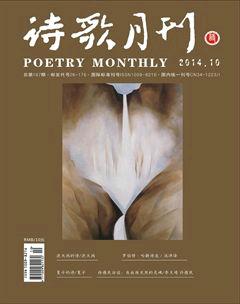沈天鴻詩學解析
沈天鴻的詩歌創作是與朦朧詩的崛起相伴的。他的詩有著強烈的現代性。《黑鴉》可以看作是對現代人生存和現代詩自身的存在本相、精神特質與本體追求的一種詩性把握與呈現: “到處可見的烏鴉,比這個夜晚/要稍白一些/這就是我們不可多得的/幸福,從它們的翅膀/傾瀉而下/陰郁的聲音。月光在水面/和天空之間跳躍/烏鴉也是如此,但它是最終的/極限的顏色,活著并非抒情/……我回頭看見/恐懼與幸福同義∥人接近烏鴉一直有個限度/才逾越/烏鴉已經飛走。
名篇《秋水》寫出了他對人生與自然的諸多思索:“我總說:秋水在遠方/總是忘了/這句話就是秋水∥我說這句話時正是夏季/這句話一出口/秋水就淹沒了/我的腳背∥站在秋水里我總說:/秋水在遠方/日子,就這么過去。”詩人通過秋水,照見自身的生存狀態,對生活中一切美好而又極易失去的事物和人進行了深刻觀照,并置身于對這個美好的事物的不懈追求之途,進而在恬淡中步入澄明之境。這首詩看似簡潔卻飽含著復雜的意蘊,具有多種閱讀的可能性,首先秋水這個中心意象即具有多重隱喻,它既象征著時間、愛情和美好事物,也喻示著一種沉靜、清澈、空茫、幽遠、澄明的境界,在藝術上,詩人化實為虛,化虛為實,虛實相生,回環往復,一詠三嘆。同時,悖論性循環也使得詩歌結構具有強烈的張力。
一直以來,沈天鴻都秉持著詩的理性思維的詩歌理念,在《還鄉》中,他寫道: “我平靜地讓草割傷我的腳/來看這些/黑暗中的我的親戚。”這是理性回歸的精神指向,靈魂高度自由的空間象征。而在此之下,那些必須忍受的事物,它們所具有的黑暗中的不安、深思、驚恐,完全統一于理性精神的徹悟中。詩中的故鄉,除了人類原鄉這一內涵之外,還指代人生終極的歸宿,因此,這首詩所達到的高度,顯然更勝于普通意義上的歸鄉情懷了。在《沉重的紀念:2008汶川地震》中,詩人沒停留在表層的描述上,而是深入人性與靈魂,對生與死進行了拷問: “還有誰敢活下去?當大地/變得恐怖,將人蹂躪?/———活下去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克服多少次死亡。”可以說,詩人極其冷靜地對這場民族大災難做了理性的闡發,他認為在災難面前只有保持活著的人性,才能讓災難成為一種永久的記憶。
對理性精神的推崇必定會帶來詩歌濃厚的哲學意味,這是沈天鴻對社會與生活不斷思考的結果,在《悖論》中他說: “我夢見我兩次/涉過同一條河流。”顯然,這是一個經典的哲學命題。而詩人告訴我們的是:“在不同的空間里.卻在/完全相同的時間里”。《深秋的果園》則引發出詩人對空間與時間的思考:“一個人站在樹下/沉郁地默想著所有不在此地的/果實/它們輕輕震顫,仿佛飛翔/經過思想和思想中的反思想/使空間和時間改變了質量。”
與在外漂泊的其他詩人一樣,沈天鴻在詩歌里充滿了對故鄉的思念、對童年生活的溫馨回憶,家鄉的一草一木都激發了他無限的詩情。在《在鄉下》中,詩人就羅列了晚上、暮色、小雨、蘑菇、泥點、劣質卷煙、燈等等,一系列與鄉村生活有關的場景與道具組成了一首韻味十足的鄉村牧歌:“點上燈,一些東西立刻就/真實卻又陌生,認識它們/要冒一點意外的危險”,而《夜間的老水車》又讓詩人回到了難忘的童年時代:“路途遙遠,老水車/和所有更深地埋在黑暗中的/東西/都住在水的外面。”詩歌創作之外,沈天鴻在詩歌理論上的成就也更顯光彩,他主張將深厚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與敏銳而深刻的反思、追問的現代詩歌精神進行有力的結合。他不僅主張努力從中國古典詩歌中汲取營養,更強調現代詩的形式和技巧的探索。他認為:“詩的形式是詩得以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沒有詩的形式,就沒有詩”、“有沒有本體,什么是本體,這是詩學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焦點所在的一個問題,詩學的其他問題都由它派生,一切分歧也由此產生”。此外,沈天鴻還是中國文藝批評界最早對后現代文學現象進行發現和研究的批評家之一。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就寫作了《中國后現代主義詩歌及其批判》一文,對中國后現代主義詩歌現象予以了清晰而理性的分析,并就這種思潮對中國新詩的影響進行了獨到的闡釋。而直到好幾年之后理論界才逐漸出現“后現代”熱潮。可以說,沈天鴻身上不僅散發著詩人的儒雅,而且深具一位學者的理論素養、敏銳觀察力和思辨力。
【節選自《安徽文學史》第3卷(現當代)第七編第五章。《安徽文學史》,唐先田、陳友冰主編。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題目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