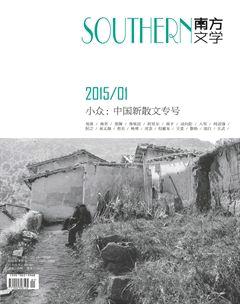老蘇(《天下農(nóng)人》選章)
魯順民
二月二,龍?zhí)ь^。春氣萌動(dòng),嵐山里的風(fēng)卻還冷。風(fēng)非常之細(xì),鋒利如剃刀,仔仔細(xì)細(xì)真心實(shí)意在臉上刮過(guò),能起一層皮的。由岢嵐縣到太原,有一條近道,取道嵐縣,直上高速可回太原。風(fēng)冷,且硬,車子行在路上,明顯感到被風(fēng)呼呼搖撼著,不敢開太快。遠(yuǎn)處的山巒頂端,積雪皚皚,哪里有半點(diǎn)春天的意思?
當(dāng)年,也是這個(gè)季節(jié),毛澤東和周恩來(lái)從中共晉綏分局翻過(guò)燒炭山,在這里停居一晚。晚上會(huì)見(jiàn)當(dāng)?shù)仡I(lǐng)導(dǎo),手書給地方上留下一句話:岢嵐是個(gè)好地方!從此,縣里頭總拿這個(gè)話說(shuō)事,宣傳。
這可能跟當(dāng)年毛澤東的心情有關(guān)系,西邊廂才擺脫胡宗南,東邊廂就布開一局大棋要下,心情不好都不行。但要在這個(gè)時(shí)候說(shuō)腳下是塊好地方,除了不拂主人盛情,再找不見(jiàn)其他更合適的理由。若不然,就是說(shuō)瞎話。
這樣,迎著拂拂而動(dòng)的寒風(fēng),由岢嵐到嵐縣。若不是貪這條近道走,不會(huì)知道老蘇的消息。
也是緣分。到嵐縣,正好中午,同學(xué)領(lǐng)著去吃飯,忽然想起老蘇,就打他手機(jī),都關(guān)著。老蘇有兩個(gè)號(hào),一為太原,一為嵐縣,打哪個(gè)都不通。同學(xué)說(shuō):你在叫老蘇?
我說(shuō)是呀!他知道,在嵐縣這個(gè)地方,除了他,就是一個(gè)老蘇是朋友了。同學(xué)眉頭一皺:“哎呀,哦知道你就叫老蘇呀,你不早來(lái)幾天?”
我說(shuō):怎么啦?
他說(shuō):早來(lái)幾天就可以給他燒張紙哩!剛埋了!
一時(shí)錯(cuò)愕,不知道說(shuō)什么。太過(guò)明白了,老蘇剛剛?cè)ナ馈U媸菬o(wú)常,無(wú)常得令人無(wú)語(yǔ)。沒(méi)有原因,沒(méi)有過(guò)渡,一個(gè)結(jié)果就這樣直白地捅在面前。同學(xué)看我錯(cuò)愕,哈哈笑:人生無(wú)常,好好活著,你看這老蘇,就這么丟下幾億身家走了。赤條條來(lái),赤條條去。
老蘇是一個(gè)煤老板,是那種在山西各縣都能找得到的煤老板。可和我們打交道,并不是因?yàn)樗倪@個(gè)身份。前些年,為補(bǔ)貼刊物,曾幫人出過(guò)書,老蘇就在我們這里出過(guò)一本詩(shī)集。清樣出來(lái),老蘇前來(lái)首校,大家發(fā)現(xiàn),這個(gè)人比他的詩(shī)更加精彩。
正因?yàn)檫@種精彩,我曾經(jīng)隨他到嵐縣為他做過(guò)一個(gè)口述。他的經(jīng)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至少山西許多農(nóng)民企業(yè)家在一九七九年之后三十年走過(guò)的人生軌跡,非常有代表性。這個(gè)口述讓老蘇非常滿意,看見(jiàn)雜志發(fā)出來(lái),說(shuō):好狗日的,沒(méi)見(jiàn)過(guò)文章還可以這么寫!可給咱鬧了個(gè)好,都是咱自家說(shuō)下的話,都是咱自家想說(shuō)的話嘛!
沒(méi)過(guò)多久,他小兒子成婚,老蘇燒包一下子買了幾百冊(cè)雜志當(dāng)作婚宴回禮送給參加婚禮的客人。
他的詩(shī)倒未必合通常意義上的詩(shī)歌體例,本來(lái)一個(gè)沒(méi)有經(jīng)過(guò)任何文學(xué)訓(xùn)練的人,你讓他怎么去詩(shī)?說(shuō)他的詩(shī)是順口溜也好,是快板書也好,怎么都行。但不能說(shuō)不是詩(shī)。分行,押韻,偶爾會(huì)冒出一句讓你怦然心動(dòng)準(zhǔn)確異常或者趣味十足的句子,還不夠?這些句子,無(wú)一例外都在寫他自己的心情,自己的經(jīng)歷,自己的回憶,還不夠?
這么些年來(lái),他對(duì)這種表達(dá)方式的迷戀與依賴到了令人發(fā)指讓人魂飛魄散的地步。編他書的時(shí)候,就奇怪他哪來(lái)這么大的雅興寫那么多詩(shī),這是需要時(shí)間和精力的,當(dāng)然也需要場(chǎng)合。一個(gè)鄉(xiāng)村粗鄙不文的煤老板,一個(gè)山溝里喧囂的煤礦,無(wú)論如何沒(méi)有這樣的條件。那一次他讓我到他礦上看一看,從抽屜里捧出一摞子紙,煙盒,過(guò)期記賬冊(cè),用廢了的月份牌,還有在街上隨手撿回來(lái)的傳單、廣告頁(yè),甚至還有拆開來(lái)的包裝盒,洋洋大觀。說(shuō)洋洋大觀的并不是這些東西的材質(zhì),而是,這些單張紙片上寫的都是詩(shī),有的成篇,有的就是兩句。老蘇說(shuō),他不抽煙,不喝酒,別人抽剩了空煙盒,就撿起來(lái)熨展寫字。這是年輕時(shí)候養(yǎng)下的毛病,改不了。
老蘇在縣里是一個(gè)名人了,大家都說(shuō)他有錢。因?yàn)榇蠹艺f(shuō)他有錢,所以更加有名。進(jìn)政協(xié),選人大,他很在意一輩子攢下的那些獎(jiǎng)狀,從少年時(shí)期的畢業(yè)證,到年輕參加工作后的先進(jìn)工作者證書,都保存得那么好,用繩子捆著放在柜子里,若推開,能把一副炕都擺滿。我知道,這些獎(jiǎng)狀與證書,大半因?yàn)樗拿旱V。我到他煤礦的時(shí)候,正值全省性地方煤礦整頓,全面停產(chǎn)。但在辦公室看到許多工作人員,不是這個(gè)局退下來(lái)的局長(zhǎng),就是那個(gè)鄉(xiāng)鎮(zhèn)退下來(lái)的書記,就連給他開車的師傅,都是若干任前縣委書記的司機(jī)。
那一次順腳搭他的車回太原,途中接了一個(gè)電話。看樣子本不想接,但還是接了。村里一個(gè)人,得了癌癥,在太原治病時(shí)他給拿了八九萬(wàn),但是八九萬(wàn)沒(méi)救住人的命,很快就去世了。打電話的是那個(gè)人的兒子,說(shuō)沒(méi)錢埋人,請(qǐng)他再出點(diǎn)錢。他說(shuō):你看看,八竿子打不著個(gè)兄弟,一口一個(gè)叔叔伯伯叫,病了咱管,死了還得咱管哩。
其實(shí),他口袋里已經(jīng)裝好兩萬(wàn)塊準(zhǔn)備順路送回村的。但在電話里他說(shuō):有一萬(wàn)夠了嗎?
那頭說(shuō):夠了。
扣了電話,老蘇心花怒放,好像平白無(wú)故撿了一萬(wàn)塊錢那樣高興。他一個(gè)勁兒說(shuō):省下就是掙下的嘛,省下就是掙下的嘛。
他永遠(yuǎn)會(huì)自己給自己找臺(tái)階下。
這個(gè)全縣有名的有錢人,成天纏絞在一堆什么樣的事務(wù)中間,可想而知了。村里人、股東、縣里市里省里的方方面面他都得應(yīng)付。看著眼前一堆材質(zhì)不同的紙片上記述那些靈光一閃寫下的所謂詩(shī)句,我想,詩(shī)歌對(duì)他而言,一定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緩釋情緒的途徑與方式。他在那里自言自語(yǔ),在那里自我緩釋,在那里為自己找到理由,在那里完成一種虛擬的身份轉(zhuǎn)換,或者,在那里他找到了一個(gè)純精神性的出口。這種方式周圍的人肯定不大理解,有些甚至不大能讀懂,他悄悄告訴我說(shuō),哪一句詩(shī)其實(shí)他是想說(shuō)個(gè)甚來(lái),后來(lái)寫出來(lái)不這樣說(shuō),偏那樣說(shuō),不散漫成句子,而寫成整齊的詩(shī)行,別人看不出來(lái)。別人不理解,不懂,恰恰是他最得意的地方。就像一個(gè)小孩子跟小朋友玩捉迷藏,他藏起來(lái),眼看著對(duì)手從眼前經(jīng)過(guò),又經(jīng)過(guò),一次次沒(méi)有將他找到,那樣的得意。
在老蘇,詩(shī)歌絕不是裝飾生活的一個(gè)文體,而實(shí)實(shí)在在是一件十分趁手的工具。
從大前年開始好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老蘇等待著煤礦整合,那是一場(chǎng)非常漫長(zhǎng)的等待,一直等到現(xiàn)在還沒(méi)有結(jié)果。將近兩年,老蘇很少來(lái)太原了,可他經(jīng)常突然冷不防就打過(guò)電話來(lái),說(shuō)他想了兩句什么好句子。或者發(fā)過(guò)短信來(lái),是一首完整的詩(shī)。他說(shuō),他現(xiàn)在寫的詩(shī),又夠出一本子了。
他說(shuō)書,是一本子書。
開始我知道,他陷入了無(wú)休止的利益紛爭(zhēng)中間。因?yàn)槊旱V幾經(jīng)技改,前些年不得不引入清徐一家企業(yè),人家一個(gè)子拿走一多半股份,這讓村里人很不滿意,尤其是當(dāng)初跟他入股的那些股東們。當(dāng)年,他拉人入股時(shí),最多股份不過(guò)二百多塊錢,現(xiàn)在當(dāng)然是一個(gè)非常龐大的數(shù)字。股東們認(rèn)為,引入清徐的企業(yè)入股,是他當(dāng)漢奸的結(jié)果,所以將他起訴到法院。他當(dāng)這事也寫成詩(shī),其中有一句“豆子炒熟都有份,鍋?zhàn)诱藳](méi)人問(wèn)”。我一下子就笑出來(lái)。他說(shuō):哦寫得有意思哇。可有意思呢。
我說(shuō),當(dāng)初你為什么不自己干?省得這些麻煩。
他說(shuō):好哦的你呀,咱是地主成分,平時(shí)回村里頭只是個(gè)埋頭受得哈哈的,不敢說(shuō)話,萬(wàn)一掙了錢,人還不把你頭打爛。朋些股子,越多越好,誰(shuí)也不能說(shuō)個(gè)甚嘛。咱成分高,嚇怕了嘛。
此前的2006年,煤礦技改見(jiàn)效,村子里就炸起來(lái)“鬧他”。大字報(bào)都貼出來(lái)了。老蘇跟我講,一看大字報(bào)就嚇壞了,大字報(bào)說(shuō):土改時(shí)候分過(guò)田,文革當(dāng)中游過(guò)街,蘇××是地主階級(jí)復(fù)辟呢。后來(lái),煤礦出錢為村里修了路,包下所有田地的出產(chǎn),甚至給村里所有的光棍都娶了媳婦才平息下來(lái)。
再下來(lái)我知道,他準(zhǔn)備回到良種場(chǎng),在縣城西邊開發(fā)一片土地重操舊業(yè)。但是,整合遲遲沒(méi)有結(jié)果,整合之后款項(xiàng)又遲不能到位,這事一直還停留在構(gòu)思之中。
去年冬天,老蘇忽然打電話過(guò)來(lái)說(shuō):來(lái)咱嵐縣看戲吧,可鬧好咧。
怎么回事?
原來(lái),老蘇出資買了鑼镲鼓板樂(lè)器,在社區(qū)組織了一個(gè)自樂(lè)班,天天在縣城里自?shī)首詷?lè)唱戲。
再后來(lái),消息就稀了。今年秋天,給他去過(guò)一個(gè)電話,說(shuō)他仍然在紅火得唱戲,仍然嘻嘻哈哈,沒(méi)甚怪異。沒(méi)甚怪異,今天想起來(lái),恰恰是怪異。
在煤礦不景氣的那些年,舉債、躲債是老蘇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內(nèi)容,少則一月,多則半年躲在外頭,在外頭的小旅館里吃方便面,就著開水啃饅頭是家常便飯。好幾個(gè)春節(jié),等債主走了他才敢悄悄回家。他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永遠(yuǎn)是順?biāo)斓哪切┤兆樱≤嚕?dāng)代表,出詩(shī)集,那些灰暗的日子是我在他的詩(shī)集中讀到的。說(shuō)起那些日子,會(huì)勾起他妻子心里的苦楚,他和他的妻子咽下多少苦楚,外人哪里知道。我剛剛問(wèn)怎么回事,他妻子眼里就擠出好些濕來(lái)。
這些時(shí)否的日子,他永遠(yuǎn)不說(shuō)。今天我才知道,在去年的秋末,他就查出了癌病。這一個(gè)不抽煙不喝酒的樂(lè)觀的人,得病了。我想,他可能以為這又是一次躲債經(jīng)歷的重演,他仍然不說(shuō)。他以為命運(yùn)又一次跟他玩否盡泰來(lái)的把戲。他不說(shuō),但這些心情留在詩(shī)里了嗎?
沒(méi)有躲過(guò)去。
這樣的個(gè)胖墩墩的,樂(lè)觀的人,突然走了,身邊閃過(guò)一段空白似的。回來(lái)給年輕許多的同事說(shuō)老蘇的死訊,都啊了一聲,說(shuō)那個(gè)老蘇,怎么會(huì)去世?不會(huì)吧?
可走掉的,恰恰是這個(gè)不可能走掉的人。在過(guò)去那些年,他經(jīng)常來(lái)編輯部,給大家?guī)?lái)多少笑聲。
老蘇用他的詩(shī)潤(rùn)飾過(guò)許多苦澀的人生片段。他出身不好,他家的成分是地主,祖上是遠(yuǎn)近聞名的大糧商。他說(shuō):我估計(jì),祖上還過(guò)販大煙,不道德!初中畢業(yè),剛滿十五歲。那一年,家里過(guò)年連買一斤豬肉的錢都拿不出來(lái)。這個(gè)剛出校門的孩子和他表哥在窯上賣了一冬天炭,早晨天不亮起床上窯,碴起一平車大炭,兩個(gè)孩子走二十多里地拉到縣城里去賣,一車可以賺到兩塊錢。一個(gè)冬天,兩個(gè)少年為家里拿回七十多塊錢。正在屈辱與窮困中度日的老父親拍了拍他的肩膀,說(shuō)他:嗯,能拿起個(gè)事了。
這是他成長(zhǎng)的開始。從嵐縣回太原的路上,兩個(gè)少年拉著大炭走在山溝里的情景讓我猜想了很多,當(dāng)年他是哪一條山溝里走出來(lái)的?當(dāng)年的路可如今天這樣平坦嗎?
我印象里,他應(yīng)該才五十多歲。但同學(xué)告訴我說(shuō):老蘇?老蘇今年六十三歲。六十一花甲,也夠一輩子的數(shù)了。
可不,毛澤東走過(guò)嵐山的第三年,正是他出生的年份。他說(shuō),哦的許多詩(shī),不敢說(shuō)學(xué)咱毛主席,但受咱毛主席影響不小哩,小時(shí)候就能讀他的個(gè)詩(shī)嘛。
彈指一揮,皆成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