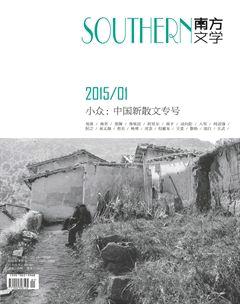舊詞匯
黃義福
芒果樹
要不是開門閉門都能看到,且已經將之視為左鄰右舍,我想我應該不會談及這些與吾鄉吾土并不十分相適的芒果樹。我說的“并不十分相適”,倒不是說此地不宜種植芒果樹,而是民間栽種并無此等習俗。從歷史上看,二十多年以前,在小城尚未開辟新區建設之時,本地好像沒有大規模栽種此樹的先例。在我們這個緊鄰興化灣南岸的濱海小城,在廣袤的閩中興化平原上,最常看到的往往是木麻黃和大榕樹。在海堤上,在村舍前,在溝道旁,目之所及,就是成排精瘦結實如農夫般的木麻黃,或是郁郁蔥蔥、像虬須老農一樣的大榕樹,它們不管是靜穆的樣子,還是隨風搖曳的姿態,都構成了南方小城和古樸鄉村的特有風貌。前者往往因為易于長成、站立成排而成為防御海風、臺風侵襲的首選樹木,后者則因造型古拙、樹蔭巨大而讓鄉人愿意將之作為庇蔭的綠化之樹。說到“綠化”,這里可能是不夠準確的,因為在鄉村和小城的邊邊角角,人們栽種這些樹木可能并沒有此等現代意識,只是興之所致,實用使然。
現在如果要去追溯小城栽種這些芒果樹的緣起,情況可能有些麻煩,但有一種設想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其時,城市建設的決策者已經具備了現代意識,他們那時亟須播種的可能就是這種現代文明意識,當他們的施政理念得以具化到城市綠化等細節時,一排排芒果樹便在這個南方城鎮栽種開去。福廈路涵江段、新涵大街、工業路,在城市十分有限的框架內,就是短短不過百來米的區府路、區府機關院前的圍墻邊,也栽種了這種之前在我們更南地方才能見到的樹種。當此等樹種蔚成規模時,在夏日芒果采摘收成季節,整個小城便被一種濃郁的果香所籠罩,小城因而具有了一種特有的韻味,有那么一刻,我甚至萌發了向城市決策者提議舉辦諸如芒果節之類活動的沖動。
但是這樣的節日顯然還不應屬于這個小城,不管怎么說,芒果樹還沒有真正走進這個小城的內心深處,也無法如木麻黃、榕樹一樣緊緊地扎根于這塊土壤,因為綠化樹、行道樹品種的頻繁更換,它們隨時都有可能終結在這個日新月異的小城之中。好在有一種事實是,在我辦公室的對面、區政府機關院前的圍墻邊,那排芒果樹終年如一地蔥郁在我的眼前。我想,除非這個機關的異地搬遷,要不它們應該沒有被更換的危險,它們已經成了這個機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寬大的樹蔭是機關車輛的天然車棚,夏日司機最想光顧的便是這片難得的綠蔭庇護;它們經由蜜蜂家族采摘鼓搗而灑落滿地的花粉蜜汁,它們與上樹摘取果實的居民構成的短暫勞作收成局面,形成了這個嚴肅的管理中樞最為動人的一面;它們的存在,甚至還帶來了城市鳥兒的福音,每當傍晚降臨,大量的鳥兒都要棲息于此,我為此獲得了無數次觀賞鳥兒在這片綠蔭群起和群落的機會。對于我這樣一個農門出身的機關工作人員來說,它們的存在往往還會使我聯想到我的鄉村、農田上任何一種作物的生長和無聲的勞作,聯想到通過廣袤的土地而與之可能根部緊緊相連的鄉村中任何一棵堅守陣地的木麻黃、大榕樹;它們的存在也會被我視為無聲的警示,這種警示涉及了靜默和從容、勞動和收獲。
因此,我敢于這樣說,在這個機關和這個小城,我是最熱愛和最關注芒果樹的人之一,也是對于芒果樹展開最多聯想的人之一。我多年觀察的結果是,我辦公室對面的這排芒果樹似乎始終并沒有長高過緊鄰它們的那幢低矮水泥房。
苔蘚
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小詞典》不管是對“苔”還是對“蘚”的釋義都有點“不屑”,三言兩語的樣子,都只提到它們是植物的一個綱,陰濕地方的附生物,根、莖、葉難以區分的綠色玩意。一種能成為綱的巨大植物體系,居然連根、莖、葉都分不出來,那會是怎樣的“低等”和面目模糊?事實上,這樣的“苔”和“蘚”是十分難辨的,因此,網絡百度百科干脆將之合成起來解釋。這樣的解釋是“尊重”和豐富了一些,但“低等”仍然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在我的印象中,如此“低等和不值得一顧者”,一般也只存在于古時大戶人家的后花園、鄉村河溝里的洗衣石上,或是敞露于梅雨季節之后的某個庭院角落。事實上,這還不是一個徹底走向自然山川的人的宏偉所見。我粗略的知識查詢后得知,苔蘚在我們的世界共有兩萬多個品種,而據其喜歡半陰和潮濕環境的習性,我相信,它們應該占據了整個溫暖濕潤的春季和夏季,應該廣泛地分布在山區和平原、鄉村和原野,應該憑據“最低等的身份”而擁有生物鏈條中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它們汲取光和水分而生,應該是水分和時光滋養而成的自然之子、天地精靈,是農耕時代的一個重要隱喻。它們還是“詩性之物”,詩歌賦予了它們世人廣為傳誦的基石。在唐代偉大詩人王維的詩中,它們得到了最為極致的描述:“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我想,就一般人的成長記憶和知識積累而言,一個人對苔蘚的認識應該是從自己孩提時代的某次摔跤開始的。你可以這樣想象,在一片長有濕潤苔蘚的角落上,一個小孩因為懵懂輕視而重重地摔在了上面,從此,吃一塹長一智,一下子長了有關苔蘚的記性。現在,我如此重提這個可怕的孩提記憶,是因為我經常要看到這樣的苔蘚,它們就長在我們夏天的空調外掛機下面,被空調水滴到的墻壁上、水泥地板上。有一天,我特地觀察了所有的機關空調外掛機,發現其所在的墻壁、地板幾乎都長上了一片大小不一的苔蘚。那一刻,我不知道我是直面了一次水生和陸生植物的進化演示,還是得到了一個古怪的啟示:當我們借助現代化的空調在房間里乘涼避暑時,“自然之子”苔蘚居然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瘋狂地生長,而且,這一原本歸屬于自然的生長方式居然寄生在了電氣化之上。
樓房
我是首次想到用“恐怖”來形容一個樓盤的,雖然我知道此后的入住者會有多高興,即便是我本人,相信住進去也會是興奮的:多高呀,視野多開闊呀,你看西南邊的壺公山、西北邊的紫宵巖,一切美景盡收眼底。
此前,大約是今年年初,當時,我所在的小區西邊還是一塊空空如也的雜地。隔著西邊的小區圍墻,我們經常要在傍晚或是在夜中臨風散步,要望著這片雜草叢生的地塊空發議論。那時候,我記得這里還有一大片黑幽幽的荒廢墓穴。然而,時過境遷,不過六七個月的時間,在這個夏末秋初到來之際,三幢高大無比的大樓居然同時拔地而起,雖然與我所在的樓房至少也有百米的距離,但我還是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些二十多層大樓所帶來的壓迫感。由于尚在外部裝修當中,外墻嚴嚴實實地包裹著建筑安全網,每當夕陽西照之時,這些大樓就會拖著長長的影子黑壓壓地逼過來,這種視覺和心理感官上的感覺每每讓人心頭生堵。
我知道,在修建大樓的過程中,一切現代化的建筑工具都用上了,挖掘機、裝載機、高空腳手架、無聲打樁機,能用上的都派上了用場。同時,有一種容易產生的假象是,大樓的建筑工人好像都被灌上了興奮劑一樣,可以不分晝夜,二十四小時輪番作戰。在我有限的人生經驗中,這樣的情景應該連辛勤的蜜蜂都無法做到,至少,蜜蜂在夜里也要休息呀。但是,不管人們相信還是不相信,就是有一種奇怪的力量,能夠排除萬難,讓人家百年的祖墳搬遷,讓莊稼遠離祖籍地,讓成千上萬噸、多到無法形容的鋼筋水泥源源不斷從不知所終的遠方運載到這里,再有條不紊地組合、投放、堆砌,準確地形成所需的體積、空間和造型,就是有一大批建筑工人要在他們本該合眼睡覺的三更半夜,堅守工地,揮汗勞作。有意思的是,所有的這一切,仿佛都可以悄然無聲地進行,神奇地升高、冒出,突然崛起于某個清晨,叫人發出一聲聲驚嘆。我同時還相信,在大樓即將竣工的時候,仍然有一種奇怪的力量,讓一沓一沓或新或舊、帶著微微體溫的人民幣,心甘情愿地匯流到那個被稱作“售樓部”的地方。
有時候,我真的不敢相信這樣的建造速度。在我的家鄉,以前要修建一座小小的土木結構房舍,需要的時間也要幾個月,而且是要動用所有叔伯兄弟中的男女成人勞力。我家現存的那座二層五廂房,據傳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分階段修建,前后歷時三年。
盡管這種比較難有一個科學的可比性,但我還是愿意把大樓崛起的這個夏天形容為“沉重、憂傷的夏天”。我不會覺得這樣的速度和創造有多么的偉大,在我的心里,關于建造和建筑的立場,我還是愿意站在蟻鳥取之有度、正義筑巢的這一邊。
農作
我相信,在比我年輕的一代中,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遠離了農村和農作,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雖然還生在農村,但是就農作經歷和農業經驗而言,仍然是一個巨大的空白。自此,他們的一生,或許絕無可能走向就在他們身邊的田間地頭。我這樣描述,絕不是要說年輕的一代懶惰成性,鄙視創造和農業生產,但似乎也無法完全排除他們對這種艱辛勞動過程的時代性倦怠。一方面,由于時代的變遷,造成了農耕人數需求的實際減少,這樣的結果是,農家子弟自此并不需要人人都留守在一畝三分土地上;另一方面,來自城市的巨大誘惑也總在或明或暗地進行著它們的拉攏事業,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不管是何種身份,從事何種職業,似乎再也難以逃脫自己與城市的千絲萬縷關系。總之,在年輕人的身上,你既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這個時代許多東西主動或者被動的頹廢、消亡,也可以自然而然地滋生難言的無奈和失落。
不說漫長的農業時代,不說那些刀耕火種的初始稼穡記憶,就是在當下之前的二三十年,農作還曾經是我們這個原本農業大國的恢宏主題。一個人好像一降生,就無可避免地要與土地、農具、作物發生血肉聯系。可以這樣說,農業時代村莊中每個人的一生,就是無數次參與農作、享用農作果實的輝煌一生。村莊對一個人的評判因而顯得簡單而率直:一個勤于農作的人,就應該是這個鄉村的優秀公民。對于農村和農作的這種美好意象,海子的那些光輝詩行是這樣描述的:“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周游世界/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然而,現代化工具的使用,使農作的方式減少了很多,一些以往熟悉的耕作把式,再也難見身影。在田頭,灌溉可以不用戽斗,抽水機械一開動,就可以走人了事;煩瑣的積肥過程不再被重視、應用,簡單有效的化肥代替了農業中最具孕育色彩的溫馨細節;甚至于插播、收割這樣千家萬戶一呼而應的田間壯觀勞作場面,也因為機械化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而難見其影。
我無由地想起了曾經有過的農作情景,直至今天,我都會相信,只要你全身心地投入了農作,就會知道信念和希望是什么,就會知道什么是黃金、火焰和純粹,而且我可以肯定,它緩慢、深愛、祥和、微妙的勞動創造,會讓所有見過的人放棄成見和陰謀,體會到生活的滿足感和人的完整性。我熟知的一種基本事實是,由于常年的農作,我年邁的母親至今血液常規檢測單上只有兩個箭頭,而我,箭頭連年都保持在六個以上,母親現在七十多歲,而我,四十還沒有到頭。
我如此這般例證農村的永恒意義和農作的健身性質,顯然不是要說我愿意終身鐘情并致力于這種枯燥的勞作,我只是想借此闡明,農作確實令人接近了人類的“童年時代”, 作為人與土地的交往途徑,無論如何,它都應該獲得永久存在的意義,也無論如何,它都不應該被排除在這個世界的秩序之外。
這個夏天,我原本想重溫一下農作,消減一些體檢單上的箭頭,但留守在家的姐姐回話說,現在已無田可以耕作了。她所擁有的田地,共有近兩畝,其中旱地四五分,水田一畝多,三年前,她還留著水田自己耕作,用以種植早稻,掙些口糧保底,去年起,她連水稻也不耕種了,只保留旱地,種植花生榨油。我想,這大概意味著,她已經徹底放棄了最原始的糧食生產,而這種情況,在我的老家已不是少數。她們或許不用擔心口糧,她們完全可以拿著打工賺來的錢,直接購買來自市場上白花花的大米。
夏日
照樣是連綿不絕的夏蟬鳴叫聲,從早上太陽升起的那一刻,直至夕陽落山,這種煩人的鼓噪似乎就沒有消停過。天空同樣湛藍無邊,有時候會沒頭沒腦地飄過一些鉛色的云朵,帶來一兩場看似氣勢磅礴的陣雨。可是這又能改變什么呢,這些都是我們心理預期范圍的事情,哪一年的夏天不會下些消暑降溫的陣雨呢?而陣雨過后,天氣依然炎熱難熬,我們仍然會呆在辦公室里,開著空調避暑享用。有那么一些空閑寂寥的間隙,我會透過半掩的門縫,抬頭仰望天空,看天空底下被陽光照射得出現了幻影的樓房,樓房頂層那些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水塔以及緊挨著樓房的那一簇簇呈現出翠綠的樹尖尖。
這時候,我所在的機關大院里的那些芒果一定是熟透了,有時候,我甚至聽到了果實從樹上掉到避蔭車上、地上的撲通聲。有時候,我還會看到一些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偷偷爬到樹上搖晃芒果置之落地的情景——這些幾乎都是每年這個時間段必將展演的事情,直至樹上空無一果。我還知道,天色漸暗的時候,這個機關大院的綠地還將變臉成為市民的休閑場所,長度十分有限的車道上滿是散步快走、健身晚練之人,一時間,這里人影晃動,熙熙攘攘,而那些芒果樹下忽明忽暗的場景和場館樓舍的隱秘角落,也必將成為情侶們的藏身之地。
烈日、空調、避暑,這些幾乎都是在冥冥之中設定好的事情,前年如此,去年如此,今年和明年也將沒有什么很大的差別。坐在辦公室,盡管我已遠離農事,不稼不穡,我也會憑著節氣,猜想出鄉下老家的留守農戶每一個時段會在農田上從事何種活計,會以怎樣老套的方式和語言,埋怨時光的匆忙和生命的空茫。
而我呢,我的夏天是一個怎樣的面目呢?當我這樣自問的時候,我已經沮喪不已,寂寥、困頓、無為充斥腦海。想象不出我今年的夏天與五年前或五年后的夏天將會有怎樣的不同。季節輪回、果實成熟、按部就班地上下班,什么都沒有懸念,老人們可能會為此形容說這是在“翻書本”,而我還是愿意還原它的本意,這就是過日子,翻過一頁,就應該是下一頁了,如此輪回,起于何時,不知何終。有時候,在空茫和困頓之中,我甚至聽到了類似于自來水汩汩流動的可怕聲響。我本是一個無甚高遠理想、無能為力的人,此刻,我只是愿意把祝愿贈予那些在籃球場上奔跑的孩子,祝愿那些屬于孩子的理想和希望,能夠隨著籃球拋出的優美弧線不斷地伸展至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