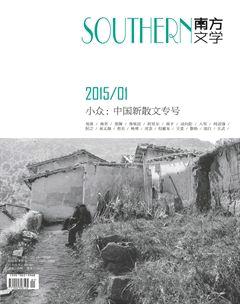夢之書(節選)
楊勇
我夢見一個血色的黃昏,我沿一條晚霞鋪滿的大河走。大河好寬闊啊,對岸就連在晚霞里。我在岸上,腳下是無盡的碎石河床,我不知道我去哪,我只是拖著自己的黑影子在走。在一個開闊的渡口,我停下來,因為遇見一位老婆婆。她的白發被夕光染成了紅色,臉也成了紅色。她在工作,在洗手絹一樣的東西。我走過去,發現她在洗臉皮,一張張軟沓沓的,有點兒像達利畫的變形了的鐘表。她說這是她在人群中撿到的臉皮,我居然認識當中的一些臉皮。我沒有驚訝,她笑瞇瞇的表情讓我不再恐懼。我開始幫助她洗臉皮,我快樂地抖動著手帕般的臉皮,洗干凈后往自己的臉上貼。一張又一張,當我照著水面,我又喝醉般地撕扯著它們,一張又一張。
我夢見我白色的裸體,它發出夜明珠般溫潤的白光。我閉著眼睛在空蕩的夜晚流浪,就像在德爾沃的畫中一樣。天是暗藍的,周圍是呼嘯的秋風,天地開敞,我周圍有一層保護性的寂靜和溫暖,我游走在大風里,漫無邊際。我碰見了一群裸體女子,她們在藍色的夜空下嬉戲,她們好像是仙子。她們沒有看見我,我只是從她們旁邊經過,我們彼此都沒有為自己的裸體而害羞。只是那么一瞬,她們回頭。我輕輕地走,輕輕地,又看見她們云一樣輕輕地逝去。
我進入了一個大長廊,來到一個大玻璃房子中。那里面的空間擠壓我,許多白色的花朵在飛,隱約間我看見了裸體的仙子們在那里。風在外面的世界呼嘯,我沒有停下來,我仍在走,那些擠壓的空間好像是氣球的皮膚,有彈性,我走多遠,它們就能擴張到多遠……
我不認識他是誰,可能這對我說來也并不重要。但我清楚地記得他的長相,我怎么也不會忘記。他,方正的大臉,光頭,有兩道充滿威脅性的眼光。我們在師院的長條形水池旁洗臉,他將水濺到我臉上,帶著明顯的故意。我說,你注意點!他沒有聽見,其實他聽見了,他在裝聾作啞,又將水向我的臉上濺。我沒有躲,看定他的目光。我們的目光打起架來,彼此交火。他的目光排山倒海地向我拋刀子,我有點兒頂不住了。后來,我說,算了吧,算你能。我端著臉盆離開,他也跟著我走。他走在我身后,像一只大熊一樣。由于夜晚的月光,他巨大的影子竟然嚴實地覆蓋了我單薄的影子。如此這樣,路上就好像他一個人在走。我說,你離我遠點,我看不見自己的影子了。他沉默著,沒有反應。這樣路面上仍舊他一個人的影子在走。我們來到了半明半晦的有月光的足球場上,我們的決斗應該在這里開始。我放下了臉盆,轉過身來,他的影子涂抹得我眼前一片昏暗。除非他閃動一下時,露下的月光像刀鋒一樣晃眼。我說,你為什么和我過不去?來吧,我們就此做個了結。他略帶驚異地看我。突然一個足球從高空飛來,是從月亮上掉下來的。那球就落在我們中間,有一瞬間我們看不見彼此的臉。我飛起一腳,向那球兒踢去,球運向他的頭部,貼著他的臉旁射走了。然后,我看見他一副呆呆的臉。他說,你強,這堅硬的石頭,要踢到我臉上可能我就死了。他嘆口氣,轉身走了,我喘口氣也走了。這回,月光下,我終于有了自己的影子。
我看見從夜空的云朵中魚貫而來了一隊透明的人群。看不清他們的長相,一縷輕風一樣,一個接一個落地且飄行。沒有一點兒聲音,他們就在空曠的街道上行。月光的照徹下,我并沒有發現他們映在地上的影子。仿佛要去尋找一個住的地方,這些發光的透明人群,似乎是身上的玉佩發出叮當的脆響,偶爾,那隱藏在空氣中的裙帶,白色和青色的裙帶隱約浮現,后來隊伍里又亮起小小的紅燈籠。在深藍的夜色里,我為我的看見而激動,并且追隨著這陣風,跟著他們跑。街道上,不知何時也跑來了黑暗的人,一律屏息觀望。突然有人大喊,這是天上的神啊,這是神啊!剎那間,那群透明的隊伍轉了一個巨大的銀色弧線,像一條騰飛的白龍,直奔月亮而去了。在我的仰視中,天空寂蕩,一派深藍的虛無。
兩排榆樹的黑枝條在鄉村的土路上相互摟抱,搭成了一個長長的晦暗的廊洞,我就走在那里,腳下摩擦出沙石的碎響。剛剛下過雨,土路上到處是水洼和流動的沙泥,籬笆下的土溝里也溢滿了黃濁的水。我從很遠的地方回來,第一次感覺到這晦暗鄉村土路竟然這么長。這是荒寂的時刻,我向著家的方向走,我盼著早點兒看見那低矮的草房。迎面一個小黑點向我移來,它漸漸地長大,接著一條大黑狗搖著尾巴出現了。它并無惡意,圍著我轉,但我不認識它。我向我家的木門走去,它也跟進來,并且坦然地趴在一個小窩里。雖然路上剛下過雨,我家的菜園卻干旱著,裂成了龜殼兒。我看見我的母親,她在澆菜地,清涼的水一瓢瓢地倒向蔫枯的小苗兒。母親是現在的年齡,衰老的腰身有點直不起來。我卻是小時的我,剛剛從另一個邊城放暑假歸來。我從來就沒有記住過母親年輕時的樣子,包括我的父親。草屋里,年老的父親還在喝酒,端著酒杯在罵母親。一切都是那樣的清晰,那所土房和它周圍的菜地,連接著更多的別人家的土房,稀疏的籬笆和無邊的水田。在那個夢里,我長不大,唯有狗叫聲腫脹地痛在整個小村里。
我感覺是在一張孤筏上。我恍惚記得周圍是藍色的沼澤和溝渠,遠外仿佛有一座島嶼,但又不是,因為這一切并沒有大海那樣的氣魄。無疑,場景是我熟悉的鄉下,恰恰是水波的藍色讓我以為是大海。有一會兒,我茫然地站在孤筏上,為這突然的大水和那條黑鯨,全身顫抖。此前,那個童年的我流連在供銷社,口袋里面一分錢也沒有。我埋頭在貨柜的厚玻璃上,專注著那些劣質的糖果和小人書兒,呆呆地不動。后來,有人把我趕出來,就遇見這荒涼的從遠處涌來的大水。大水無聲地漫過來,閃動著藍色的光澤,眼前的村莊消失了,變成了眼前的沼澤。我大聲地尖叫,站在冰涼的越來越深的水中,但沒有人聽到我的喊叫。一條黑色的露出了旗翅的鯨魚貼著水面向我沖來,像小潛水艇一樣沉沉浮浮。我慌忙地向后跑,跑到一處淺灘上,那是一堆從地下挖出來的沙子。大魚沖不上來,在藍色的水里圍著我游弋,并且隨著潮水的上漲,一次次地靠近我。水更大了,大魚烏云一樣讓我恐懼,我害怕從那里投來閃電和炸雷。我不斷地退后,喪失了一條條回家的道路。
有三只老鼠鉆進了蘋果箱子里。隔著紙箱我能聽見吱咯吱咯的啃噬聲。我將手伸進箱子里,感覺到了它們奔來奔去光滑的皮毛。此前有三個男人在箱子邊轉悠,交頭接耳,后來他們就消失了。我不知道他們去了哪里?一會,一個男人出現在箱子旁,優雅地吃著一個蘋果。我沒有理他,只是搜尋著箱子里的老鼠,我感覺到那里還有兩只,但我抓不到它們。我茫然了一陣,身邊又多出兩個人來,他們帶著禮節性的微笑看我。這樣,我身邊出現了三個男人,他們穿著裘皮大衣,一模一樣,臉尖尖的。我說你們是老鼠,他們大笑。我充滿怒火地追逐著他們,他們停下來不屑地看我,又輕蔑地推開我。我斗不過他們,他們慢條斯理地走了,我的蘋果箱子空了。
一個草棚搭建在大水上面。草屋里擠著我和兒時的伙伴,還有大學的同學。他們在狂歡,彼此說著一門我并不懂的語言,可我居然能聽懂幾個單詞。我并不是來參加他們的聚會,我只是來躲避著地面上那追擊我的滾滾洪流。水流夾雜著石塊,像一群潛伏的野獸,洶涌在我的身旁。草棚的四個柱子在石頭的碰撞中震顫,草棚不停地搖晃,我們在上面飄搖,浮在樹葉上一般。他們不關心大水,用外語吵鬧著,唯我孤單著,孤單于我的恐慌和隱憂中。后來,水中出現了一個皮膚棕色吹喇叭的女人,長長的頭發濕漉漉,腰間圍著類似樹葉穿綴成的裙,少得可憐的裝飾,讓她的整個胴體格外俊美。一會兒,一個健壯男子也從水中鉆出來,也是棕色皮膚,腰間繞一草裙。他們顯然是一對,在波濤上他們幸福地合奏,風情萬種地吹。草棚里的人還在吵鬧,沒有人看到這一對奇異的外國情侶。一會男人離開女人,乘著浪濤去了遠方,那可能是一個沙灘或者小島,他的背后是煙波。女人在哭,向那男人大喊,你不愛我了嗎?我聽懂了這句話。男人沒有回頭。于是,我看見了許多吹喇叭的女人,從水面上升起,泡沫般憂傷,妖艷而動人。
我看見一座空房子。它破敗不堪,轉過去后是一條鋪滿灰土的巷子,空空蕩蕩。我擦著汗水走,陽光熱辣辣地曬著,腳下踢踏的塵土飛揚,嗆得我不斷地咳嗽。仿佛是我的故鄉,但我找不到曾經熟悉的一切。我忍受著饑餓,尋找可以吃飯的地方。后來,我看見一座土坯房,一口水井。我走進房間,眼睛適應了一會屋里的光線,看清了橫七豎八的桌椅,其實是許多椅子放在桌子上。有一個小柜臺,后面坐著個木然的人。我走近他,突然認出他是我村子里的朱偉東,我小時的玩伴。他說,是你呀,在這兒吃點飯吧,我開的小店兒,生意不錯,你看這滿屋子里的人。我回頭看看,仍看不見滿屋子的人。我說我不餓,急忙走掉。剛出門口,碰上了兩個陌生人,他們說在這兒喝啤酒呢,出來撒尿,一起進來喝吧。他們邀請我。我說,我有事情要辦,不能喝酒。我們是在門口的空地上說話,他們皆是少年的長相,但我們談論的卻是成人的話題。我們頭頂的天空,像日全食一樣半明半晦著。我探頭看那口水井,里面有一汪淺水,荒涼地反射著天光。
我躲在一個被拆毀的空房里,另一個男孩也躲在這里,我們是一起跑進來的。我記不起那個男孩子是誰。我們擠在墻角,房子上面已經沒有房蓋,窗戶也沒有,四下露風。我們跑到這兒是為了躲避另一伙人的襲擊。他們的石塊流星雨一樣快速而密集,從屋頂和窗口飛進來。真怪,我們跑到哪,那石塊跟到哪兒,我的后背挨了子彈一樣痛疼。后來,我選擇了一個夾角,剛好避開石塊的進攻路線。那些石塊著急地落在我身旁,卻打不著我。我正為自己的選擇慶幸,忽然后背又挨了幾下石塊。是那個男孩子砸來的,我正想喊叫,從窗子邊上跳進來幾個人。我清楚地看見是小伙伴關長勝,檜吉賓,趙小慧。那個男孩子說,你跑啊,有能耐你就跑!后來,他和他們一起撲向我。我被那個男孩子出賣了,我還是個做游戲的孩子。在夢中,我感覺自己被他們用石塊砸死了,哭泣中,我看見了他們臂上血一樣紅的紅衛兵袖標。
我的村莊不知怎么的變成了巨大的飛機場。村里的人于是擁在一起搞慶祝活動。大家仰頭看飛機一架架騰空,興奮地尖叫。最后,開闊的土地上就剩下一架飛機,其他的飛機早無影無蹤。大家靜靜地期待著,幾乎屏住了呼吸。終于,那飛機也轟鳴著起飛了,像只銀白色的蜻蜓。后來,飛機好像失去了控制,在藍天里垂直下墜。巨大的機身遮蔽了空中的太陽,濃濃的陰影覆蓋在村莊上空。我希望飛行員跳傘,但已經來不及了,飛機一頭扎進了大地。我們奔向出事地點,飛機宛若巨大的針頭,插在田野里,靜靜地燃燒。好久,飛行員出來了,居然安然沒事。那飛行員,讓我驚訝,他居然是年輕時差點當上飛行員的我父親。
只是一瞬間的事兒,我回到了故鄉的東大河邊上。在河邊,我兒時的同伴還是那樣小,而我身邊多了兩個上班的同事。我們沒有因時空巨大的轉換而驚訝,也沒有因為年齡的問題影響在一起游戲。我們奔跑在一望無際的稻田中,像奔跑在油綠的毯子上,滿眼都是點燈般的小黃花。后來,我們迷路了,在水溝縱橫的土路上尋找回家的路,我們激烈地分歧起來。我認為沿大河前行找路是浪費時間,因為河道太多了,我寧愿走冒險,涉水回去。我的兩位同事跳躍著,踩著油黑的田埂,順著水的流向外走,他們總是這樣活泛,給自己找退路。我渡河,水已經沒到我的腰身,我不在敢前行,焦慮地立在河水中。我的童年伙伴不見了,我的同事也不見了,我的四圍滿是清涼的大水。我繼續涉水,我看見了對岸有朝鮮族人的村落,有他們的生產隊,馬廄,播種機和生銹的鐵鏵犁。水水終于淹沒了我,我感覺到眩暈,好像飛了起來。當我大口喘息時,我終于濕淋淋地站在了對岸。我快速地跑動起來,我的童年也跟我跑了起來,向著村莊那個方向。
我夢見我在黑藍的大湖里游泳。水面空寂開闊,飄滿涼森森的霧氣。我一個人,無助地游,兩臂劃著湖面,嘩嘩的水聲激越。我很自由,但找不到岸。后來我游到一個大橋下,我摸到滑膩膩布滿青苔的粗大橋墩,內心感覺出一些踏實。但我還是上不去,那橋高至晦暗的云中,我判斷不出它的高度。我一圈圈地游弋,我看見了從我身邊,向廣闊水域漾開的孤獨的大漣漪,白色絞索一樣環在我脖子周圍。就這樣,我游啊游,我碰不見一個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力氣游上岸。
我回到了我老家院落。園中開滿了粉杏花和白李花。我在那兒尋找果子,在沒到秋天的時候。后來我穿過一個老倉房,來到豬圈邊。我看見人一群人在圈中挖掘,他們向我解釋說下面有人,也就是說這黑暗的地層下有人。我停下來,耐心地看著。果然,他們挖掘出來一團人形的東西,周身黑黝黝的,蠕動著,在新拋出來的土層上。我俯身看那些類似蟲蛹的物件,居然認出了不少人,其中有我的大學同學以及與我同居一個城市的熟人。我很驚訝,問他們為什么在這兒。他們說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在這里,感覺到自己有意識,還像活著一樣,卻恍然如夢。他們還說,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是人還是動物,只能就在土層中一動不動地呆著。接下來,他們抱怨這兒風水不好,糞便和尿水都流進身體里去了。他們還說,人死前一定要找個好地方,避免被污染身體。
我在參禪學佛。我一個人穿越了空曠的大野,進入到深山的大古寺中。帷幄黯然的大殿內,我盤腿坐在一個蒲團上。我在打坐,入定。突然我旋轉起來,感覺到了身體的騰空,并且有時整個身體會倒轉過來。我身邊的那位大和尚,他甩動著拂塵,那迅速掠過的風兒,讓我知道了是他的緣故。我在拂塵的風中被迫旋轉,他在妨礙我打坐。我緊閉著雙眼,讓自己膠似的沾在蒲團上,時刻暗示著自己堅決不能掉下來。又一會兒,我感覺自己消失了,成了那蒲團,或者與它融為一體,無論多大的顛倒我都穩穩地坐著。當我落地,睜開眼睛,大和尚點頭示意我可以了。我發現他身邊,還有一個和尚,我們認識,我卻記不起他是誰。他為我披上袈紗,絳紫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