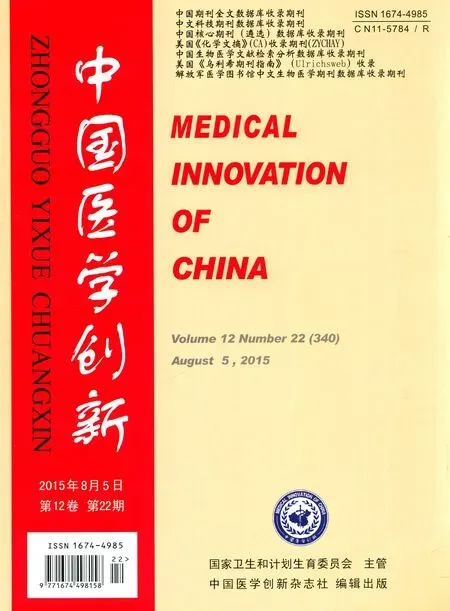振幅整合腦電圖評分系統在早產兒腦損傷早期診斷的價值*
王德勝 賴麗芝 蔣新華 何康成
近年來,隨著圍產醫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全國各級醫院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陸續成立,早產兒存活率顯著提高,高危早產兒病死率較前下降,但早產兒腦損傷發生率卻有相對升高趨勢。尋找能夠輔助臨床早期識別和診斷早產兒腦損傷的檢測手段,盡早采取干預措施,最大程度地避免后遺癥的發生,是今后我國新生兒重癥監護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振幅整合腦電圖(amplitude integrated electroencephalogram, aEEG)是常規腦電圖的一種簡化形式,可直觀反映腦功能狀態,在神經系統損傷的早期診斷和評估預后方面有很高的應用價值。本研究對28~36周腦損傷早產兒及無腦損傷早產兒進行aEEG監測,參照Burdjalov等[1]創建的評分系統對aEEG圖形進行評分,比較兩組評分特點,以期為早產兒腦損傷的早期診斷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3年1月-2014年10月在暨南大學醫學院附屬東莞醫院產科出生并收住于新生兒科的腦損傷早產兒(腦損傷組,50例)和無腦損傷早產兒(對照組,40例)為研究對象。兩組早產兒胎齡為27周+0天~36周+6天。腦損傷診斷需符合以下標準:(1)意識改變:興奮、嗜睡或昏迷;(2)原始反射改變:活躍、減弱或消失;(3)呼吸困難;(4)生后48 h內出現肌張力改變:降低或增高或癇性發作或喂養困難[2-3]。排除標準:由遺傳代謝紊亂引起的腦損害及低血糖腦病、膽紅素腦病、宮內TORCH感染及生后中樞神經系統感染等[2]。所有研究均通過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及獲得患兒家屬知情同意。早產原因:孕母妊娠期高血壓病或重度子癇前期26例,胎膜早破24例,前置胎盤或胎盤早剝9例,宮內窘迫4例,瘢痕子宮7例,多胎妊娠9例,原因不明11例。兩組早產兒胎齡分布情況見表1。兩組早產兒在胎齡、性別、出生體重等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P>0.05),見表2。

表1 兩組早產兒胎齡分布情況 %

表2 兩組早產兒的臨床資料比較
1.2 研究方法
1.2.1 aEEG的監測 使用美國Nicolet-one腦功能監護儀。使用一次性電極,描記前清潔頭皮。電極放置于雙側頂骨(相當于10-20國際電極安放法電極位置的P3-P4導聯處),參考電極在距頭頂中央向前25 mm額中線上。所有研究對象均于生后48 h內行aEEG描記,記錄時間為8 h。
1.2.2 aEEG圖形分析 采用盲法判讀。由兩位具有腦電圖認證資質的醫生,參照評分系統對aEEG圖形連續性、睡眠覺醒周期、下邊界振幅和波譜帶寬度(帶寬)分別進行評分,各參數原始分相加得總分,并用相應孕周早產兒總分平均值減去原始分得校正后總分,以消除不同孕周所致差異。校正后總分越大,提示aEEG異常程度越明顯。見表3。不同孕周早產兒aEEG平均分:胎齡24~26周、27~28周、29~30周、31~33周的分數分別為2、6、8、10分。

表3 早產兒aEEG評分系統
1.3 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 19.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s)表示,經方差齊性分析后,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 字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腦損傷組aEEG圖形校正后總分為(0.82±1.14)分,高于對照組(0.23±1.07)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53,P=0.013)。
3 討論
早產兒腦損傷是指因產前、產時或/和出生后各種病理因素導致早產兒不同程度的腦缺血或/和出血性損害,可在臨床上表現出腦損傷的相應癥狀和體征,嚴重者可導致遠期神經系統后遺癥甚至死亡[2]。早產兒腦損傷的發病機制主要是,在圍產期缺氧缺血或/和宮內感染的影響下,通過能量耗竭(細胞膜泵功能障礙)、過氧化、炎性細胞因子或興奮性毒性氨基酸等機制導致典型的腦室內出血或/和腦白質損傷,繼而正常的腦發育程序受阻或紊亂,皮質及皮質下神經元損傷或缺失[4-6]。新生兒腦代謝極其旺盛,腦組織對缺氧的耐受性差,敏感度高,即使短暫的缺氧也可能導致腦組織的損傷,甚至產生腦功能的損害[7]。早產兒的腦組織發育欠成熟,離子通道和脂質數量少,對缺氧等圍產期不良刺激尤為敏感,使得腦損傷早產兒的早期死亡率和致殘率都較高[8]。不同程度的缺氧導致或加重本不成熟的早產兒腦血流動力學的紊亂[9],使腦血流自主調節能力受損,從而導致或加重腦損傷。但同時未成熟腦的可塑性較強,早期應用神經保護措施有可能減少神經元凋亡的發生,從而減輕腦損傷,這是新生兒腦損傷治療的關鍵[10-12]。由于早產兒各系統發育不完善,生后病情不穩定不宜外出檢查,加之早產兒腦損傷缺乏典型臨床表現,目前臨床及影像學不能早期確診早產兒腦損傷,相應危險因素不能及時得到糾正或避免,遠期神經系統損傷發生率亦居高不下。因此,確定一個敏感、簡便的早期判斷早產兒腦損傷的方法,對臨床有效治療有很大的指導作用。
腦電生理檢測是臨床上研究新生兒腦損傷的重要手段。aEEG是常規腦電圖的簡化形式,只記錄單個通道(頂骨電極)的信號,采集的信號首先被放大,通過一個不對稱的波段濾波器,濾去低于2 Hz和高于15 Hz的信號,最后以6 cm/h的速度從0~100 μV輸出在屏幕上。與常規腦電圖相比,aEEG電極少,操作簡便,受環境影響小,且圖形直觀,易于判讀,在發達國家已廣泛應用于高危新生兒的床旁監護[13-14]。
aEEG可直觀反映腦細胞功能狀態,腦損傷早產兒aEEG圖形主要表現為缺乏睡眠覺醒周期、窄帶下界電壓過低、窄帶帶寬加大、連續性低電壓、癲癇樣波形和爆發抑制等[2],但其圖形分析缺乏完全統一標準。Naqeeb等[15]和Hellstrom-Westa等[16]按振幅波譜上下邊界及是否伴發癲癇樣電活動,將新生兒背景活動分成正常、輕度異常、中重度異常3個等級,其標準明確,容易掌握,被證明能較好反映缺氧缺血性腦病的病變程度。但這一標準并不適用于早產兒的腦功能分析,因為隨著胎齡的增加和腦的成熟,早產兒aEEG成熟度增加[17]。Burdjalov等[1]綜合以往的研究資料創建了一個早產兒綜合評分系統,分別對背景活動的連續性、睡眠覺醒周期、下邊界振幅、波譜帶寬度進行等級評分,同時,其研究組對30例胎齡24~39周的新生兒在生后12~24 h及生后48~72 h進行aEEG監測,隨后每周或每兩周進行aEEG監測,共收集有效aEEG圖形146份,并以此求出不同胎齡段及糾正胎齡段,評分系統中各參數及總分的平均分[1]。研究結果證實該評分系統可定量分析腦成熟過程各參數變化,客觀反映新生兒不同的腦電活動,也便于不同患兒間aEEG圖形的比較和同一患兒不同時間點的比較,有助于對腦損傷患兒aEEG圖形進行客觀評價[18]。本研究參照該評分系統,對不同胎齡早產兒aEEG進行分析,簡化了操作,有利于臨床判讀。
連續性電活動指規則帶寬,沒有明顯振幅差異;不連續性電活動指不規則帶寬伴明顯振幅差異,下界振幅可變,但主要<5μV,上界>10μV。aEEG的睡眠覺醒周期表現為平滑的正弦曲線變化,主要指下界。Luo等[19]等研究中,睡眠覺醒周期出現情況與臨床近期預后的等級有序資料相關性檢驗,結果示睡眠覺醒周期分類與臨床預后存在明顯相關性(Spearman等級相關系數為r=0.677,P<0.001)。下邊界振幅即aEEG下邊界的平均最低電壓,隨著睡眠覺醒周期的出現,將圖像窄帶的下邊界電壓作為下界振幅。帶寬即上、下界電壓差值,可同時反映圖形電壓的跨度和aEEG抑制的程度。以上4個參數的分數相加得總分。總分綜合了連續性、周期性、下界振幅及帶寬的變化,能更好的反映早產兒的腦功能狀態。
本研究比較了臨床腦損傷組和對照組早產兒生后48 h內aEEG圖形校正后總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胎齡27~36周早產兒出生早期aEEG評分可反映腦功能的改變,對早產兒腦損傷具有預測作用。aEEG校正后總分越高,腦功能受損越嚴重。另外,本研究中對照組并不能完全排除腦損傷可能,因為早產兒腦損傷可不表現出明顯臨床癥狀,這種情況更需要依靠aEEG等輔助檢查進行腦功能監測。以上結論尚需進一步多中心、大樣本研究以證實。
早產兒aEEG評分系統不納入爆發-抑制、癲癇樣電活動等明顯異常的aEEG形式。但本研究旨在發現早期的、程度較輕的腦損傷,以指導臨床及時采取干預措施,如出現明顯異常的aEEG形式,建議同時參考Naqeeb和Hellstrom-Westa等分度標準,以更好地了解腦損傷的嚴重程度及更準確地估計預后。
綜上所述,aEEG評分系統對aEEG圖形連續性、睡眠覺醒周期、振幅、帶寬進行量化分析,簡潔明了,對早產兒腦損傷具有預測及評估作用,適于在NICU中推廣應用。考慮到早產兒腦損傷是一個持續動態的過程,有必要對腦細胞功能狀態進行動態監測,以了解損傷嚴重程度及評估預后,指導臨床工作,建議對早產兒于生后早期常規完善aEEG檢測,依據具體評分結果確定動態監測方案。另外因aEEG導聯少、時間壓縮等所致的臨床漏診不容忽視,aEEG需與傳統EEG、影像學、實驗室檢查等結合應用,提高診斷率。
[1] Burdjalov V F, Baumgart S, Spitzer A R. Cerebral function monitoring: a new scoring system for the evaluation of brain maturation in neonates[J]. Pediatrics,2003,112(4):855-861.
[2]中國醫師協會新生兒專業委員會.早產兒腦損傷診斷與防治專家共識[J].中國當代兒科雜志,2012,14(12):883-884.
[3]鄧明映,吳曉華,陳凱星,等.早期干預對早產兒腦損傷及腦發育的影響[J].中國婦幼保健,2011,26(17):2609-2610.
[4]袁天明,俞惠民.重新認識早產兒腦損傷[J].中華圍產醫學雜志,2014,17(5):289-292.
[5] Rees S, Harding R, Walker D.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injury and neuroprotection in the fetal and neonatal brain[J]. Int J Dev Neurosci,2011,29(6):551-563.
[6]周叢樂.深入認識早產兒腦病[J].臨床兒科雜志,2015,33(3):201-204.
[7]馬曉利,宋金枝,李建明.新生兒腦血流動力學改變與腦損傷的關系[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10,25(8):607-609.
[8] Vasiljevi? B, Maglajli?-Djuki? S, Gojni? M.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amplitude-integrated electroencephalography in neonates with 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J]. Vojnosanit pregl,2012,69(6):492-499.
[9]盧紅艷,常明,吳麗華.未足月胎膜早破后早產兒腦損傷的相關危險因素分析[J].中國婦幼保健,2012,27(29):4547-4549.
[10] Kolb B, Gibb R. Brain plasticity and behaviour in the developing brain[J]. J Can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2011,20(4):265-276.
[11]龍莎莎,程國強.早產兒腦白質損傷治療的循證醫學進展[J].臨床兒科雜志,2015,33(3):287-290.
[12]韓炳娟,鄒卉,韓炳超,等.早產兒早期干預的研究進展[J].中國婦幼保健,2015,30(7):1146-1148.
[13] Okumura A, Komatsu M, Abe S, et al. Amplitude-integrated electroencephalograph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encephalopathy with refractory,repetitive partial seizures[J]. Brain ev,2011,33(12):77-82.
[14] Frenkel N, Friger M, Meledin I, et al. Neonatal seizure recognitioncomparative study of continuous-amplitude integrated EEG versus short conventional EEG recordings[J]. Clin Neurophysiol,2011,122(6):1091-1097.
[15] Naqeeb N, Edwands A D, Cowan F M, et al. Assessment of neonatal encephalopathy by amplitude-integrated electroencephalography[J].Pediatrics,1999,103(6):1263-1271.
[16] Hellstrom-Westas L, Rosen I, Svenningsen N W. Predictive value of early continuous amplitude integrated EEG recordings on outcome after severe birth asphyxia in full term infants[J]. Arch Dis Child Fetal Neonatal Ed,1995,72(1):F34-F38.
[17]劉登禮,莊德義,邵肖梅,等.早產兒振幅整合腦電圖的影響因素[J].實用兒科臨床雜志,2012,27(14):1111-1113.
[18]程國強,施億赟,邵肖梅,等.振幅整合腦電圖評分系統評價新生兒腦發育的臨床價值[J].中華圍產醫學雜志,2012,15:234-237.
[19] Luo F, Lin H J, Wang C H, et al. Diagnostic value of amplitudeintegrated electroencephalography in predicting outcome of newborn patients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J]. Chinese Journal of Pediatrics,2013,51(8):614-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