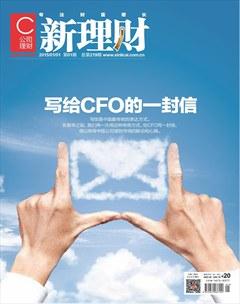無需過度夸張盧布危機
No Need to Overstate Russias Rouble Crisis
面對盧布危機,只要俄羅斯政府應對得力,反而可能成為俄羅斯經濟結構改善的契機。
俄羅斯盧布的急劇貶值已經構成了一場貨幣危機,盡管尚未發展成為金融危機。2000年俄羅斯盧布年均匯率為1美元兌28.13盧布,2005年為28.28盧布,2010年為30.37盧布,2011年為29.39盧布,2012年為30.84盧布,2013年為31.84盧布,而2014年12月15日收盤匯率已達1美元兌63.4盧布。為遏制盧布貶值,俄羅斯央行采取了干預匯市、提高利率等措施。據統計,截至2014年12月11日,俄羅斯央行已7次干預匯市,總計賣出外匯59.58億美元,12月17日可能再次拋售了2億美元。同時,在不到一周時間里,俄羅斯央行兩度大幅度加息,特別是12月16日凌晨一舉加息650個基點,將基準利率從10.5%提高到17%,成為1998年金融危機以來加息幅度最大的一次。
近日俄羅斯盧布匯率的大幅度貶值及其防御措施給俄羅斯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無論是實體經濟部門,還是資產市場,概莫能外。匯率暴貶本身的損害自不待言,即作為俄羅斯中央銀行防御投機性貨幣攻擊武器的高利率,盡管其目的在于提高本地資產吸引力并提高投機者遠期頭寸的融資成本,但高利率必然損害經濟產出水平,對經濟衰退國家和高度依靠負債融資的行業(如房地產)影響尤其顯著,從而與國內經濟政策目標相互沖突,政府也要為此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內外政策目標差距越大,市場越懷疑中央銀行高利率政策的可持續性。不僅如此,倘若高利率持續時間過長,很可能威脅銀行體系安全,并加重政府的融資負擔。
盧布危機對俄羅斯經濟社會的沖擊固然不容低估,但深入分析,不難發現,這場貨幣危機起因并非經濟基本面崩盤,而是遭遇一系列政治、經濟因素引發的投機性貨幣攻擊。因此,這場盧布危機不至于與實體經濟部門危機相互促進而造成俄羅斯經濟崩潰,相反,只要俄羅斯政府應對得力,反而可能成為俄羅斯經濟結構改善的契機。
貨幣危機的主要成因是什么?政府深陷持久財政危機不能自拔;國家持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資本流入不足而持久地喪失國際清償能力;大部分骨干企業因資產負債結構大面積貨幣錯配而集中陷入流動性危機;一旦這些情況引發私人資本恐慌性地集中外逃,那么“預期自我實現”的效應還會大大加劇貨幣危機的烈度。顯然,俄羅斯經濟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就財政狀況而言,俄羅斯此前財政狀況堪稱穩健。2000年財政盈余占GDP的1.4%,2006~2013年此項比例依次為7.4%、5.4%、4.1%、-6.0%、-3.9%、0.8%、-0.1%、-0.5%(負數為財政赤字),雖然2012、2013年連續赤字,但占GDP比重甚低。與其他在初級產品牛市期間卻仍然出現占GDP四五個百分點甚至更高的巨額財政赤字的資源出口國相比,俄羅斯上述財政數據還表明該國沒有在牛市期間過度濫用其收入,這也意味著在熊市期間調整壓縮福利和其他支出的痛苦沒有其他資源出口國那么大。鑒于此,盡管俄羅斯財政對石油天然氣稅收依賴度較高,國際市場油價暴跌并持續滯留低位對其損傷不小,但其財政還遠遠達不到引爆如此大幅度本幣貶值的地步。
在國際收支方面,俄羅斯更沒有達到危機地步。不同于外蒙古、巴西、南非等資源出口國在初級產品牛市期間仍然出現巨額經常項目收支逆差,俄羅斯經歷了持續的經常項目收支順差。2006~2013年間,其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占GDP比重為9.3%、5.5%、6.3%、4.1%、4.4%、5.1%、3.5%和1.6%。依靠持續的經常項目收支順差,盡管存在持續的資本外逃現象,俄羅斯2013年末外匯儲備仍然達到了4564億美元。
毋庸諱言,俄羅斯某些大企業過度負債,而且其債務中外幣負債較多,因此在理論上,如同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期間過度借入美元債務的韓國財閥接連倒閉一樣,這些俄羅斯大企業也有可能因為貨幣錯配而一時間資不抵債,或是集中陷入流動性危機。但現在的俄羅斯是一個凈債權國,其國際資產足以償付到期外幣負債,俄羅斯政府也不會坐視這些大企業破產。
在國內購買力方面,俄羅斯盧布貶值程度沒有那么大。盧布匯率貶值接近60%,但國內商品價格總體漲幅為10%,離1990年代拉美不得不美元化時期的景象還很遠。而且,這些商品漲價主要發生在非生活必需品,大米、面包等基本生活品漲價很小。隨著來自中國、土耳其、阿根廷等國的相對廉價食品涌入俄羅斯市場替代昂貴的西方食品,其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壓力還會趨降。某些大城市搶購風的主要搶購對象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是高收入、高凈值階層以此作為資產保值手段,而不是陷入生活困境。
不僅如此,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此前20年俄羅斯經濟始終未能消除資本外流問題,即使在2011年油價高漲、俄羅斯經濟景氣時期,資本外流也未能阻止。根據俄羅斯央行數據,當年俄羅斯資本凈流出842億美元,創下1994年以來的歷史第二高位,比2010年增加近1.5倍。但昔日景氣時期的資本流出客觀上也具有積極地調節作用,減少了當時俄羅斯過多的流動性,降低了經濟、特別是資產市場過熱的程度;進而削弱了今天遭受投機性貨幣攻擊和被迫實施高利率防御時資產市場遭受的打擊程度,減少了當前資本外逃的規模。由于高收入、高凈值階層在盧布貶值條件下為尋求保值而購買房產,高利率重創房地產市場、進而拖累銀行體系的風險也會大大降低。
從更長時間跨度看,如果石油熊市延續10年甚至更長,俄羅斯經濟也不會因為漫漫石油熊市而全盤崩潰。苦難輝煌,最能考驗一個國家、民族“成色”的正是危機的沖擊,社會凝聚力虛弱、國民意志薄弱的國家在危機面前一觸即潰,但擁有偉大文化傳統、社會凝聚力堅強、國民意志堅韌不拔的國家就不一樣了,只要有堅強的領導核心,危機對這樣的國家反而可能是自我提升的發展契機。當年布爾什維克繼承的是一個“既強大又軟弱”的農業國,1927~1928年,前蘇聯在經濟形勢較好的情況下發生了谷物收購危機,在探討解決糧食問題的出路時,斯大林曾指出,當時前蘇聯使用的木犁至少有500萬部,只要把這些木犁換成鐵犁,就能大大增加糧食產量;1929~1933年,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也導致前蘇聯出口的初級產品價格全面暴跌,但恰恰是在這場危機中,前蘇聯快速實現了工業化。今天的俄羅斯雖然沒有堪比前蘇聯工業化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的堅強高效組織,但至少領導核心足夠堅強,也沒用成建制的反對派,保證領導核心5年穩定基本沒有問題,保證10年穩定問題不算大,這個國家比其他大多數此前10余年同樣高度依賴初級產品行業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更有能力度過危機考驗。
對俄羅斯而言,過去10余年的初級產品牛市是一把雙刃劍,它令本來就遭受蘇聯解體重創的俄羅斯制造業進一步經歷了10年“荷蘭病”折磨,出現了“非工業化”趨勢。在這一時期的俄羅斯領導人不是不想改變這種狀況,問題是他們無法扭轉經濟規律。2009年11月12日,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向聯邦會議發表國情咨文,其中將“經濟現代化”定義為俄羅斯面臨的生存問題,多次提到不能再依靠高油價作為收入來源,要擺脫依靠能源原料出口支撐國家經濟,應該開始讓整個國家的生產部門實現現代化。“在我看來,這是我們目前所面臨的生存問題。”“祖國的威望與人民的福利不能無休止地建立在過去的成就上。占預算收入最大部分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綜合體、保障我們安全的核武器、工業與公共設施 & &所有這些大部分還是由前蘇聯專家創造的”,而“不是我們創造的”,他還宣稱,北高加索地區的腐敗程度史無前例。現在,油價下跌,“荷蘭病”因素消失,俄羅斯制造業迎來了一定程度復興的契機。須知,這個國家不是同樣高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拉美和非洲國家,因為它的人民富有才智技能,教育水平不低;它的人民在景氣時期可能顯得與拉美和非洲國家大眾一樣喜好玩樂和懶散,但遭遇危機沖擊時的韌性卻在全世界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