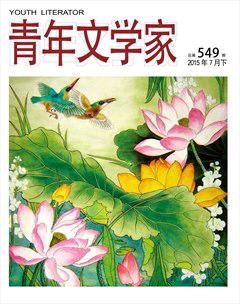《后花園》里馮二成子生活哲學的心理分析
劉秀
摘 ?要:《后花園》原文以后花園為活動場所,記敘了磨倌馮二成子戀愛,失戀,結婚,妻死子亡的故事。看似馮二成子最后仍然獨自一人繼續生活在后花園里,做著他打篩羅的工作。但是,馮二成子的過去因為有了他人他事的參與,他已經有了一套他自己的生活哲學。我們著重探討的即是圍繞生活哲學這一話題馮二成子的心理分析。
關鍵詞:愛情;婚姻;生活哲學;心理分析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1-0-01
一、馮二成子生活的開始——愛情的萌發
后花園里是很熱鬧,在這熱鬧里,其實是有幾分寂寥的,寂寞的磨房理當配著一個寂寞地磨倌。
這磨倌在寂寞中獨自生活,什么都忘了,于是他終日打著厚厚的梆子,寂寞地磨倌與熱鬧的大菽茨并無差別,大菽茨年年代代開著花,磨倌年年代代打著磨。
磨倌開始走出身份的代稱而擁有人的名字,是因為他開始發出疑問——馮二成子開始思考梆子的用處。這個問題,是馮二成子潛意識里對生活的控訴,是對單調枯燥工作的精神層面上的反抗。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歲月里,單調地重復昨日的活動,這是不能稱作生活的。真正使馮二成子活起來的,是鄰家的女兒,是他單純愛情的萌發。馮二成子是刻意拒絕外界,他終日沒有朋友訪他,他也從不去訪朋友。一個人獨自生活久了,對于闖進他生命的他人有時是帶著恐懼和防備之情的。馮二成子于是有意識地忽略掉鄰家的女兒,然而,這種有意識地忽略在長久積存之后,總是在不經意間流露出我們的本意。
一個雨夜,黑暗里只亮著那一盞燈,夜與光的強烈對比下,馮二成子內心是起伏不定的。最折磨人的是鄰家女兒的笑聲。這溫暖明亮的光下,年輕女孩子格格的笑聲使馮二成子不經意爆發了。笑聲使生命力的象征,是幸福生活的樂音。馮二成子的生活是缺少這樣一份活力的。“馮二成子的心理好不平靜,趕快關門,趕快撥燈碗,趕快走到磨架上,開始很慌張地打著篩羅。”此時馮二成子還在試圖做最后的抵抗和掙扎。三個“趕快”,一個“慌張”里透露的是一個三十多歲單身男性的緊張。故意拒絕,卻拒絕不了潛意識層面里對愛情和異性的憧憬,拒絕不了對生活的向往。
馮二成子也許是又打了一夜的梆子,然而我們可以斷定的是:他不是原來打著梆子的磨倌了。他的心中起了一陣莫名其妙的悲哀,趙姑娘是個好姑娘,而他身無長物,又是個身份卑微的磨倌,如何能夠給她幸福的生活呢?這種萌發了愛情卻又守護不了愛情的挫敗感讓馮二成子更加痛苦不堪,他對眼前的一切事物都感到不滿,好像這樣能緩解一下他的痛苦與無力感。
馮二成子的生活開是開始了,甜嘗到了一點兒,更多的卻是酸澀——趙姑娘不久便家人了。
二、馮二成子生活哲學的行程——他母親和趙老太太對他的影響
馮二成子的母親與他是一樣老實忠厚的農村人。這位老實的母親叫馮二成子不要回來給她送終免得耽誤為東家打磨。同樣溫厚敦良的馮二成子并未聽母親的話,他和哥哥親自為母親送的葬。母親生前叮囑馮二成子好好生活正視生活中的生離死別;母親死后,馮二成子更加體會到生活的艱辛和應有的的勇氣。
相較而言,趙老太太則更大程度上觸發了馮二成子認識更多關于生活哲學的問題。趙姑娘出嫁后,馮二成子把趙老太太當作近親一般,與她攀談,還到她房間去坐一坐。馮二成子是帶著愛趙姑娘的心來照顧趙老太太的,又是帶著未能盡母親的孝而轉移到趙老太太這里。然而,趙老太太的搬家再次打破了馮二成子生活的平靜。送走趙老太太比送走他自己的親娘還難過,因為他沒了趙姑娘,沒了親娘,如今又是沒了趙老太太,回到后花園去,從此又是一個孤孤單單打磨的磨倌了。若是從來如此倒也罷了,可如今他是愛了一個姑娘,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了,他有著對愛情的憧憬和生活的希望了。這樣的生離帶來比死別更沉痛的創傷。他看到田里勞動著的活著的人們,他心里對他們是滿滿的鄙棄——“到了終歸,你們是什么都沒有的。”這樣的憤怒,是馮二成子對平庸生活的控訴,他笑那些勞動的人只知忙忙碌碌,他也是在笑自己,在對自己憤怒。此時的馮二成子,像失了魂魄,而他真正明白時,他與老王結婚了。
三、肯定和踐行人生哲學——結婚及婚后生活
回到磨房的馮二成子打算再次工作,兢兢業業的他第一次沒有打磨而是走到街上來蕩了半夜。當人生經歷多了,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有他自己對于處理生活的“哲學”。
馮二成子像個快溺水的人,抓住了老王這根救命稻草。老王是個可憐的寡婦,馮二成子本是心神不定,進了屋又要走的,可老實熱心腸的老王勸慰他,給他買酒買燒餅,又聽他說今日的心情。老王發的議論又句句合馮二成子的心意。馮二成子走出老王的屋子后,坐在小土坡前,看著天空的北斗星,他的心境自由得多了,也寬舒得多了。馮二成子是想清楚了,世間的人們大多都一樣,為著生存費盡心力,如他,如老王。然而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和幫助又使人在冰冷的處境里感到溫暖,生活再苦再難,又有什么過不去的呢?
馮二成子對趙姑娘的愛是帶著自卑的,而他現在對老王,卻是莊嚴而平等的。“他在王寡婦家結了婚,他們莊嚴的很,因為百感交集,彼此哭了一遍。”這是兩顆受盡生活折磨惺惺相惜的可憐的心的結合呀!一個是三十多歲的青年的老頭,一個是白了一半頭發的三十多歲的老婦。過去孤苦無依,如今有個知心的人怎不百感交集?
馮二成子此時已經完成了生活哲學的洗禮。他也許沒有專業的名詞來表達,也沒有系統的知識來梳理。然而,他已經走過了禪宗的三個階段了。初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接著,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所以,再碰到抱著小孩的趙姑娘時,他=馮二成子繼續平靜地生活;他自己孩子的媽媽死了,他把孩子騎在梆子上,打他的篩羅;那孩子也死了,他仍舊在那磨房里平平靜靜地活著,打他的篩羅,搖他的風車。
生活,有多少歡笑,就有多少淚水。紙上的故事化成了心上的朱砂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