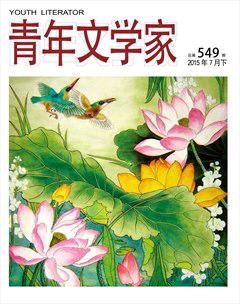《詩經》中的風教思想
摘 ?要:《詩經》是一部詩歌總集,對后代影響深遠,也具有教化作用,分析認為:《詩經》中的風教思想是與《詩經》密切聯系分不開的,詩經與禮樂的密切聯系以及國風中的“風”的特殊意義都體現了《詩經》的風教思想。然而風情與風教也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詩經》的內容十分豐富,風教思想也十分突出。
關鍵詞:詩經;風教;禮樂;風情
作者簡介:李雪(1984.1.4-),女,籍貫:成都,民族:漢族,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方向。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1-0-02
《詩經》,我國第一部詩歌的總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業的詩歌總共有305首,因此在開始的時候也被人稱之為“詩三百”,到漢朝后,由于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才開始稱為《詩經》。《詩經》對后代影響甚遠,客觀地說:其一、詩經中的305首詩創作者已不可考,因為時間差距有500年之長,到周朝才被匯編。其二、詩經中300篇詩都是有樂調的,到周朝時,樂師在音律、詞章和樂舞上表現《詩經》,并在各種禮儀場合教授王孫公子,慢慢形成了初步的教化作用。
程俊英的《詩經譯注》前言上就說:“《周禮》說: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又說:‘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可見周代樂官不但保管《詩經》,且擔負著教授詩、樂的任務。周詩可能即在春秋士大夫‘賦詩言志的普遍要求下,樂工不斷地加工配樂,逐漸地結集成為一本教科書。”因此,可推斷出在春秋時代,已經形成了諸侯間的交際頻繁,為鍛煉口才,引用《詩經》中的章句,來表達自身的訴求,所以上層人物學詩成了一種風氣,也體現了《詩經》的教化作用。
一、風教的涵義
所謂風教,是中國古代關于詩歌作用于社會的一種說法。比如《詩經》中的305首詩被分為風(160首)、雅(105首)、頌(40首)三部分,其實都一定程度上的反映了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對于文藝的功利主義要求,和用文藝思想來教化世人的統治思想。最早提出風教的說法的是在《毛詩序》中體現。《毛詩序》很系統的歸納了《詩經》中十五國風的特點和在社會中起到的作用:“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最早提出了本質、體制和體系以及功用的三重教化意義,本質上說,《詩經》的音樂發源于大自然風聲模擬的結果,比如《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帝……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引申而為各地方的民謠,如《左傳·襄公十八年》師曠所說的“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北風”、“南風”即指北方和南方的民謠歌謠,而《詩經》中的《國風》,也是指各國地方的民謠和歌謠。因此,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經過教化而成為規范,形成各種禮儀,作為穩定階級秩序和加強統治的手段和方法。從體制和體系方面說,“風”即風誦吟詠,比如《論衡·明雩》篇所說:“風乎舞雩;風,歌也。” ?《論語·陽貨》中也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說明了《詩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起源階段的詩歌總集,文化內涵豐富,自成體系和內涵,在封建社會的體制中有重要的影響。從功用上講,則是“風教”。孔穎達《毛詩正義》:“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即詩之美是一種改良政治“疾病”之“救藥”,背出而合訓。由此可見,詩經中的風教思想有很大程度的教化作用,成為一種流行和統治手段,或者成為文化壟斷的一種形式和表達,國家之立本。
“風教”包括兩方面的要求:第一在于創作詩歌的時候,由于詩歌的流行而對世人起到的感化作用和在社會生活中起到的教化作用,比如《關雎》中的“后妃之德也”;《毛詩序》中“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第二在于統治階級對于起到這種作用的加以利用和統治,從“上”到“下”的統治和教化,比如《毛詩序》說:“上以風化下。”
詩經中的風教思想基本體現在詩經的內容上,詩經的內容涵蓋很廣,大到齊家治國、國風民俗,再到老百姓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甚至小到喜怒哀樂,無不生動的豐富的全面展現了西周到春秋時期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以及世人的情感寄托,這部文學寶典,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也是一部豐富的歷史館,窺《詩經》以窺歷史,從《詩經》問世到現在,傳播幾千余年,《詩經》的滋養和哺育中國民族文化和傳統文化寓意深遠,要了解華夏文明、要了解中華文化的源泉,《詩經》都是一部很好的教科書和歷史書。
二、《詩經》與禮樂的關系
《詩經》與禮樂的關系據《論語》的記載,“三百篇” 全部可以“弦歌”,可見《詩經》的詩呈現出來的其實都是歌曲的唱詞,最初在社會反映的本質,只不過是用于音樂或者是配曲歌唱的模板。從藝術表現的角度上看,《詩經》是具有巨大的成就和長久的藝術魅力的,《詩經》的語言也具有藝術性,日常生活中,用話語表達感情,但是平談的話語卻難以表現郁結的感情,在不能滿足時,說話者不免就會加重語氣,或提高嗓門,或拖長聲音,加重聲音,為的是用感嘆或某種變化的音調補充單調的語言表達的貧乏,從而增強表現力。不可否認,感嘆語調與變化的音調都會增強語言的表現力,具有了抒情的性質,也使語言突破了單調的說話,形成了唱歌的因素和歌唱的表達。然而情緒的沖動也只有受到某種規律的節制,才能構成有表現力的形式。《樂記·樂本篇》:“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虞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都強調了形式對歌聲的規制和它構成的秩序感。節拍首先是賦予感嘆聲以音樂性的主要手段。當有規律的節拍把每一個詞的發音固定在節拍之上時,歌詞本身就會產生吟詠的節奏,由二言到四言,最終形成了古代詩歌最基本的句式:四言詩。因此,詩與樂存在著密切的聯系。《詩經》中也體現了詩用樂的形式來表現。
《詩經》源遠流長的主要原因在于受到儒家學派的推崇和追捧,以孔子和其他儒家先哲為代表的儒家掌門人對《詩經》都是大力詮釋和奉行的,因此,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詩經》以禮樂的形式也形成了獨特的試教,這是詩經風教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詩教,即《詩經》和儒教的結合,以《詩》為手段,以教為目的。從時代嬗變上看,詩教從其目的功和用大致可分解為以《詩》為教、《詩》教合一、以《詩》代教三個方面或者三個階段。《詩》為教,意思是把詩當成教材,用以教化的作用,從中可學習和感悟儒家教派精髓、周公家法之規范,比如孔子就取《詩經·魯頌·駟》中的一句總評《詩經》為“思無邪”,大概意思指《詩經》的主要功能為“興觀群怨”。所謂“無邪”,是對《詩經》的稱贊,《詩》反映事實,表達道理,本源于心,依據感情,善惡分別,平和中正,是有利于學習的,并且無害,學習《詩經》自然自能通達;所謂“興觀群怨”,是詮釋《詩》是感情抒發、考驗得失、規范人倫、對不平之氣宣泄的四種基本功能,學《詩經》可以學會孝順父母的道理,可以學會為人臣子的規矩,尤其是年輕人學好了《詩》,更是可以無往不利。孔子正是對于這樣的認識,不遺余力地親身垂范并倡導詩學。并且孔子還告誡兒子孔鯉:“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女為《周南》、《召南》矣夫,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論語·陽貨》)。意思是指,如果不學《詩》,可能連話都說不好,不學《詩》中的《周南》、《召南》就如同面對著一堵墻,沒有路可走,甚至都不配作為人,多么嚴重!孔子還鼓勵弟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論語·子路》),在孔子看來,年輕人學習的東西是很多的,而《詩》最重要、必須學習的科目,只要學好了《詩》,就可以在國內外都無往不利了,國內當官、還是國外大使,簡直都是綽綽有余。從孔子的論述中可以看出,《詩經》是具有重要性的,《詩》可以增長知識、增長見聞、鍛煉口才、增強禮儀、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多方面都具有價值。以《詩》為教科書,實用而樸素,全面體現了儒家“入世”的哲學思想,也體現了孔子自身“述而不作”的學風和教風。
三、風情與風教的關系
《詩經·國風》中的風詩是《詩經》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刻地反映了周代的社會風情、風俗和風教,任何風情、風俗與風教都離不開任何時代的社會環境和君主教化、統治、強化的大背景。所以,這兩者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即直接的反映和被反映的關系 。
首先,十五國風大都是從民間采集而來的民風民俗,民風和民俗最初都是零散的,也是不成系統的,但是卻代表了周代的社會風情。《詩經.國風》中把這些民俗給集合、經過統治者采納,再經過文化人加工,就逐漸在《詩經》中反映出來了規矩、制度、法律、禮儀,成為一種風俗習慣,被人自然采納。就《風》的本質來說,“風”本指音樂中的聲調,因為各諸侯國流行的歌曲集合了起來,因此總稱為“國風”,所以“風”也指“風土之音”。朱熹說:“風者,民俗歌謠之詩。” 因此,“風”首先意味著一種起源于民間歌謠和民間風俗的詩歌傳統。
從制度方面說,“風”即風誦吟詠, “風”又特指男女言情之作。在《詩經》中充分體現了男女愛情婚戀詩約50余首,有的是描寫男女之間互相愛慕、思戀的感情;有的是寫婚嫁民俗,有的則寫婚姻破裂關系。比如《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淮南王也有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之說,這種說法與《國風》中男女言情表達感情是一脈相承的,因此,后世也把女男女之情稱為風情或風懷。因此,“風”又意味著一種關于男女之情的主題:《 風》中表達的愛情是自由的,大多數講述的是一種對愛情追求真摯強烈、簡單淳樸、執著、濃烈的態度,其中更有青年男女毫不掩飾感情歌唱心中愛情的描寫。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如這種大膽純真的表白和濃烈如酒的情感,正是人生命欲望和人性本能的自然顯露。
因此,《詩經》中代表社會風情的“風”的音樂性質,其首要目的是政教而非娛樂的。在政教目的大前提下,《詩經》所傳達的美好與領悟,感情與民俗,都是不自覺地完成的。也正因為如此,這些真實的情感與領悟也才更加有血有肉。正如《毛詩序》強調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對詩歌的教化力量作了高度的估價。這就是在封建社會中長期流行的“風教”說,它對封建社會的詩歌及詩論發生過很大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孔維. 詩經的魅力——淺談詩經的現實主義傳統對中國文化的影響[J]. 北方文學(下半月),2011,03:20.
[2]王玉潔. 從《詩經·小雅·蓼莪》淺談孝道文化[J]. 貴州文史叢刊,2007,01:1-4.
[3]鄭婕,孫艷平. 淺談《詩經·唐風》和《詩經·魏風》表現出來的地理環境對人物性格的影響[J]. 華北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03,02:60-62.
[4]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5頁
[5]魏源:《詩古微.檜鄭答問》.《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16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