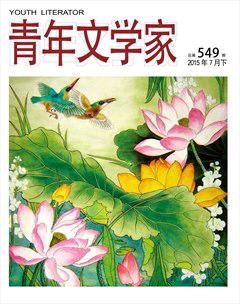東晉玄言詩中的“山水”意象
摘 ?要:自然山水景觀作為一種獨立的審美意象,歷來被文人墨客視為詩歌意境,將其融入詩歌創作當中。尤其在東晉時期,文人將山水風光當做精神寄托和隱逸的終極歸宿。本文以詩歌文本為例,研究玄言詩與自然山水的關系,不僅有助于深入認識玄言詩的詩歌特質,而且便于分析在山水詩全盛之前,山水自然景觀在東晉玄言詩中的角色意義。文章從梳理玄言詩與山水的關系角度出發研究玄言詩中的山水意象。
關鍵詞:東晉;玄言詩;山水意象
作者簡介:郭曉瑜(1988-),女,漢族,甘肅張掖人,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先秦方向,在讀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1-0-01
玄言詩是東晉時期詩歌的主要表現形式,玄言詩萌生于西晉末期,之后逐漸興起在東晉時期發展到鼎盛階段。其產生有兩個方面的特點:一是由于在儒家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為主導的主流思潮的影響下便出現了“理過其詞,淡乎寡味”的玄言詩,此后玄言思想開始進入文學創作中。二是魏晉清談風骨興盛以及與東晉政治大環境下的士人心態的逐漸變化息息相關。本論文的研究角度就是從玄言詩中的“山水”意象的演變過程及通過“玄理”來闡釋自然的文學現象出發,討論玄言詩中的“山水”意象的表現方式。
一、東晉的山水玄言詩
山水玄言詩在西晉、東晉時期的詩歌作品中比較常見。大部分作品中都僅僅從作者詩人的角度提出對玄理的認識,其中都是以“玄理”的理論闡釋詩歌為主,對于詩中出現“山水”意象和玄言互相融合且表現詩歌意境的詩體形式是從東晉時期才逐漸出現并被士人接受,究其原因主要是:
首先,“永嘉之亂”以后,士人遷徙至南方。當時士人生開始適應江南水鄉的生活,其獨特的地理氣候造就了雋秀、典雅的自然環境和溫文爾雅的人文環境。士人觸景生情,由情入理,不禁產生出對自然之美的贊嘆和對自然之道的崇敬。此時的環境正是士人所追求和向往的自然環境與創作心境,于是士人將所見所感上升為理性情感用“玄理”的文字表達出自己對山水之美的由衷贊嘆和折服。這時的東晉正處于政治混亂的時期,但正是由于躲避政治的混亂而追求歸隱自然的士人才能夠創作出這樣的山水玄言詩。
其次,物質富裕、環境愜意的生活為士人創造了更多用心品味自然之美的條件。因為有了充足的物質基礎才使得士人可以有充足的精力和大量的時間怡情于山川之中,并宴飲作詩。
再次,玄學地位在東晉時期更加穩固以至達到鼎盛。鐘嶸《詩品序》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此論述大體上準確地敘述了東晉時期的論“玄理”社會和這種風氣影響下的玄言詩的真實狀況。
東晉的玄學清談往往以山水為背景,詩人們通過描寫山水風景之盛,體悟自然之道,感受人生之苦從而將社會現實隱匿于玄言詩中,期望通過詩中“自然山水”的意境把內心的苦怨和對社會的失望寄托于其中,達到道家所說的道法自然之境。
二、“山水”意象與詩歌創作
東晉是玄言詩發展的鼎盛時期。詠物與玄理之融合手法的運用,將“山水”意象的描寫推向了創作的高峰。“山水”意象作為一種玄言詩的意境元素,它將士人所謂的“天道”觀轉變為人間的山水田園之相。因為對于士人而言,自然山水之中包含著“道”,所以“山水”即作為悟玄理的重要表現手法被應運于玄言詩的創作之中,進而士人大量地進行山水描寫就逐漸成為玄言詩意象的一個顯著特點。“山水”被當作寄托精神之所在。“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山水之美也成了東晉這個時期對于中國藝術和文學的絕大貢獻。” “山水自山水,玄理自玄理,便是未融。玄理意味從山水中來,玄思之于山水,如鹽之在水,無跡可尋,方是已融。”(湛方生)
綜上所述,可見東晉士人運用獨特的處世哲學和生活方式表達對“自然”和“道”的關系的理解以及對人生的思考。玄言詩是以玄學思維方式表現玄學主旨和審美風格的一種詩歌類型。“以平淡之詞,寓精微之理。”這是玄言詩創作獨有的特色。玄言詩因改變了《詩》、《騷》言志緣情、比興寄托的創作傳統而在文學史上別具一格。玄言詩開辟了詩歌創作的一個新的時代。東晉玄言詩更是中國文學詩歌創作中的獨樹一幟。
注釋:
[1]鐘嶸.《詩品》.曹旭.《詩品集注》卷一。
[2]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119頁。
參考文獻:
[1]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19年版。
[2] 田文棠《東晉三大思潮論稿》,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許抗生《東晉玄學史》,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4] 羅宗強《玄學與東晉士人心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寧稼雨《東晉風度——中國文人生活行為》,上海:東方出版社,1992年版。
[6] 陳順智《東晉玄學與六朝文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7] 盧盛江《東晉玄學與文學思想》,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8] 李文初《論東晉的山水詩》,《學術研究》,1986年第1期。
[9] 王鐘陵《玄言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8年第5期。
[10] 祝振玉《對東晉玄言詩的再認識》,《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