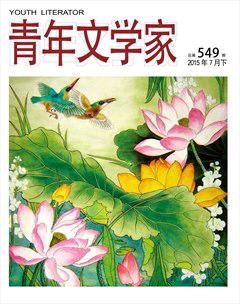論世界文學中的“憂郁”
摘 ?要:在世界文學中,廣泛存在一種文學美學情感——“憂郁”,這種感情纖細,痛楚,給讀者帶來獨特的閱讀感受。拜倫、普希金和波德萊爾筆下的“憂郁”既有相似之處又各具特色,讀之給人以美的享受。
關鍵詞:憂郁;拜倫;普希金;波德萊爾
作者簡介:程靜(1993-),山西陽泉人,臨沂大學文學院2012級漢語言文學2班學生,研究方向:外國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1-0-02
在世界文學中,“憂郁”并不作為一種心理意義上的情緒,而是一種藝術風格,一種獨特的審美視角,一種詩意的情調,能帶給讀者以不一樣的審美感受,雖然它的內容與哀傷、憂愁、痛苦有關,但最主要的還是一種美學效果。以英國詩人拜倫、俄國詩人普希金和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為例,他們三人生活的社會背景及他們的個人經歷,造成了他們作品中以“憂郁”為基調的不同表現。
拜倫生活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國,這個時候正處于歐洲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拜倫出生在1788年,在1789年,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統治,這次革命給整個歐洲巨大的影響。英國雖然一百多年前就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但結果卻是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勾結在了一起,資產階級并沒有占據統治地位。拜倫雖然也是貴族中的一員,但他屬于沒落的貴族,他雖然獲得了爵位,但并沒有什么金錢。加上拜倫深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同情民族解放運動。就拜倫生活方面來說,他的父親是一個浪蕩子,后來拋棄了他的母親,以至于他的母親深受刺激,經常遷怒于他,苛責凌辱,再加上顛沛流離的生活,他的童年很不幸福。他天生微跛,這種與生俱來的缺陷使他形成了敏感、孤傲的反叛性格。拜倫的愛情之路也十分坎坷,最開始他喜歡自己的表姐瑪格麗特-帕克,但其因受傷很早就離世,后來又愛上一個叫查沃斯少女,可她嫁給了一個貴公子,18歲和一個叫伊麗莎白的姑娘戀愛,也沒有成功,第四段愛情是與塞莎在一起,他為她寫了許多詩,但塞莎卻在熱戀中病逝,這對拜倫是一次次的打擊,直到1815年,27歲的拜倫才與一個貴族小姐結婚,但也很快因為思想觀念的分歧很快分手。由于他的政治態度引起上流社會的不滿,就借他不幸的婚姻生活對他進行誹謗和打擊,而拜倫也開始流亡生涯。這所有的一切都是拜倫憂郁的緣由。
《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是拜倫游歷歐亞一些國家后寫的,其中塑造了第一個“拜倫式英雄”——哈洛爾德——他孤獨、憂郁、悲觀,出身于“顯赫過的家族”,“整天在花天酒地里沉淪”,身邊多是一些“登徒子和情婦”。他并不愿意這樣生活,“心里十分苦惱”,“孤獨的懷著憂郁的思想”,處于痛苦之中。也促成了他的外出游歷,他漸漸對歐洲的現實越來越不滿,感到人情淡漠,世態炎涼,知音難覓,沒有一個人“真心地愛他”,憂郁的情感一直沒有消失。《海盜》中的康拉德也是一個孤獨憂郁的形象。他雖然是一個海盜,但他光明磊落,即使在有性命之憂的時候,完全可以殺死敵人的時候也不愿意這樣做;有同伴遇難,他一定會舍命相救;對于愛情他也純潔,忠貞。但就是這樣一個正直、勇敢、誠信的人,卻成為了海盜,就反襯出了這個社會的黑暗。
普希金受到拜倫的影響很大,但普希金的憂郁則表現得更為明朗,正如他所言:“我憂郁而輕快。我的哀愁是明朗的。”普希金生活在俄國解放運動第一個階段——貴族革命時期,這個時期進步力量是以十二月黨人為代表的貴族革命家。普希金雖出生于一個貴族家庭,但他受到當時進步思想的影響,在讀書時就與未來的十二月黨人交好,寫下了許多揭露沙皇統治的暴政,描寫農奴悲慘生活的政治抒情詩,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這也觸怒了統治者,對他進行了流放,后來又在他父母的領地有過一段軟禁的時期。在個人生活上,早年他暗戀著娜塔莎,后來在對艾麗溫娜狂熱的愛及后來的離他而去,讓他陷入深深的悲傷之中。之后在皇村碰到奧加遼娃,前幾次愛情的失敗已經使他無法再鼓起勇氣表白了,但是他的羞怯和懦弱使他感覺更加痛苦。但是普希金本身就有對生命有著無比的熱愛,而且他相信光明總會勝利,他一直以一種積極的、樂觀的態度去面對生活,對未來充滿了信心,這也成了他詩歌的基調,蘊含在他詩歌的憂郁之下。
例如在《致凱恩》中,“煩囂的日子重壓著我,我沉郁的心充滿了憂患。”但詩人并沒有陷入痛苦的深淵,在憂郁的情感過后,“但是,你的玉容和溫柔的聲音,卻久久縈系我心間”“我的心在歡樂的激蕩,因為在那里面,重又蘇生。”他沒有一直渲染憂郁的情緒,痛苦的心情,在詩中,情緒是多重的,有痛苦,但也有歡欣和快樂。又如在《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中,他鼓勵人們不要在悲傷憂郁中沉溺,而要鼓起信心和勇氣,面對生活,生活中雖然有悲傷,有挫折,但不能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別林斯基說過,“普希金的憂郁不是溫柔脆弱的心靈的甜蜜的哀愁,不是的,它永遠是一顆堅強有力的心靈的憂郁。”例如《哀歌》“那荒唐的歲月,已逝的歡樂重壓著我,有如酒后的昏沉,但過去留下的憂郁,和酒一樣,在心靈愈久,卻變得愈醇。”雖然詩人生活艱辛,但他并沒有絕望,“然而,我的朋友,我還不愿死去,我要活著,可以思索和苦痛,我知道,我也會有種種樂趣,在憂思、悲哀和煩躁之中。”體現了他的樂觀與堅毅。
波德萊爾生活在十九世紀的法國,這一時期的法國乃至整個歐洲,隨著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的確定與鞏固,內部矛盾日益尖銳化、明顯化,整個社會都充滿著銅臭味。在家庭方面,他的父母是相差三十五歲的老夫少妻的畸形婚姻,童年喪父,母親改嫁,他與繼父的感情也一直不好,繼父嚴厲的管教使敏感的比德萊爾陷入深深的孤獨之中。后來被送到寄宿學校,使他更加孤獨和憂郁。后期波德萊爾的生活拮據,債務纏身,還有神經系統的疾病,這些都造成他的憂郁。
波德萊爾憂郁的主要表現在《惡之花》中的《憂郁之四》中,其中表現最多的就是各種丑惡面。詩中有很多壓抑的意象,例如“低垂沉重的天幕像鍋蓋,壓在忍受長久煩悶、呻吟的精神上。”將天空比成一個低而沉得鍋蓋,扣在人的心上,把地也嚴實的扣上,給人一種透不過氣的感覺;“向我們傾瀉比夜更悲的黑光。”“黑光”也和憂郁密切相關,給人一種悲傷、壓抑、恐懼的感覺;還有“一長列柩車沒有鼓樂作為前導,從我的心靈緩慢的經過”,柩車本就是哀傷的象征,沒有鼓樂,更顯悲涼。這種類似的意象還有牢房、蝙蝠等等,這些意象以實寫虛,以有實的意象寫無形的感覺,使憂郁這種抽象的,無形的心態以具體的方式出現,也使讀者能對其中的憂郁感知的更為明確。波德萊爾的詩中也有對于“死亡”描寫,例如《遠行》:“哦死亡,老船長,起錨,時間到了!這地方令人厭倦,哦死亡!開航!如果說天空和海洋漆黑如墨,你知道我們的心卻充滿陽光!”這些關于死亡的詩句也與他的憂郁的情感相聯系,用來抒發詩人的憂郁情懷。
在廣闊的世界文學中,“憂郁”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文學現象,雖然它作家們所處的時間不同,國家各異,但對于世界和人生的感受造成了他們共同的“憂郁”風格,為文學世界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也為讀者提供了獨特的閱讀感受。
參考文獻:
[1]鄭克魯.外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張潤.漫談俄羅斯文學中的憂郁情緒[J].雞西大學學報,2011,(5).
[3]波德萊爾.惡之花&巴黎的憂郁[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4]普希金.普希金抒情詩全集[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
[5]楊崇華.拜倫的憂郁和他筆下的人物[J].駐馬店師專學報,19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