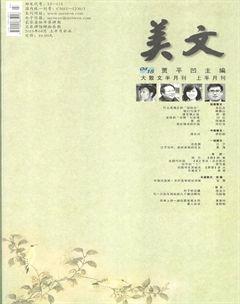村子的邊疆
龐永力
青壯時的逃離,莫非就是為了如今的惦念?
——題記
血脈龐雜
將近半年的時間,我總做為別人尋祖覓宗的報道,那些名門望族之后,一臉執著,家譜幾十代,正宗旁支,滿心光宗耀祖的念頭。國人總有這個情結,我亦難免。龐姓屬偏姓,我家上推幾代亦無顯赫,爺爺去世太早,我連他的大號都不知道,去年回家專題詢問老爹——他也垂垂老矣,一些東西已經記不清了。之后寫出一篇千余字的《家史簡述》,爺爺叫什么,所掙家業如何,還有奶奶、姥爺、姥姥——那些賦予我血緣如今永逝不再了的人。也只能如此。我又去查姓氏起源,龐姓很古老,姓氏源流有六,其中顯赫當屬黃帝之孫顓頊的后代,還有周文王受封龐鄉之孫;我祖籍蠡縣,源流應屬高陽氏,得姓始祖為顓頊之子龐降。皇胄正統,好了,得以滿足了。
在國家推行計劃生育國策之前,每個家族都是呈幾何倍數增長的,以一代三子計,三子九孫,九孫二十七重孫……像張王李趙這樣的大姓,至今已過億人,遍布寰宇。計劃生育后這種宏愿盛景就難以實現了:“只生一個好”,一對夫妻一個孩兒;兩個孩兒結婚,再生一個孩兒,人口是呈幾何倍數銳減的。
地球資源緊張,人口是需控制,但計劃生育至少滋生兩個問題:一,絕戶,以前以無子嗣為絕戶,女兒生的外孫、外孫女是外姓,姓氏無以為繼,身后有誰祭祀都不知。只生一個孩子,你這代生兒子了,下一代難保不是女兒,此代不絕,下代也懸。二是稱謂絕跡,一代一個,弟兄姐妹沒有,以此伸延的叔伯姑姨舅也完了,還有他們的配偶,嬸大娘姑父姨夫舅媽,何為連襟,哪是妯娌?以人種、養老計,竊以為還是生兩個孩子好,最好一男一女,人口漸減,社會傳統觀念不至于巨變。
當然,女兒也是傳后人。在血緣上,女兒有女婿加入,兒子還有兒媳摻和呢!僅以我論,龐氏之外,還承有奶奶的孫氏、姥姥的李氏、姥爺的邊氏之基因,血脈早就混雜了。古時為姓,有封地的,有官爵的,也有避禍改姓的,曲曲折折、蔓延四流,難尋增長與消減的規律;如細究,意義又有多大呢?
村子的邊疆
回家,從城里空出兩三天,回到父母身邊。在這個村子長成,二十歲后開始往外躥,如今也有二十年了。這是爹娘的家,他們六七十年在此。除了看望,回家就是復習、憑吊。
那條小白河穿村而過,它只是一個溝了,干涸三十年,偶爾來幾天水,它也過節一般的驚喜。我們也算鄰河而居,那座石橋大我三歲,順著河坡走,西南是上游。出村,林子、秋田、荒草、孤墳,一個小村子的邊疆,很多地方從未踏足,還妄論游遍高山大川呢?東南西北走遍,這里很多景致仍不能被等同、替代,一副兀自存在、誰都不理的孤僻神情。
石橋向東北,姥姥家在村東口,她埋在了河南,與家隔河三百米之遙。循著少時記憶走,很多屋舍前的人叫得出我的小名。出村,便是少時耍鬧的“戰場”:兩三個村的上百個孩子,分成兩派,以河為界,喊殺聲一片,泥丸、土坷垃亂飛——那時的我彈弓玩得不好,土坷垃扔得遠而準,充任小隊長。再走,污水一段;不遠處,城鎮已入侵過來。
走了一遭,獨自一人,與上萬棵樹相見,與億兆塵埃相見,似曾相識,期期艾艾。
齊步走著
出差,住在酒店,忙了一天,臨睡前頭腦才得以安靜下來。這個夜,妻女在另一個城市,爹娘在村子里,大概也都睡了。一些外在喧囂經過一天的蒸騰,虛無得遙遠而飄忽。生出一些惦念來,這些血脈親人分布在世間,雖然彼此有些距離,但他們都安在——這恐怕就是每日絞盡腦汁、蒙受仰面之羞的終極價值吧。
人活著大致有兩種認知:有人剛一掰眼兒就開始爭,他們的人生是一個空落落的筐,每日想著如何填滿;有人卻以為嬰兒呱呱落地是完滿的,成長的過程中飽受紅塵的侵蝕、劫掠,直至赤裸裸身無一物地死去。二者各有各的出發點,匯合到一個人身上,大概是壯年為前者,不惑之后感悟后者了。
血脈親人間,也有前緣修定與緣分終了,每一縷的失去都是撕扯。奶奶故去十五年了,爹如今也七十了,前些年他在睡前忽然念及,嗚咽著:“俺沒娘了!”姥姥也活到八十多,因為小腦萎縮與跌傷,后幾年受了活罪;前不久娘也跌傷,在炕上翻身不易,忽然淚下:“你姥姥那會兒不定多疼呢!”每年都給奶奶上墳的,作為外孫沒有給姥姥燒紙的規矩;她就睡在村東口,每次從城市回來進村我都摁兩下車喇叭,告訴她回來看她了,住幾日回去時也摁:“過些日子再來!”
雖然如此,最終還是要放下的。這幾日血壓飄忽,先是惶恐、委屈,漸漸就適應了。人非常在意周遭的比較,獨自好、獨自壞都是不被容忍的,大家都齊整整朝著一個方向走,到最后差不了多少。前幾年,一位老鄰居去世,歲數不大;我很在意娘的感受,她卻避而不談。我現在有些明白了:娘也老病許久,身邊人的故去就變得不那么難以接受了,人被掠奪得所剩無幾時,反倒平靜了,大概已經把結束看做另一個開始——重聚不遠。
那些同缸共鍋的日子
俗語云:“皇帝也有三門窮親戚。”窮親戚、富親戚,這兩個定語在前面一掛,就有功利、薄厚在里面了。《菜根譚》言:“饑則附,飽則颶;燠則趨,寒則棄,人情能患也。”在利益、成本之外,親情只是親疏的因素之一罷了,或多或少,自覺不自覺的。譬如同樣兩個表哥,一個做官兒、一個務農,一個出手闊綽、一個上門求助,對待二人自然會不一樣:闊表哥來了,至少會拍拍座椅上的塵土,這樣細節上的重視,可能連你自己都意識不到。對于闊表哥,自家是窮親戚;而對于窮表哥,自家又是富親戚了。親戚間可以幫忙,可以施予,有的是主動自發的,但也會有意無意地流露出高姿態來;有的是無奈推不開,更會有掩飾不住的膩煩。
所謂親人,皆在血脈也。以血脈為核心,一層層的圈子,最小的最緊密的,就是父母妻兒,這是倫理親情的中心,是每個人的責任田,不僅有道德約束,從法律上也有剛性要求。次之是兄弟姐妹,從一個娘肚子里爬出來的(也有同父異母、同母異父的,此處忽略不提),成年前都在一個屋檐下住著,一口鍋里吃喝;長大后各自成家,分出去幾根枝杈,父母還是共有的,配偶子女卻不同了,空間也就拉大了。在同一間屋子里,共用一口飯鍋、一個水缸,再怎么鬧也散不了;有了空間就不同了,各自添置了飯鍋、水缸,可以不臉對臉、背靠背了。各自成家了,有了新的同鍋共缸的人,心也就分到新的成員身上,有了新的擔當。
再往下,就是叔伯姑舅姨家的弟兄姐妹了,又差了一層,標志就是不曾同鍋共缸。叔叔伯伯尚是本姓當家,自古喪事以孝服不同分親疏,由親至疏依次分為五種: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親族往上推五代,高祖、曾祖、祖父、父親、自己,出了“五服”,血脈稀釋得又可以通婚重來一回了。而姑媽、舅舅、姨媽的子女,都不是一個姓氏了,只能一表再表,倒是有一句話可以安慰:“姑舅親,輩輩兒親,打折骨頭連著筋。”
有一句話論及親戚頗為精準:“一層肚皮一層山”,說的就是離那些同鍋共缸日子的遠近。一代代的人,親近而疏遠,疏遠又親近,構成一個村莊、一個家國。
慶生
午后落了些小雪,到傍晚天還是放晴了,一輪圓月靜浮在東邊的樓上。昨天也見過的,剛出來的月亮,滾圓、濕潤。已是真正的冬,冷寒中皎潔無邊的月色,得感謝爹娘,在這個日子把我送到世間。也得回顧一下自己,已經度過了四十個春秋。
農村過生日是講究陰歷的,算歲數按虛歲不按周歲,周歲的計算大概是上半年出生的減一歲,下半年出生的減兩歲。算法的差異,使農村的孩子稀里糊涂地老大了一兩歲。這幾年,我也不糾纏這個,被人問起,就統稱“都四十啦”,就好像入秋的莊稼,快熟了與剛剛熟沒有什么區別。所以我的前幾年及今后幾年,都可稱為不惑。
不惑,好像一下子就躥到了一樣。發達的人早積累了一定的財富,而我與廣大的凡人一樣,別無選擇地積累了年頭。掐指一算,很多記憶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也不太敢往以后預言,再過二三十年,自己不知已老朽成什么樣子,心里沒底。每年都忙忙活活,干的也算新聞“公差”,十幾年寫了一二百萬字;自認為事業的寫作,也投身其中二十多年了,也留下了一百余萬字。尚不至自棄的地步,仍然樂此不疲,說來也算“百萬富翁”了。
這幾年一直寫“青黃不接”的主題,曾感慨那些文字“使我老了五歲”,這四十年的時光,特別是揖別青春、幻夢破碎后的二十年,期間有多少掙扎與沉淪,又不知已老死了多少回!
生日快樂。自己在心里對自己說。一下子想起一句歌詞:“有生的日子天天快樂,不必在意生日怎樣過。”那是當然。我順下去想:有生的日子天天不快樂,也不必在意生日怎樣過。當然,生活雖然不是少時預期的那樣順滑,也不會悲催到什么地步。這一天,只是應該對爹娘道一聲謝,讓他們重又想起:他們在這個日子出生的兒子,已經越漂越遠啦。
沒有悲喜的時光
人到中年,許多情緒就飛揚不起來了,平緩、暗寂,像現在初秋午后的時光。在樓后的園子里,陽光從西面照射過來,透過樹枝和葉子們,迷離、斑駁,其實也算美的,主要看獨立人的心情罷了。
記起范仲淹的名篇《岳陽樓記》:“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作者描摹出厄境、美景兩種狀態,把人的內心搞得迥然不同。外界的陽光、風雨投注到內心,引來溫馨、歡喜,抑或憤懣、絕望。文人大多喜春傷秋、心隨景去,但于此之外,更有景由心生的時候,至悲至喜兩種心境,亦可改變眼前風景的:單以秋雨論,不同心境之人看來,便有纏綿悱惻與凄涼蕭索之分。
一些小蛾蟲在光線里飛舞,細小如塵埃,它們卻是有生命活力的。相比之下,一些更為鮮活、更為立體的卻逝去了,人的神經疲敝了,連懷念也模糊了。其實蛾蟲更有生死替換,我們的一喜一悲之間,它們不知已多少世代了。只是,我們看不到它們的悲喜,就認為它們沒有悲喜——即便有,也大可忽略了;所以我們反倒羨慕它們,覺得它們在沒有悲喜的時光里,又該是多好啊。
你管我叫啥
早起,第一時間奔廁所,坐在馬桶上,卻想起一個悠緩的話題:你管我叫啥?
琢磨的就是以血緣為基礎派生出的稱謂,我經常在腦子里盤桓一陣兒這個問題。小時候在村子里,爹娘總教導:“見面要叫人兒,別蔫兒不拉幾的,別弄差了輩分。”他們還經常講解,該給誰叫啥,他是咱啥的啥。也有串門兒的考我們:“你管我叫啥?”如果把該叫叔的叫成了舅,該叫奶奶的叫成了嬸子,就會得到溫和的糾正,他們有這個耐心。
現在想起來,那就是農村啊,三鄉五里、連洼帶地、四姑七姨,不像城市里的鋼筋水泥,對面不識,誰也懶得搭理誰,也不用怕做下什么孽事被人嚼舌頭、戳脊梁骨。
現在的家庭大多是獨生子女,稱謂更已模糊,記得附近幼兒園經常放一盤童聲磁帶:“爸爸的哥哥叫伯伯,爸爸的姐妹叫姑姑,爸爸的爸爸叫爺爺……”諸如此類,這是最簡單的,要連這個都迷糊,那真的頭腦嬰兒了。叔伯姑舅是最近的親戚,計劃生育當然利國利民,但副作用之一就是孩子們會逐漸不知“叔伯姑舅”為何物。叔伯姑舅是普通話,還有方言的叫法,我們那兒給爸爸的哥哥叫大爹(爸爸的表哥、非血緣哥哥叫大伯),爸爸哥們兒多且排行小的話,就大爹、二大爹、三大爹往下排;東北叫大爸、二爸、三爸——北京叫大爺,經常爆粗口:“你大爺的!”想不通,這能有什么倫理上的殺傷力?
我經常順著輩分思維往下排,那些彎彎繞兒難叫的,譬如:爺爺的姐妹叫姑奶,奶奶的姐妹叫姨奶,姥姥的姐妹叫姨姥,姥爺的姐妹叫姑姥——想著這些稱謂,我的腦海里就會浮現少時在村子里遇見的那些張滿是皺紋的臉。還有,叔叔的老丈人得隨著堂弟叫姥爺,姑姑的小叔子隨著表弟叫叔叔——隨著思索火力的延伸,一時很寬闊,很有快感。
諸多關系,也有遠近之分,譬如論爸爸這邊叫人家哥,論媽這邊就叫人家舅了,怎么辦?看遠近,哪邊血源近隨哪邊。也有單論的,兄弟歲數相差不多,卻是叔侄爺孫之差,處得親密了,可能夾雜在一群人里拜了盟兄弟——當然,這叔侄爺孫得夠遠,嫡親一兩代的長輩你倒是敢?
出外凡二十年,也有稱謂上的驚喜。一次單位招人,一個應聘女孩與我同縣同鄉,她打電話問家里,她媽說:“那是你表哥呀!”一論,她的姥姥是我姑奶奶,是我爺爺的親妹子,她媽媽跟我爸爸是姑舅表兄妹!住得遠、歲數差得多,在老家幾乎沒見過;她在我寄居的城市求學三年,我們對面不識。
前兩天去外地,一個朋友找了一輛車,開車的司機一開始這樣說:“我姐夫讓我來接你。”后來彼此話多了,又說:“不是我的親姐夫,是我親姐夫的親姐夫。”我立馬兒開始盤算,稱謂“原路返回”的話,司機就是朋友的親小舅子的親小舅子,也就是說,朋友的妻子是司機姐姐的大姑子。頭腦一轉,還是找坐標的問題:有一個孩子,給我朋友叫姑父,給這司機叫舅舅!一時順暢,什么姐夫小舅子的,把人家都繞暈啦!
家史簡述
我爺爺名叫龐冠英,下面有倆妹妹,因為是家中獨子,受寵,小名可意。他屬馬,與清末帝溥儀同年,應為1906年生。一百年前,我曾祖那輩兒,從蠡縣東五夫村搬來,那村半村龐姓,到肅寧縣袁家佐村,倆村相隔幾里地,目前分屬河北省的保定、滄州兩個地區。我爺爺生于袁家佐,我父親、我、堂弟之子,算來已繁衍四代人了。
我曾祖與人合開煙鋪,不是大煙,是加工旱煙葉子。待我爺爺長大,社會發展,開始做卷煙;解放初,爺爺與政府合作開辦卷煙廠,算是實業家。爺爺不善務農,有商業頭腦,積攢下幾十畝地、兩套院子外加場院的家業。我爺爺與我大奶奶育有二女一子,大奶奶去世后,娶我奶奶,育有二女三子,我父親龐五岳大排行第五。
我奶奶是肅寧縣城李牛軍莊村人,名孫卷(又名秀蘭),我姨奶奶名孫經,可見外曾祖起名之意。奶奶屬鼠,小爺爺六歲,識字,常謂我“結婚那年日本鬼子進城”,后幾經運動驚嚇,膽小多疑,于1999年夏天八十八歲高壽去世。
我爺爺具備經商頭腦,日子過得較為殷實,建國初期,土改定成分,反遭打壓;家道衰落,他也是踅摸著賣柿子、販魚、推煤油,以小買賣貼補家用。小時候聽爺爺的同輩人說他,付得下辛苦,有頭腦。父親曾說,爺爺與人搭伴去保定上貨,推小車,抄小路走也有百里;子夜動身,天亮到清苑,上午上貨,推著趕回來又是深夜了。一天二百余里,步行推貨,是現代人不能想象的。爺爺應該好吃,卻算計得很到位:出門在外,自帶干糧,饞了在集上稱上一斤肉,給飯鋪倆火錢,借人家鍋做得美味。
有家業,農忙雇人。有倆村人干活兒偷懶,地頭長,耪地只耪兩頭兒,我曾祖母顛著小腳驗看,兩個地頭兒都看了,就算完工。多少年后,龐家家道中落,二人的女兒卻先后嫁了過來,便是我的母親與四嬸。家境好時,爺爺供養著子女,還有他鄰村的外甥——日后成為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的楊嘯。可能正因為勤儉置業,在土改中被劃為富農,幾經運動清算,家產被分,幾十年不得抬頭。
所謂地主富農,有些像現在的企業家,在專政年代,曰剝削、壓榨,但沒有頭腦、不付辛苦,何以發家?農村小民,辛苦置業,牙縫里摳錢,也未見幾個如黃世仁、周扒皮欺壓鄉鄰萬般歹毒。有戶鄉鄰原比我家殷實,當家的吃喝玩樂,敗了家,倒被劃為貧農,根紅苗正。任丘作家李富強著長篇小說《萬各莊》,涉及土改劃成分,塑造了一個勤勞持家的富農形象、一個好逸惡勞的貧農形象,在社會大環境下,二者順逆立變。這可算做當時階級成分大運動的一點兒弦外之音。時過境遷,父輩被殃及所經歷的歧視、屈辱,我沒有太趕上,所受影響也不是那么直接——人云“貴族三代養成”,家道興衰所帶來的影響,遠非短暫歲月所能消除的。我也不想考證、推翻什么,只是想起爺爺,我倒為他的努力、聰慧而自豪。
家道在運動中衰落下來,雖然爺爺從未失去他的頭腦與辛勞。1960年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下爺爺也全身浮腫,終于沒有熬過,在睡夢中昏迷,沒有醒過來,沒有留下一句話。其時,父親十五六歲未成年,最小的四叔才三歲,奶奶帶著幾個子女辛苦度日。
我爺爺未能安享子孫繞膝的晚暮之樂,我也從未見過他,不知有爺爺是何種滋味。爺爺去世后,父親跟隨他姥爺學中醫,二十來歲看病,成為赤腳醫生,屬羊的他至今行醫已快五十年了,仍在本村開診所懸壺濟世。我也沒有太多商業頭腦,棄農、疏醫,跳出農村,混掙都市,勉力從文而已。時值2012年中秋,爺爺的輝煌與悲慘均已煙消云散、不留痕跡,老宅或翻蓋,或斷壁殘垣,很多東西就連父親都記不準了。而我作為他的孫子,如不特意詢問、查實,真的連他的大號、生卒都不知,對于那點遙遠、纖細的血脈,連如此簡述都沒得做。
父子倆正聊著,母親過來。母親屬虎,1950年生,名叫邊曼女——農村小民,落后封閉,不像現在材料證件齊全,時刻備查;加之村人把小名、別稱叫熟,還有“為長者諱”,不能直呼長輩姓名的,如不當回事兒記述,還真不得而知呢。問母親,得知我姥爺名叫邊化民,屬豬,1923年生,肅寧縣東泊莊村人,少時住袁家佐姥姥家,后落戶。我姥姥名叫李秀閣,屬牛,1925年生,亦為東泊莊人,嫁了過來,故我是當村姥姥家。姥爺老實本分,日子過得清貧,他于1989年去世,那時我尚懵懂;姥姥于2011年初去世,我業已年近不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