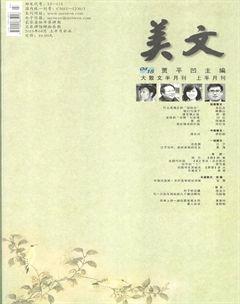向散文中有價值的真人致敬
王冰
一月份的文學刊物里,讀了一些記人類的散文,除了祝勇的《再見,馬關》(《江南》第一期),鄭驍鋒的《出新安》(《江南》第一期),程川的《憶江南》(《花城》第一期),李元洛的《矛盾的靈魂人生的苦酒》(《湖南文學》)等幾篇外,其他散文中的人物,我覺得還是有著較大問題的,主要是進入散文的這些人物有價值嗎?他們的經歷和經歷帶出來的個人苦痛,里面有時代的大悲歡嗎?這種悲歡有足夠的理由進入到散文寫作中去嗎?一個作家將一些人物寫入自己的散文中,如果僅僅是抒發了自己的小小的喜悅與憂愁,那么這些喜悅與憂愁與我們相關嗎,我們為什么去讀它?他們能喚醒我們對于過往的記憶嗎?他們能帶給我們一種啟示嗎?或者能夠滿足我們小小的閱讀快感嗎?如果沒有,那么為什么要在散文中寫這些人物?于是我就覺得更有必要來說說散文中的人物。
一直以來,散文中記人的寫作占了很大比例,往前推,比如魯迅的《藤野先生》《范愛農》《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記念》,比如豐子愷的《懷李叔同先生》、葉圣陶的《兩法師》、梁衡的《覓渡》、季羨林《我記憶中的老舍先生》、史鐵生《二姥姥》、冰心《小橘燈》等;近年來的,比如蔣子龍的《人書俱老》、李敬澤的《小春秋》、江子的《井岡山往事》、從維熙的《浪人傳奇》、孫郁的《〈民報〉拾趣》、吳克敬的《放生法度猿臂翁》、陳恭懷的《閃亮的白帆》、程紹國的《黃宗江二題》、聞舞的《丹柿小院與老舍的割舍》、周樹山的《我的父親母親》、馮淵的《小簟輕衾各自寒》、北島的《父親》等。如果說這些散文作品中所寫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我們所共知的一個常識,他們寫的都是真人。而這些真人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情感價值、道德價值都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給人足夠的沖擊、警醒或者感動的。在散文中,這樣的人物就是有價值的真人,正是他們對于散文的進入,使散文有了自身本就具有的重量,散文寫作是需要這一類真人的出現的。
為了更清楚地將這個問題說清楚,我們先說說散文中的真人。一般而言,對于上面所說到的散文中的真人,大體有顯性的真人和隱性的真人之分。
顯性的真人,就是散文作品中所寫的人物,都是在現實中真實或者活過的人,都是真人。既然是真人,那么他們的真生活真經歷是不能杜撰的,對于他們生平經歷的抒寫就是對于這個人物個人史的描述,散文只能在回望的系統中真實記錄,最多在一些細節上在尊重真實的基礎上做出一些想象,進行合理的細節還原,所以散文中的真人只能描述,無法塑造,雖然它也必須經過取舍和藝術化,否則文章就會寫成真人的生平介紹,而不會是作為藝術品的散文了;當然散文對于顯性的真人的需要并不是迫切和必須的,是可以疏離甚至沒有的,散文中即使沒有這些真人,也一樣能夠成型,它能夠靠情感,靠描述,靠景物等來完成整篇散文的創作,而且是很完整、很優秀的散文創作。
散文中隱性的真人,是指在散文的有限時間和空間里并不出現的那個人。謝有順教授有一篇談散文的文章,題目就叫《散文的背后站著一個人》,隱約記得也是發表在十年前的《美文》上,雖然類似的觀點早在清初,著有《圍爐詩話》的昆山吳喬就提出來了,吳喬認為,詩文要“有人”,“詩中亦有人也”,但我依然一直覺得謝教授寫得好。應該說,隱性的真人雖然在一篇散文中是隱在文字之中的,但他又確實是無所不在的,他的修養品質的高下決定著文章的品質品味。如果在散文中呈現出的文字是一片為人所見的水域的話,那這個人就是隱藏在水面之下的蘆葦,那是一棵思想根基和文化根基的蘆葦。因此,散文的字里行間到處都彌散著這個人的氣息,隱藏著這個人的背影。比如郁達夫的《感傷的行旅》中的那個隱性的人,是一個走在江南,感懷人世的人;《釣臺的春晝》中的那個隱性的人,是一個胸中有山水神奇的人;冰心的《到青龍橋去》的那個隱性的人,是一個難以忍受壓抑的人。今年《美文》第一期上的張怡微的《水城一春今日盡》的那個人是一個穿梭在臺北的古典女子,馬敘的《過去的,現在的》的那個人,就是一個被歲月侵蝕撕扯的一個人。“文如其人”在這類散文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文章的價值在于這個隱性真人的價值,文章的境界在于這個隱性真人的境界。
在這兩類散文中,還有一個尤其重要的因素是,散文中的時間和空間也必須是真實的,散文中的時空都是不能設計的,而是真實的存在。如果說散文中的人物只能是真實的人物,那么這個真人物必須活在真實的空間里,否則真人生活的土壤就會失去,最終也將失去散文中的這個真人。應該說,一篇散文是由這些真人和真實時間、空間合成一張真實的生活場景。
如同文章開始所談到的,對于真人的散文寫作相伴而生的一個問題是,散文中所寫的真人都有價值嗎,比如自己的父母,比如自己的朋友,也許對于個體而言是有的,可以寄情托意,但對于別人呢?估計很難說,我們為什么要讀一篇散文,他給我們的啟示是什么,這個真人給我們提供了什么嗎?因此,寫好一個被人喜歡、被人記住的真人確實很難,但大多數作家在散文寫了很多人物,我們卻再也找尋不到他們任何的蹤跡,這確實也是散文寫作者值得反思的事情。
對于一個散文寫作者而言,如何寫出有價值的真人,這是散文寫作的一個基本難題,但往往越是基本的問題,越是無人去認真思考。一般來說,散文是來記述舊物的,寫散文基本都是往回看,但是,就像不是所有的老東西都是古董一樣,不是任何古董都值銀子一樣,能進入散文的人物也不是所有的都合適,也許有例外,但要看寫作者的本事,看他是怎么去對這個人物進行寫作上的處理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再次先不談。
縱觀近十年的記人類散文,幾乎進入到散文的,不是一些臉譜化的形象,就是一些個人化太重的人物,他們與讀者是沒有多大關系的。所以當作者或激情滿懷,或悲傷落淚的時候,讀者對此卻覺得沒有意思的很,原因在于讀者期待看到的是散發著價值氣息、藝術氣息的散文作品,而不是與己無關的作者的個人幸福史和苦難史。因此,我們要在散文中描摹怎樣的人物,為什么這個人物會進入我們的視野和作品中去,也是考一個作家的眼力和審美標準和判斷標準的。
在散文創作中,無論是以上哪一種,我們是要在散文中通過真人去找尋真人的,所以這個真人在散文中,不是魯迅先生所說的,“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不是別人的合成品或者替代品,不是抽象化了的形象、代碼或者符號,不是像小說一樣塑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人,而是寫一個有價值的真人。這個真人在現實世界中或者體現人具有所追尋的理想和境界,或是給人一種警示作用,這個人物是對于人的破壞與修正,都是有著現實存在意義的,他體現著寫作者一種獨特的寫作價值,我們將用這個真人來塑造后世的人的精神,因此我們要向這樣的真人致敬,因為他們有價值,有思想,有肉身,體現著我們對于我們自身的認識和把握。
與之相關的,最后來說說我們的肉身,散文中寫到的是真人是真實的,所以他首先具有真實的肉身,這是一具能夠承擔現實苦痛酸甜的肉身,這是很關鍵的。但是在當下的寫作中,真正去關注和抒寫人體肉身的作家依然不多,也似乎還不到位。身體是多么重要啊,裝滿我們的血脈、思想和靈魂,但身體卻都被我們健康的散文家忽略了,常常被忘記在那流淌的時間深處。那么,當我們的身體漸漸干癟瘦弱,當我們的肉身隨著時間逝去,我們還有地方承載我們的各種想法和欲望嗎?于是有些散文家開始關注我們存在的最為關鍵也是作為基礎的身體,開始了對生命和時間、身體與魂魄的思索,并有所體察和覺悟:身體太重要了,但他確實又是太切近了,切近到了它會用時間將我們漸漸壓彎,但我們現在似乎麻木到無力去做絲毫認真地思考。于是應該是到了我們的散文家將眼光適當地收回的時候了,去直接面對我們的眼睛本身,胸膛本身,四肢本身,肝脾本身,心臟本身、大腦本身,這對于我們肉身的寫作也許會有更為切實的意義。
讓我們要選取一些有價值的真人去寫,讓我們向散文中的有價值的真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