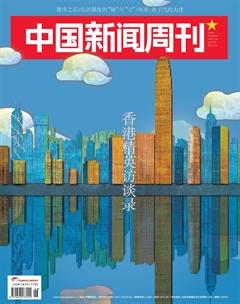李秀恒:共同把蛋糕做大
徐方清
在深圳各個往來香港的口岸,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內地旅客拎著大包小包歸來。而在改革開放前,拎著大包小包進入內地的幾乎都是香港人。
61歲的李秀恒祖籍廣東清遠,他至今還記得,年少隨父母回老家探親的情景,雖然家里并不富裕,但每一次都是大包小包地要拿上很多禮物。
改革開放后,很多香港人來內地不再只為了探親,而是投資興業。1987年,李秀恒在深圳坪山開建工廠,成為其中一位最早投資內地的“吃螃蟹的人”。
在李秀恒看來,和三十多年前大不一樣的是,以前投資內地還要教內地人怎么做外貿,然而如今,“香港經濟要跟著內地經濟走,因為內地的經濟體量太大了,內地需要什么,我們就要提供什么,而不是由香港來主導內地的經濟發展。” 在位于中環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大樓的辦公室,李秀恒不無感慨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李秀恒如今的身份,不僅是旗下多家企業的老板和董事,也是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的會長。創立于1934年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擁有各行各業的會員超過3000家,是香港四大商會之一。
從上世紀80年代初創業至今,打工起家的李秀恒發展成為身家百億的香港“鐘表大王”,并坐擁酒店等多個產業,而30多年里,中國也從改革開放之初的經濟貧弱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個過程中,香港和內地的經濟關系也經歷了一次反轉。
“不是由香港來主導內地的經濟發展”
2015年5月中旬,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等機構在香港中環發布了《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2015》(《城市競爭力藍皮書》)。報告稱,2014年全國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第一位被深圳奪得,香港、上海和臺北緊隨其后,而香港更是該報告發布13年來首次跌落綜合競爭力排行榜首位。
超越香港的深圳與其毗鄰。這個如今人口超過千萬的城市在30多年前還只是人口僅3萬人的邊陲小鎮,當時,前來投資建廠的李秀恒面臨的是一下雨就泥濘難行的道路和時常“罷工”的電力供應,發電機成為工廠開建時的標配。
從1987年在深圳坪山投資建廠,到1997年香港回歸,這十年是李秀恒的鐘表公司的黃金時代,也是香港工業的巔峰時期。據當時的統計數據,1995年全球鐘表市場容量約為6億只,而香港的鐘表產出量約占其中7成,把老牌表業強國瑞士和新興表業強國日本都甩在后頭。
“價廉物美的石英電子表當時非常流行,我主要做這一塊。”那時的香港,李秀恒不愁訂單,愁的是招不到充足的工人,找不到能用于工廠擴建的土地。李秀恒將目光轉向內地,雖然對內地改革開放之初的優惠政策能否持續仍有擔心。李秀恒逐步將相對落后的設備和幾條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線從香港轉移到內地工廠。
出口量在全球都名列前茅的鐘表、玩具、服裝工業等引領了香港工業在上世紀80年代走向黃金時代,最高峰時香港的工業產值占香港經濟總量的3成,并吸納了將近半數的就業人口。
根據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份有關香港制造業發展趨勢的調查報告,從事制造業的港商,在向內地遷移后,很多從原本的小廠,迅速發展成為在內地擁有數千員工的大規模生產基地。
在李秀恒看來,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走上騰飛之路到現在,香港工業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于香港的經濟自由港的優勢,再加上一定程度上因為香港并非高福利社會,所以香港人非常勤奮,物美價廉的“香港制造”發展迅速;第二個階段為八十年代中后期到1997年香港回歸,香港工業騰飛正盛,工人嚴重短缺,工業用地供應也跟不上,而內地逐漸開放,成為香港工業發展的后盾,有大量的土地、資源、勞動力,配合香港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香港工業的生產加工也紛紛向內地轉移;香港回歸后至今,由于內地的開放程度加深以及自身的經濟發展,一方面內地給香港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內銷市場,另一方面很多外國企業進入內地,而內地自身的加工企業也快速興起,與香港企業直接競爭。靠著勞動密集型產業起家的香港工業,在人力等成本上劣勢盡顯,香港經濟開始由工業主導轉向金融、旅游、娛樂、教育、醫療等服務業主導。
“一開始,港商在內地投資建廠時,內地人不會做外貿,我們幫內地出口。過一段時間,內地跟香港一起走,有競爭有合作。但是再往后,香港要跟著內地經濟走,內地的經濟體量太大了。內地市場需要什么,香港企業就提供什么,而不是由香港來主導內地的經濟發展。”李秀恒說。
“在內地,能發揮的地方很多”
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的十多年里,香港出現了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潮。
在這個過程中,李秀恒卻選擇了與內地加強合作和聯系。“第一是因為我去內地比較多,在內地也有投資,對內地的政策和環境都已經熟悉并理解,對與內地進行合作的信心也不斷增加。”李秀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內地政府的思路越來越活躍,經濟上也一步步跟同際接軌。”
“我從來沒有做移民的準備,包括家人。”李秀恒說。他的現實考量是,移民去外國,港商并沒有自己的優勢。其次,西方的教育水平比較高,港人的專業水平在西方也沒有什么優勢。反而在內地,能發揮的地方很多,競爭力上還會有一定的優勢。
但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和香港工業開始下滑的情勢下,李秀恒的鐘表生意也遇到了嚴峻的挑戰,曾經不愁訂單的他面對著訂單量的不斷下滑。在內地,一大批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快速興起,也開始生產鐘表。雖然李秀恒選擇了向鐘表高端化方向轉移,但高端鐘表的市場規模要小很多。
李秀恒的應對之道是,“與其惡性競爭,不如分散投資”。
在香港回歸后,特區政府鼓勵港商進入內地發展,香港本地留下了很多空置的工業樓宇。再加上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房地產價格急劇下跌。一些建筑成本達每平米1萬港幣的工業樓宇,售價卻只要每平米三四千港幣。
香港地少人多,樓市的需求低迷只是暫時的。李秀恒出手買下一些工業樓宇后,進行裝修改造,或出租,或做酒店運營。
2003年非典結束后,香港的房價開始走出低谷,一路飆升。
同年的7月28日,出現了內地與香港之間人員往來的轉折點。廣東中山、東莞、江門、佛山4個城市的居民只需辦理港澳通行證,就可以個人身份到香港旅游。這就是后來大家俗稱的“自由行”。一年后,“自由行”擴展至華南及華東的32個城市,這些城市里1億5800萬居民可以申請“自由行”,之后范圍不斷擴大。
統計顯示,2002年“自由行”尚未展開時,訪港游客僅為1660萬人次,其中682萬為內地旅客,占整體旅客量41.2%。而十年后,到2012年底,訪港旅客大幅增至4861萬人次,內地旅客占整體訪港旅客的七成以上。
香港的零售業和酒店業成為“自由行”的最大獲益者。在旅游旺季,香港三星酒店房價會超過千元每晚。
不過,赴港內地旅客數量的激增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爭議也開始變得激烈。2013年3月,香港特區政府實施“奶粉限購令”,將嬰幼兒配方奶粉列為法定儲備食品。法定儲備食品意味著,無論是奶粉進口數量還是出口數量都會受到嚴格限制。
對于香港面臨的奶粉短缺情況,李秀恒認為,港人應該正面地去看待。“內地人士來香港買需要的東西,這是很好的事情,政府需要找到好的解決辦法,要思考怎么去把物流搞好,把進貨渠道搞好。就世界整體市場而言,是不缺奶粉的。”
“我們那個時候不流行找政府”
服務業代替工業成為香港經濟的主導,在李秀恒看來,這是經濟發展規律的一種體現。“這是全球的一種經濟現象,社會要進步,老百姓生活水平要提高,就會有一個轉變,要做高增值的部分。”
如今,香港的綜合競爭力和經濟總量都面臨著被深圳和其他諸多內地大城市趕超的情況,但李秀恒并不對香港經濟過分擔憂,因為香港的經濟體系本來就不大,不過700多萬人口,就業人口才300多萬,其中政府的公務員,學校老師等有固定工資的職員加起來就超過100多萬。有統計顯示,香港的失業率非常低,只有3%,接近全民就業。
李秀恒認為,眼下,香港要考慮的是怎么樣跟內地多配合,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擴展增量,而不是只把眼光盯著競爭;另一方面,特別是在服務領域,要考慮應該怎樣發揮香港的優勢。
談及目前年輕人對香港未來的擔憂,李秀恒說起自己上大學時的經歷。土生土長在香港的他,一畢業后什么社會福利都沒有,而因為家里條件不太好,就拼命讀書,“主要是為了工作后能多賺些錢,也希望盡可能減輕家里的負擔。當時社會對老人也沒有什么照顧,自己有責任去照顧。”
“當時我們都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上,也不流行找政府。”李秀恒說。
在他看來,香港由于過去長時間殖民統治,沒有受過愛國教育,年輕人的國家意識比較薄弱,對國家不太理解。年輕人參與政治是應當的,有助于理解社會,但年輕人又很容易受其他人的影響。他希望年輕人應該多了解歷史,多思考自己的實際情況,有獨立的判斷,而不要片面地去看問題。
“不能都是批評,而沒有一點實際的建議。”李秀恒說。
就在李秀恒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的當天,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舉行發布會,介紹“香港大學生赴天津考察團”的情況。兩天后,來自香港9所大學的62名大學生會前往天津進行為期四天的考察,全部費用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承擔。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青年委員會主席、考察團團長張永鴻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考察團的天津之行的主題為“創意創新創業”。“我們發現,在培育新一代企業家方面,香港的力度比不上內地,這方面需要向內地好好學習。”
這次參訪團的主要目的,還是加強香港年輕人對內地的了解。“很多年輕人的想法會隨著年齡的變化而變化,有一些年輕人可能未來去當民運領袖,但是大部分人在進入職場并跟不同階層的人溝通后,會更理性地考慮現實問題,也會明白香港跟內地其實是分不開的。”張永鴻說,“但這不等于我們什么都不用做,只等著這些年輕人慢慢成長,慢慢改變。香港和內地雙方都要盡可能多做一些加強交流和溝通的事,以增進相互間的了解和信任。
(實習生楊懿瑾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