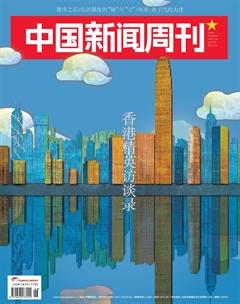他不是魔鬼,只是年輕
楊時旸
似乎再沒有一個時代比當下更偏愛年輕人。對于年輕的歌頌,幾近一種迷信。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拜互聯網所賜,它顛覆了關于時間、積累、閱歷等等這些與沉淀相關的一切概念,更加強調活力與顛覆性的可能。年輕成為了天然的政治正確,年長近乎一種殘缺。這部《年輕時候》講的就是這樣的故事。用兩對不同年齡的夫婦的故事,探討了年輕、野心,以及在時光逝去的恐慌中,到底該以怎樣的心態去面對。
喬什是一位紀錄片導演,曾拍出過著名的作品。他與自己的太太已入中年,沒有子女,生活平靜但也無聊。他偶然認識了一位年輕的紀錄片導演杰米和他的妻子。兩對夫婦很談得來,尤其這對年輕人的活力感染了喬什夫婦。
杰米開始試著制作自己的一部紀錄片,在這個過程中意外發現了一個有關美軍在阿富汗戰場上的故事,大家都很興奮。一直處于事業瓶頸期的喬什從這個年輕人身上看到了某種光彩,決定盡力幫助他,他自己協助這個年輕人拍攝,又把自己的人脈資源介紹給他。但直到最終,卻發現自己似乎一直被利用。
《年輕時候》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從一開始,導演就用兩對夫妻的個案故事,寫出了他們背后兩個群體的特質。喬什所代言的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群像,穩定、成功、無聊、對新事物和年輕人有酸葡萄心理式的輕蔑;而杰米則代表著活在當下的年輕人群體,貧窮但充滿希望,生活陽光而有樂趣,對一切世俗成見從不在意。杰米的出現,正好切中了喬什中年危機的當口,某種程度上說,這個年輕人成為了這個中年人的精神導師。喬什有意地改變生活方式,開始追隨年輕人的步伐,從穿著打扮到行事方式。
更有趣的一層意義就此顯現出來。當所有同齡人都為人父母,開始了更加確定而瑣碎的生活,由于喬什夫婦沒有孩子,再加之他們與那群年輕人為伍的生活,他們被同齡人視為“有問題”的怪人。朋友們勸喬什,“我們已經老了。”言外之意是告誡他們應該成熟一點,不要再有什么奇思怪想。但喬什對此無法認同。這是《年輕時候》表達的第一層觀點,當人們處于“中年”這個尷尬的轉折時刻,到底應該按照既定軌跡認命地跟隨慣性,還是應該不去考慮年齡,只是跟隨內心。
如果說,對于喬什夫婦的描述,探討的是中年危機的故事,那么杰米那條線索,探討的就是年輕人的野心與手段的問題。到了最后,喬什發現,杰米其實一直在騙自己。他早就發現了那個阿富汗的好故事,但用了一個近乎圈套的手段,讓自己自愿貢獻了人脈資源。他有些分不清,對方邀請自己參加年輕人的聚會,和自己一起騎行,把自己當朋友,這一切到底是設計好的手段,還是真心為之。
到此為止,喬什陷入了一種孤立的境地,同齡人把自己當做“不成熟”的孩子,而看似把自己當做朋友的年輕人,卻只是把自己看作一個籌碼,一個有資源、有經驗可以榨取的中年人。他的困惑就又加深了一層。
《年輕時候》的導演和編劇是諾亞·鮑姆巴赫,曾經寫出過著名的《魷魚和鯨》《弗蘭西斯-哈》,也和《布達佩斯大飯店》的導演合作創作過《了不起的狐貍爸爸》等作品。這一次,他把這個處于危機中的中年人的困窘展現得非常透徹,同時又不乏幽默感。
像所有這類主流電影一樣,最終,他呈現了一種舒緩的解決方案。在與年輕而富于野心的杰米鬧翻之后,喬什不再屈從、臣服于年輕人的生活方式,不再去模仿他們,也沒有認同同齡人沉悶的狀態,而是開始按照自己相信的軌跡繼續生活。其實,年輕和年長并不必然指向對與錯,它們都只是一種年齡狀態和心理狀態。沒有確定的方案可供遵循,更沒有必要故意表演年輕和扮演成熟,在年輕時刻意放浪形骸,在中年里故意墨守成規。
電影的最后,喬什夫婦翻著雜志,發現杰米已經憑借紀錄片成名,在雜志上洋洋自得。妻子說,“魔鬼被釋放了。”喬什卻已經變得通透,“其實他不是魔鬼,只是年輕。”這種態度才是真正的成熟、豁達,而不是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