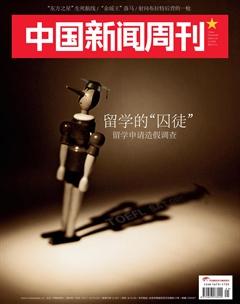中美關系的“臨界點”在哪里?
何亞非
近來,關于中美關系接近“臨界點”的辯論在兩國專家和學界愈演愈烈。同時,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強行介入,美國防部長卡特在最近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點名指責中方在南海島礁建設,揚言要采取進一步強硬行動。中國政府和軍方在各個場合包括香格里拉對話會,明確表示捍衛主權的決心,并揭露了美方在南海問題上玩弄“唯恐天下不亂”的“平衡術”,以及擔心失去西太平洋軍事霸權的“焦慮感”。
中美關系不僅關乎中美兩國長遠利益,因為兩國“塊頭”大,還將影響世界格局的變化,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
從目前形勢看,圍繞南海島礁的爭端有升溫之虞。這對中美關系有何影響,學者們所說的中美關系接近“臨界點”,是否符合兩國關系的實際,都需要認真分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這一“臨界點”意味著什么?
“臨界點”是個偽命題
關于中美關系處于“臨界點”的說法是美國學者蘭普頓發明的。他認為,自2010年以來,美中關系正在接近“臨界點”,即雙方對對方的恐懼已超越對雙邊關系的“希望”;美中關系一些根本性的支撐受到侵蝕。不少中美學者都表示了類似的擔憂。
學者們對“臨界點”的解釋大概不外乎兩種:
一是中美接近“修昔底德陷阱”,即中美作為新興大國和守成霸權的博弈將從和平競爭走向對抗,甚至軍事對抗。希臘先哲修昔底德描述了,古希臘文明毀滅于雅典和斯巴達兩大城邦的戰爭。哈佛大學教授由此創造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詞。歷史長河中另一種“陷阱”是,過去五百年世界歷史上16次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博弈,其中12次用戰爭方式解決。
二是中美關系從合作與競爭并存、合作為主階段向合作與競爭并存、競爭為主階段轉變,已接近兩個階段的轉折點。當然,這里講的競爭未必就是對抗,也可以是和平方式的競爭。
不管按上面哪種說法,中美關系現在接近“臨界點”了嗎?這個問題需要好好分析,因為它牽涉中美兩國對對方的戰略認知和對中美關系的總體評估,從而會影響兩國的對外戰略和對華/美政策。而如何穩妥處理中美關系、中美能否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可能是21世紀上半期世界地緣政治的最大挑戰。
其實,世界力量的消長是歷史常態,是動態的。關鍵在于如何看待這種地緣政治變化,而且對這樣的“慢性病”是用西醫“動手術”方式處理,還是用“看中醫”細細調理。東西方不同的世界觀對此有不同的視野和處理方式。中美需要從兩國人民和全球利益出發,作認真思考,謹慎行事。
中美關系是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兩國歷史、文化、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但同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全球治理體系的核心成員,解決全球挑戰需要兩國的密切合作。兩國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結成了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兩國年貿易額超6000億美元,雙向投資存量逾1000億美元,2014年中國在美投資超120億美元,而5年前只有7億美元。
中美關系如此復雜的“系統”不可能“直線”運行,不時出現起伏十分正常,只要總體穩定、向前發展就可以了。
兩國要按照建設“新型大國關系”的框架加強溝通
正是出于全球和兩國根本利益考慮,習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建設“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這一倡議充分體現了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核心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思想和中方倡導的新型國際關系。盡管中美之間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矛盾,兩國對建設新型大國關系還是有初步共識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正確認識兩國關系所處的歷史階段,在雙邊關系發展中真正落實建設新型大國關系的戰略共識,妥善處理分歧,化解矛盾,增進互信。
南海問題是個現實、緊迫的考驗,但只是“一個問題”而已,并非什么“臨界點”的標志。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是中國主權范圍內的事情,合情、合理、合法,別人無權指手畫腳。而美國聲稱的南海航行自由根本不存在任何障礙。美國指責中國在南海的修建活動,無非是擔心中國實力壯大,影響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絕對控制力。可以清晰地看到,南海發生的事情一面涉及中國主權利益,另一面涉及美國對待新興大國的態度和在西太平洋的戰略態勢。
其實這兩者并不一定要對立。如果美方堅持以“零和”方式來看待和處理南海事務,那么很遺憾,矛盾就有可能激化。這不符合地區各國利益,也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中美不管在南海還是其他地方都沒有根本性利害沖突,美國如果為了維護地區絕對控制權而不惜與中國發生沖突,那是戰略的誤判和錯誤,于美國無益,于中美關系無益,于世界也無益。對此,中方是冷靜、理智、克制的,希望美方也能投桃報李,采取冷靜、克制態度,降低緊張局勢。
更為重要的是,雙方需要深入思考,作為世界第一、第二大國,如何認識對方和雙邊關系,即對世界格局和雙邊關系有恰當、正確的戰略認知。這是個緊迫而又關鍵的問題。
進入21世紀以來,中美傳統意義上的摩擦,如對臺軍售、人權等并未增多,但新出現的矛盾和誤解如南海問題等卻在上升。這些間接的“軟傷”雖未直接對中美關系造成大的沖擊,但嚴重影響雙方的戰略認知和判斷,會侵蝕本已脆弱的戰略互信。
無論從全球力量消長還是經濟全球化角度看,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確實是提高了,而不是減少了。中美關系經過這么多年的“磨合”,已經趨于成熟,不管怎么理解,正在步入建設“新型大國關系”的新階段。雙方比過去更加開誠布公,敢于正視矛盾和分歧。處理雙邊關系問題也更加務實、有效。這些進步在外界看來可能會表現為,摩擦比過去多了,批評比過去增加了。其實兩國合作遠比過去深入、廣泛,涉及雙邊關系和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
習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萬隆會議上提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這首先就是中美兩國的命運共同體建設,因為離開了中美合作,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成為一句空話。中美關系緊張會令中國周邊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緊張不安。中美都具有全球影響力,兩國如何互動將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未來起決定性的作用。
中美需要開展更加有效的戰略溝通
我認為,“臨界點”的說法值得商榷。“臨界點”本指核反應的爆發點。以此來說中美關系很容易誤導。如果是指中美關系兩個階段的“連結點”和起承轉合,這樣的描述雖不準確,也算過得去。確實中美關系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如果是指兩國由此放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建設,而從合作為主的關系走向對抗乃至軍事對抗,這樣的“臨界點”說法就是誤讀、誤判形勢,完全沒有依據,只會給中美兩國和外界傳遞錯誤的信息。
由此說來,中美需要開展更加有效的戰略溝通,把話說清楚、說透徹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如中國對美日加強軍事同盟以及美國加強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疑慮很深,反對美國直接介入南海爭端,在南海島礁爭端中站隊選邊。中國對美國高調介入南海爭端背后的戰略意圖深感憂慮。美國對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正常做法往往誤讀誤判,得出“最壞的結論”。美國常說其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不針對中國”;中國強調自己做的事都是中國主權范圍內的事情,美國管的太寬了、太多了,手伸得太長了。
中美雙方有必要在高層和工作層詳盡地把各自戰略意圖闡述透徹,盡力消除誤解,防止進一步的誤判,以免觸發沖突,引起不必要的對抗。可以適時考慮在戰略和經濟對話(S&ED)框架內建立2+2磋商機制,即外長+防長的定期磋商機制,進行上述溝通。
另一項緊迫任務是建立可靠、管用的危機管控和處理機制。這一機制可由兩國負責總體國家安全的委員會負責,外交和軍事部門參與。雙方的聯系和溝通渠道務必要暢通、無障礙,包括相互通報在西太平洋區域的重大軍事行動、對全球危機地區特別是周邊區域局勢的定期判斷等。
中美這些年積累了許多管控危機的經驗,有效降低了中美摩擦。這些正能量需要延續并轉化為兩國互信的成果,即中美就戰略利益交織的亞太地區凝聚共同的愿景。這一愿景要給中國發展留出足夠的空間,接受中國發展的現實,同時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得到尊重。
中國在較長時間內將是中美之間相對較弱一方,中國沒有擴張的歷史和文化基因。目前中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任務繁重,將長期需要穩定、友善、和平的國際和周邊環境,不會也不可能將挑戰美國地位作為國家戰略目標。也就是說,中國對外和對美戰略將長期處于以合作共贏為基點的戰略防御態勢。美國和西方炒作“中國威脅”,無論從什么角度看,都是“庸人自擾”。
現在,美國和西方輿論有一種說法,稱中國已放棄“國際體系利益攸關者”的立場,正采取“切香腸”的辦法漸進式地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他們把中國在主權范圍內所做的事情,包括最近在南海的行動、“一帶一路”建設和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都看作是,中國雖然沒有全面挑戰美國“治下”的全球治理體系,但已經在“另砌小灶”,試圖與前者一比高下,并由此質疑中國的“小灶”與美國的“大灶”是否“兼容”“合拍”。
總之,美國和西方輿論十分擔心中國試圖“修改規則”,而非繼續“遵守規則”。美國權威的智庫外交關系委員會最近發布對華政策研究報告,聲稱中國已對成為美國治下的國際體系“利益攸關方”失去興趣,想修改體系的規則而達到塑造新體系的目的。該報告雖未將中國定性為“敵人”,需加以“遏制”,但已將中國確定為“戰略競爭對手”,要求美政府迅速采取行動,“限制中國濫用其日益增長的力量的能力”。該報告得到不少人贊同,認為是美國朝野“對華戰略再思考”的結果。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顯然出于同樣的戰略評估。按照這一戰略,將中國壓在第一島鏈內,再控制中國出南海進入印度洋的通道,使美海洋霸權自然延續。這才是美在南海給中國制造麻煩的根本原因。
中美關系矛盾和摩擦增多是事實,我們不必緊張和擔心,“臨界點”一說乃是部分學者對中美關系處于轉折階段的一種描述而已,并非表明中美正進入“對抗”和“沖突”階段。只要兩國按照建設“新型大國關系”的框架加強溝通,減少猜忌和疑慮,通過務實合作增進互信,中美關系的大方向就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