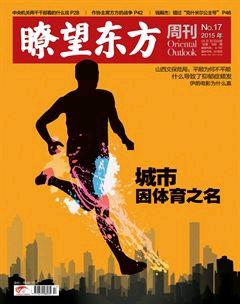最鐵的巴鐵
徐穎+徐晴晴

2011年12月20日,巴基斯坦卡拉奇,中國曲棍球隊隊長駱方明(左)與巴基斯坦曲棍球隊隊長在訓練前交流
“儂是上海人伐?”皮膚黝黑的巴基斯坦駐華科技參贊澤米爾.阿萬一見面就這樣問《瞭望東方周刊》記者。
他的上海普通話,還要追溯到1949年之前。那時,澤米爾的父親曾是英軍駐上海的一員,往返于香港與上海之間。
從小聽父親講中國故事的澤米爾,于1980年開始在北京語言大學學習。一年后,他前往父親居住過的城市——上海,就讀于上海大學機械制造專業,從而成為在中國的上萬名巴基斯坦留學生中的一員。
澤米爾還記得當時有位老師是著名科學家錢偉長先生,“不僅課講得好,還在那個困難的年代為學校申請到了很多的資源,是個很了不起的人。”
根據中國外交部網站,1964年中國開始接收巴基斯坦留學生起到2013年,來華學習的巴基斯坦學生總數為10941名。
半個世紀以來,無論老新巴基斯坦留學生,都是中國日新月異變化的見證者和參與者,被稱為“最鐵的巴鐵”。
正如澤米爾所說:“我受到中國的教育,最好的時光在中國度過,吃的中國飯,喝的中國水,呼吸著中國空氣,雖然我是巴基斯坦的外交官,雖然我長得像老外,但我有中國心,有中國夢。”
目睹改革開放
與通常滿是本國風光和藝術品的外國駐華使館走廊不同,巴基斯坦駐華使館的走廊里滿眼都是中巴領導人親密握手的照片,其中很多都是歷史久遠的黑白相片。
曾任巴基斯坦駐華商務參贊、巴基斯坦駐上海首任總領事以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對華事務局首席執行官的扎爾法的遺憾是,他沒能見到傳說中的中國領袖毛澤東。
還在讀中學的扎爾法被印有毛主席和普通農民一起勞動圖片的畫報深深地感染,他決定到中國看看。
1976年,20歲的他終于如愿申請到了獎學金到中國語言大學學習漢語。只可惜他9月到北京時毛澤東已經去世。
不過,他正好趕上了天安門舉行打倒“四人幫”的慶祝大會,還遠遠地看到華國鋒主席。至今他記憶猶新的是,自己也穿上了那個年代中國流行的深綠衣服,“感覺每個人都很平等”。
扎爾法來自拉合爾,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富裕的旁遮普省省會、巴基斯坦的文化和藝術中心,擁有2000多年歷史。
一年語言學習后,他去了改革開放前的廣州,在中山醫學院繼續學業,“那時廣州還未開放,少有外國人,我到哪兒去都被圍觀。”
1982年,大學畢業時他已經能聽懂粵語。雖然這6年間他沒有回過巴基斯坦,但目睹了中國改革的關鍵過程。
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已允許外資銀行進入。憑借熟練的中文和英文,扎爾法找到了一份外資銀行在中國辦事處的工作。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企業在國外做項目很困難,獲得銀行貸款需要層層審批還要去外管局備案,出具一份保函相當難,耗時至少三四個月。當時在外資銀行,我也積極為中國企業提供各種幫助,也算直接參與了改革開放,現在回想起來是比較有意義的。”扎爾法自豪地說。
最近他正在閱讀中國國務院原副總理李嵐清所寫的 《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翻開書,他為本刊記者找到其中一章: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并不善于使用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貸款,巴基斯坦財政部負責世界銀行業務的首席專家烏拉赫·汗先生應邀來華為銀行、企業舉辦講座的故事。
“雖然其他國家也有相關經驗,但都有所保留。”扎爾法說。

澤米爾·阿萬

扎爾法
兩個變化的國家
其實,“剛來中國時,巴基斯坦國內的基礎設施、經濟條件都要比中國相對好一些。”澤米爾說,上世紀60年代巴基斯坦經濟增速曾達到每年7.5%到7.8%,有很多周圍國家政府官員到巴基斯坦學習經濟發展模式。不過隨著1979年蘇聯進軍阿富汗,巴基斯坦經濟一蹶不振。”
不過他說,在80年代讀大學時,已有說法“巴基斯是中國的鐵哥們”,也就是后來的“巴鐵”。
他在中國7年本碩連讀后,不但漢語流利,還學會了說上海話。畢業后他一度前往沙特,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最終于2010年被任命為巴基斯坦駐華科技參贊。
回到中國,他被中國的變化驚呆了,“很多高樓林立,配置現代化的電腦房,還記得當年我們讀書那會兒學校購置一臺電腦,我們輪流參觀。”
只是此時教過他的很多教授已經去世。所幸教過他數學的朱老師還在。此后每到上海,澤米爾總要去探望朱老師,喝喝茶,聊聊天,“我是班上唯一的巴基斯坦人,朱老師對我格外照顧,像一位‘大家長一樣”。
在回到中國前,澤米爾在2002年開始就職于巴基斯坦科技部。那時美國已經發動了反恐戰爭,雖然成為盟友,但他覺得美國的援助和軍費遠抵不上巴基斯坦在戰爭中的消耗,其具體表現就是科技投入的快速下降:原來科研立項申請10個可以批準9個,這時一般就是2個。

2010年10月8日,巴基斯坦海德拉巴洪水災區,中國人民解放軍直升機救援隊懸停投放救援物資
“相當于巴基斯坦從1979年開始一直陸續在戰爭,所有的財力、人力都花在養軍隊、買武器上,教育部、衛生部、科技部、農業部均缺乏財政支持,老百姓就很辛苦。”澤米爾說。
他的家鄉是位于伊斯蘭堡北部30公里的小城市——瓦赫。巴基斯坦國防部管轄的兵工廠也設立于此,他父親退伍后就在該廠工作,澤米爾也親眼目睹了戰爭時這里的繁忙。
提到在中國的這5年工作經歷,澤米爾的情緒立刻好轉,“兩國的科技合作很順利,沒有遇到過大麻煩,我們對中方提出什么要求中方基本上都同意,當然我們也不會提不合理的要求。”
什么是全天候朋友
1991年扎爾法雖然決定回到巴基斯坦,但還是想從事與中國有關的事業,于是開設了一家投資咨詢服務公司,為中巴之間的投資提供咨詢。
3年后,他促成了中國企業在巴基斯坦投資的首個非政府項目——濟南輕騎摩托車有限公司在巴基斯坦設立“輕騎賽格爾”工廠,這種摩托車在隨后20年里成為從總統到老百姓都知曉的暢銷產品。
到上世紀90年代末,巴基斯坦政府決定從社會上選拔商業經驗豐富的人擔任駐華參贊。
扎爾法激動地報了名,并在1999年1月出任巴基斯坦駐華商務參贊。次年正值中巴建交50周年,兩國的經濟合作被前所未有的重視,中國電器產品開始進入巴基斯坦市場,海爾的冰箱、洗衣機、空調等產品在巴十分暢銷。
2004年起,扎爾法出任新成立的巴基斯坦駐上海領館總領事,推動大量省市級代表團互相交流學習。在他看來,目前影響中巴合作的最大因素,恐怕還是巴基斯坦國內的黨派之爭。
他解釋說,在巴基斯坦,聯邦政府和省政府有的時候會分屬不同的黨派:比如,在他擔任旁遮普省對華事務局的時候,聯邦政府是人民黨當權,省政府是穆斯林聯盟當權。
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早在2009年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政府與中國北方工業國際公司就拉合爾城鐵項目進行溝通,但是城鐵項目需要國家主權擔保,聯邦政府為了防止省政府的利民項目成功后獲得更多支持率,便以各種理由推諉,進展緩慢。
不過,“反對黨與政府互相打來打去,對中國的問題上都是統一的。無論軍政府還是各個黨派執政,兩國關系都沒有變——就是我們說是‘全天候。”澤米爾說。
他認為:“從政治上說,世界上一些國家可能覺得中巴關系很好,他們不太高興,可能有各式各樣的想法,但是我們不管他們。巴中關系就是非常密切,現在中國已經足夠強大,這些阻力即使存在,也好像沒有作用了。”
扎爾法的舉例是,“如果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想要在一天之內見到巴基斯坦財政部長、總理、總統、軍隊司令都是可能的,別的國家就不行。當然,中國現在的朋友也很多,需要平衡外交。”
現在,他們兩人共同關注的焦點就是“中巴經濟走廊”。
扎爾法將在4月習近平主席訪問巴基斯坦后被正式任命為中巴經濟走廊顧問。
這位“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受益者”的辦公室墻上,有他在外資銀行工作時與鄧小平握手的照片。雖然拍照者技術并不好,照片過度曝光畫質并不算好,但他還是堅持把它鄭重地張貼了上去。
新“巴鐵”的中國夢
2015年5月初,澤米爾將參加大學同學舉辦的35周年同學聚會。可以見到因為通訊落后而失去聯系的朋友們使他激動不已。
因為習近平主席對巴基斯坦的訪問,澤米爾這幾天已經用“巴鐵”這個詞語在朋友圈刷屏了。
比如他連續分享的鏈接就包括“巴鐵是怎樣煉成的?”“巴鐵,你知道嗎?”“巴鐵關系已經升為巴金關系”,等等。
他還分享了“北京出現巴鐵快閃”的視頻,畫面中一群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年輕人用快閃的方式來歌唱中巴友誼,預祝習近平主席訪問巴基斯坦圓滿成功。
活動的組織者是一名來自中國語言大學的26歲巴基斯坦留學生阿姆扎德,他也算是澤米爾的半個校友。
目前為止這個名為《跟著大大走:習大大訪巴前夕》的視頻僅在優酷上播放的次數已超過25萬。在快閃過程中,中巴學生手挽著手一起高喊“中巴友誼萬歲!”
阿姆扎德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其實他來到中國也是受到了父輩的影響——父親年輕時是長跑運動員,有過一位中國教練,“所以父親很有中國情結,并把這種感情也傳遞給了我”。
此時,雖然在中國的外國人已經不會被圍觀了,不過他還是得到了和上一代留學生一樣的關懷,“剛來中國的時候買東西都不知道去哪兒,很多中國同學和老師都熱心幫忙。”
來到中國的第三年,阿姆扎德終于能看懂《還珠格格》和《隋唐英雄傳》,最近他還看了《武則天》,中國傳統文化對于他來說很有吸引力。
雖然中巴關系密切,但是阿姆扎德告訴記者,很多巴基斯坦人對中國的認知還很有限。每次回家,總會有朋友問他“是不是中國人都會飛檐走壁?”因為他們認識中國主要還是通過成龍和李小龍的功夫片。
現在,與阿姆扎德聯系緊密的巴基斯坦留學生朋友大概有10個人。
這個圈子也會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如何從中國經濟發展中吸取經驗”這類大問題,也偶爾會探討一些中國現象,比如“為何很多中國青年如此癡迷于美國文化和韓國文化,相反卻忽視古老的中國文化。”
當然,“畢業后是否留在中國”也是他們之間探討頻率比較高的問題。阿姆扎德說,找一份中國工作“可能比較復雜”。不過在中國留過學的學長雖然沒有在中國工作,也都幾乎利用了自己的語言優勢從事了與中巴貿易相關的工作。
阿姆扎德說。對于7月即將畢業的他來說,未來的可能無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