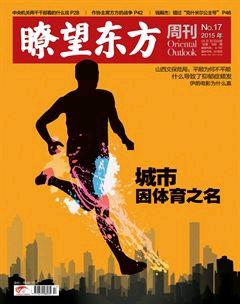名編劇說IP熱:與其埋怨,不如“反攻自己”
覃柳笛

對于當下的中國影視圈來說,IP(知識產權)無疑是炙手可熱的詞匯。有業內人士調侃,現在影視圈搞創作不再說“拍戲”,而是“IP 開發”。也有人說,IP的流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好劇本的匱乏,制片方更傾向于選擇一個經過市場檢驗的故事內核,開發出不同的產品。
2015年4月,一場由“編劇幫”主辦的中國電影編劇研討會在北京國際電影節展開,一線編劇匯聚,對當下的“IP熱”展開討論。與往常的行業討論常演變為吐槽大會不同,這次研討會展現出了難得的自省精神。
他們承認,目前編劇的原創力、想象力水平遜于作家,這也是制作公司大量購買熱門文學作品并改編成影視的重要原因之一。
電影《親愛的》編劇張冀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我原來在編劇會議上會說,編劇最重要的狀態是維權,但現在我要說,編劇最重要的是‘反攻自己,我現在主要的狀態是創作,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寫出有創意的好故事,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IP不等于好劇本
影視行業的IP意識已經今時不同往日。《畫皮Ⅱ》編劇冉甲男記得,早前她接觸的一些影視公司在看到一個好故事時,往往會改頭換面一番,“直接拿來用”,卻不會去買版權。
現在,幾乎所有影視公司都在談論熱門IP,都在砸重金囤版權。但是版權恐怕并不等于好劇本。
“影視公司買一個熱門IP,是買了一個熱門話題,但在改編成影視作品時會出現很大問題。”冉甲男坦言,“比如一個跟帖量很高的網絡小說,讀的時候很有代入感,改編成一個劇本時才發現,它沒有堅實的人物關系、沒有推動人物的核心情節,也沒有出人意料的環節設計,編劇等于要完全原創,重新做故事架構和人物關系。”
《泰囧》編劇束煥2014年去了美國洛杉磯的夢工廠,他驚訝地感受到國外創作團隊對劇本的重視程度:一個團隊正在制作一個上海題材的動畫片《十二生肖》,計劃花3年的時間來打磨劇本。“要是我們的話,劇本打磨到這個程度,再過兩個月電影都可以開機了。”束煥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我們不缺投資,就缺好編劇、好劇本。”這是業內人士最常念叨的一句話。現實情況卻相反,束煥到某公司參加項目討論會時發現,“談電影植入的時候有20多個人,談到劇本的時候,就只剩一個人了”。
“現在大家都在談投資、談項目、談檔期。然而大家的興趣點卻不在最重要的劇本上。所有人都說我們需要一個好故事,但實際上卻很少人扎實地去抓劇本。很少有人關心,好故事到底是什么。”在束煥看來,目前影視行業對于一個“好項目”的需求已經超過了“好故事”,這是十分危險的。
“我有時覺得這些公司真的挺虧錢的。大家現在花了大價錢買熱門IP,就是因為有一票粉絲追捧,但是粉絲所感動的那個點,恐怕也沒法把它轉化到電影的視覺上面去。”冉甲男說。
當然,重金砸向版權,并不意味著影視公司是從故事層面來考慮這些熱門IP的。“我們買過很多網絡小說的版權,我認為質量遠遠不夠好,甚至非常差,但是也能賣出很高的價錢。原因是這些劣質的故事滿足了一些三四線小鎮青年的需要。”萬達影業的一位項目開發負責人如是說。
地位需要自己去爭取
冉甲男最近與資方談項目,發現資方都會帶著一個劇本顧問一起參加討論。
劇本顧問會對劇本創意是否適合市場作出判斷。而以前談項目是與資方直接對接,常讓她感覺“牛頭不對馬嘴”,現在“終于有一個專業的人來做這件事了”。
“我最近給我的同行打電話,發現90%都在跟戲,剩下10%的人在度假。此外,編劇同行里抱怨甲方拖款、坑蒙拐騙的人也越來越少。”這是《繡春刀》編劇陳舒的感受。
然而,陳舒也有一個困惑,最近她接觸的項目也多是影視公司在買到熱門小說IP之后,讓編劇改編成劇本,“這讓我有一種當后媽的感覺,畢竟做原創故事才是更有成就感的。”
改編為何成為編劇行業的一種趨勢?
陳舒認為:“這反映編劇的原創力和想象力低于小說作者。現在很多年輕編劇都是做委托創作入行的,想象力被禁錮,甚至不如網絡小說作者。我們做委托創作積累行業判斷和專業技能以后,應該重視開發自己的原創故事,這樣才能更上一個臺階,給電影市場帶來新鮮血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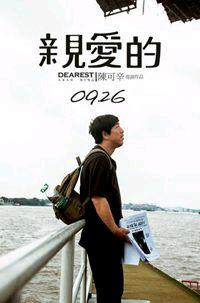

電影《親愛的》和《畫皮Ⅱ》海報

中國電影編劇研討會現場
除了改編,還有翻拍的流行。束煥坦言,這種“復制和山寨”的確是行業現狀,“就像我國的綜藝,把韓國所有的綜藝節目都買光了。”
“翻拍更多是商業行為,而非創作行為,一個經典是一個成熟的創意,有其可利用的商業價值,所以翻拍無可厚非。但是翻拍成為主流,就是不正常的,證明編劇原創力的低迷。”北京新影聯影業總經理周鐵東告訴本刊記者。
“我個人是拒絕翻拍的,社會現實已經足夠豐富,給編劇提供了原創的大量素材。”張冀告訴本刊記者,目前編劇的原創力確實亟需提高。
由于很多編劇自己原創的劇本缺乏新意,達不到電影工業標準,成為造成編劇地位沒有導演、演員重要的原因之一。
“與其埋怨,不如‘反攻自己,努力研究創作,練就技能,寫出真正的好劇本。話語權不是別人給予的,而是自己爭取的。”張冀說。
“先不說創意水平,我收到編劇發來的各種劇本,甚至連格式都五花八門,字體、字號、行距都不統一。在美國這些都有嚴格的標準,但是在中國編劇還沒有建立起行業標準。”周鐵東說。
不過,張冀仍然認為編劇擁有自身的優勢,他認為未來10年劇本創作的主力是編劇,而非作家,因為“編劇對故事是最敏感的,具有電影化的思維”。
在他看來,編劇應該往更專業的方向努力,首當其沖的是要建立“類型意識”,“美國片就是細分類型,非常健康,每一種類型都有不同的受眾。”
陳舒提出,自我表達和市場無法兩全,是年輕編劇經常會碰到的困惑,而訣竅是將自我表達放進類型的框架之下,“本來類型框架就是創作者和觀眾進行溝通的一種姿態,我的姿態是寫一個大家所熟知的類型中的故事。”
編劇要走出“小黑屋”
這次中國電影編劇研討會上,一位觀眾提出,“目前的中國編劇都不太‘接地氣,他們應該了解現在觀眾的喜好,哪怕去到影院當售票員賣一天票,實實在在感受一下什么樣的觀眾喜歡什么片子。”這引起了在場編劇對于“接地氣”不同角度的更深層次的思考。
“接地氣”已經是創作上老生常談的一個詞,然而《心花路放》編劇董潤年認為,這個詞有被濫用和偷換概念的危險,“接地氣不是迎合觀眾,如果什么東西賣得好,我們就做什么,這樣電影就做死了。”
在《大明劫》編劇周榮揚看來,“最重要的是你劇本中呈現的東西,能不能讓觀眾相信。《哈利.波特》接不接地氣?但是它的觀眾會相信里面的世界,就是接了那個世界的地氣。”
“我在近3年最喜歡的電影,就是最不接地氣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豆瓣上有條評價這樣寫,‘看完電影后覺得語言匱乏,只想搬個凳子在電影院門口說,進來看吧。我覺得一個好電影給觀眾的應該是這個反應。我覺得應該有接地氣的電影,也應該有想象力飛升的電影。”束煥說。
陳舒認為,“一幫宅男,關在小黑屋里寫寫寫”的創作方式已經不成立了,“我們一直在玩耍,一直在走出去看這個世界,我們玩的聊的都是最新鮮有趣的事情”,這是陳舒“接地氣”的方式。
在張冀看來,“接地氣”其實是把觀眾放在心上,“比如龐麥郎的《我的滑板鞋》,就多么‘接地氣,我被他打動。這是一個在街上游蕩的小鎮青年,希望表達自己跟這個世界的關系,希望讓這個世界看見他。比如在這個4月,北京的空氣很糟糕,交通很堵塞。”張冀說。
他認為,“這時候電影就像一個溝通的工具,表達人們的焦慮,人們對現實的不滿足,對理想世界的希望。寫故事的原動力是什么,這對于編劇來講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