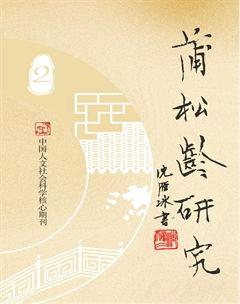《聊齋》叢脞錄
趙伯陶
摘要:《促織》作為《聊齋志異》中的名著,諸多《聊齋》選注本不可或缺,全國各地高中語文課本也為上駟之選。蒲松齡對于養蟲、斗蟋蟀并非內行,在寫作中明顯參考了明代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中有關捉蟋蟀的記述,指出小說中部分詞語借鑒前人之處,對于理解作者深刻用心大有裨益。“以蠹貧”三字何解?今人注釋多不準確,影響了讀者對于小說真義的探究。本文認為此三字語本《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比喻禍國殃民的人或事,這里即指皇宮“歲征”蟋蟀的弊政。
關鍵詞:聊齋志異;促織;帝京景物略;比籠;以蠹貧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識碼:A
《促織》中成名之子魂化蟋蟀,手稿本文字屬于暗寫,青柯亭本在刻印過程中或許編者認為作者針線偶疏,于是改“但蟋蟀籠虛”三句為:“但兒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成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為念。”又改“由此以善養蟲名,屢得撫軍殊寵”二句為:“后歲馀,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斗,今始蘇耳。撫軍亦厚賚成。”這樣就改為明寫成名之子“變形”的悲劇了。何者為佳?見仁見智,這里不做討論。有論者將此篇與唐陳鴻《東城老父傳》傳奇比較,唐玄宗喜斗雞與明宣宗喜斗蟋蟀,玩物之心,毫無二致;但前者因安史之亂險些亡國,關于后者,史家則有“蒸然有治平之象”的贊譽(《明史》卷九《宣宗本紀》),兩者實有所區別。至于有論者將《促織》與20世紀奧地利作家卡夫卡《變形記》之所謂“異化”說為比,則有些風馬牛不相及了。關于《促織》一篇的本事來源,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四《斗蟲》,明呂毖《明朝小史》卷六《宣德紀·駿馬易蟲》、明馮夢龍《三教偶拈·濟公火化促織》,明擬話本小說《濟顛語錄》中促織化青衣童子故事,清褚人獲《堅瓠集》馀集卷一《蟋蟀》,皆有論者指出其文獻依據,此處不贅。然而從作品圍繞促織的諸多民俗性問題,作者顯然從明劉侗、于奕正所撰之《帝京景物略》中借鑒良多,而且可證蒲松齡于斗蟋蟀之有關民俗細節不甚了了甚至疏漏之處,但他轉益多師,縱橫捭闔,亦可見其《聊齋志異》寫作的苦心孤詣之處。孟昭連先生《〈促織〉與〈帝京景物略〉》一文(載《齊魯學刊》2000年第3期),對此闡發甚多,可參考。
蒲松齡對于《帝京景物略》一書甚為熟悉,其《聊齋文集》卷三有《〈帝京景物選略〉小引》一篇小文,內贊劉侗等人之文筆有云:“其所為創,不直學,才也。”可見推崇。《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中有捕捉蟋蟀的描寫:“秋七八月,游閑人提竹筒、過籠、銅絲罩,詣草叢處、缺墻頹屋處、磚甓土石堆壘處,側聽徐行,若有遺亡,跡聲所縷發而穴斯得。”《促織》加以借鑒:“早出暮歸,提竹筒、銅絲籠,于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比較兩者文字,可見淵源有自。《胡家村》中又有“墳兆萬接”一語,就被蒲松齡直接用于《公孫九娘》一篇中,可證作者對《聊齋志異》反復修改潤飾的過程中多所取資的認真態度。
斗蟋蟀之風從南宋奸相賈似道于秋壑堂大開風氣之后,迨至明清乃至民國,社會上下皆有同好。明袁宏道《促織志》:“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群聚草間,側耳往來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廁污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饞貓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斗以為樂。”可見風氣一斑。作為一項民間娛樂,只要不過分,說不上玩物喪志,但帝王耽于此樂,則有可能誤國誤民,蒲松齡也正是站在這一立場上意欲進諫帝王的。比蒲松齡早生三十年的黃宗羲在其《明夷待訪錄·原君》中對于“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的封建帝王做過“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明確批判。黃、蒲兩者相較,在對待封建專制統治的態度上,前者比后者“異史氏曰”中的感慨,顯然進步多了。清方舒巖評此篇云:“以苛政論,宣德間不必有其事。然宮中偶戲促織,似亦無礙于治。烏知成之破產遭刑,幾至于死,而身復難存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是以事每忽于所微,而害常生于莫測。”這是從事理上加以判斷,已脫離對于專制主義的批判。可見蒲翁態度在當時仍有其前瞻性的積極一面。
《聊齋志異》全注本以外,《促織》一篇也是諸多選注本的上駟之選,高中語文課本也常能覓其蹤跡。然而選注者往往對于一些語詞的注釋卻不甚了了,有進一步商榷之必要。如“循陵而走,見蹲石鱗鱗,儼然類畫”,何謂“蹲石鱗鱗”?張友鶴先生《聊齋志異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下簡稱張注本)注云:“石頭一塊塊在地下排列著,好像魚鱗一樣。”中山大學中文系《評注聊齋志異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下簡稱中山本)注云:“石塊像魚鱗那樣密排著。”朱其鎧先生主編《全本新注聊齋志異》(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下簡稱朱注本)注云:“亂石蹲踞,密集像魚鱗。”盛偉先生《聊齋志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下簡稱盛注本)未出注,“蹲石鱗鱗”作“蹲石嶙嶙”。李伯齊、徐文軍先生《聊齋志異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下簡稱李注本)注云:“即前文的‘塊石亂臥。蹲石,叢聚的石頭。蹲,通‘僔,聚,眾多。鱗鱗,密集排列的樣子。”馬振方先生《聊齋志異:精選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下簡稱馬注本)未注。實則蹲(cǔn忖)石鱗鱗,意謂石層聚疊合如魚鱗一般,有層石相疊壓的意思,如此方能與魚鱗的狀況相合。蹲,聚集,疊合。《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晉杜預注:“蹲,聚也。”
“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何謂“覆算”?《漢語大詞典》解釋:“覆核帳目。喻指清算并做出相應的處理。”并以《促織》為書證。張注本注云:“再來算賬的意思。”中山本注云:“等于說算賬,意即追究。”盛注本作“覆算”而未出注,其馀各本皆作“復算”且不出注。在這里,“覆算”不當作“復算”,以《漢語大詞典》的釋義最為明晰,當遵從之。以筆者所見三種白話譯本亦皆以“算帳”或“算賬”為譯,雖不甚準確,卻也差強人意。endprint
“因出己蟲,納比籠中”,何謂“比籠”?諸多注本皆無注,唯盛注本注云:“評比促織大小的籠子。清陳淏子《花鏡·養昆蟲法·蟋蟀》:‘初至斗所,凡有持促織而往者,各納之比籠中,相其身等、色等。”再看白話譯本如何翻譯“比籠”。《聊齋志異評賞大成》(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下簡稱漓江本)譯為“旁邊的籠子”,《文白對照聊齋志異》(中華書局2010年版,下簡稱中華本)譯為“斗蟋蟀用的籠子”,《聊齋志異全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下簡稱上古本)譯為“比賽用的瓦盆”。梁宗奎先生《也釋“納比籠中”》(載《臨沂師專學報》1989年第3期)云:“據上,我們可以斷言‘比籠不是一個詞組,而是兩個詞。‘比籠不是‘比試的籠子,而是‘比于籠的省略。‘納比于籠是一個成分省略較多的句子,其主語為村中少年,整句成分全部補出為‘(村中少年)納(之——蟹殼青)比(之——小蟲)(于)籠,全部譯出是:村中少年將自己的蟲納入成名籠中與小蟲緊并在一起。這樣就言之成理了。”如此一來,“比籠”是否成詞都成了問題。
《漢語大詞典》收有“比籠”詞目,釋云:“用于盛放準備打斗的蟋蟀的籠子。”并以《古今圖書集成》卷一七五引明劉侗《促織志》“初斗蟲,主者各內蟲乎比籠,身等、色等,合而內乎斗盆”為書證,似乎明清飼養蟋蟀仍用籠子。唐五代至宋,飼養蟋蟀的確多用籠,有文獻可證。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二《金籠蟋蟀》:“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于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宋顧文鑒《負暄雜錄·禽蟲善斗》中所謂“鏤象牙為籠”,南宋姜夔《齊天樂·賦蟋蟀》小序中所謂“鏤象牙為觀貯之”,皆可為證。南宋以后至于明代,飼養蟋蟀已改用瓦盆泥罐,以適應蟋蟀喜陰之特性,明袁宏道《促織志》以及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等文獻皆有記述。飼養蟋蟀的工具稱“籠”,當屬于沿襲舊詞,上文“籠養之”當亦屬仿古之稱謂。一說“比籠”源于宋代的石質“比匣”,入明后改為陶質、瓷質或澄泥燒制的蟋蟀罐,為貯存斗蟲的專用器具,并非一般意義上理解的竹篦、木條或金屬絲制造的籠子。清顧祿《清嘉錄》卷八《秋興》:“白露前后,馴養蟋蟀,以為賭斗之樂,謂之秋興,俗名斗賺績。提籠相望,結隊成群。呼其蟲為將軍,以頭大足長為貴,青黃紅黑白正色為優。大小相若,銖兩適均,然后開冊。”所謂“提籠”,當為“提罐”,言“籠”,沿襲古稱而已。總之,所謂“比籠”,就是用于盛放準備打斗的蟋蟀的陶罐或泥罐。
“獨是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以蠹貧”何謂?“蠹”又何所指?張注本注云:“蠹:蛀蟲。這里指敲詐勒索的里胥像為害的蛀蟲。”中山本注云:“蛀蟲。這里指敲詐勒索的里胥。”朱注本注云:“蛀蟲,這里指里胥。”盛注本未出注。李注本注云:“蠹胥,害民之差役。這里指里胥。蠹,蛀蟲。舊時把暴政稱為‘蠹政,把為害民眾的官吏稱為‘蠹吏、‘蠹胥。”馬注本注云:“蛀蟲,指里胥等蠹役。”再看白話譯本。“以蠹貧”,漓江本譯為“因為讀書受窮”;中華本譯為“因蠹吏敲詐而貧窮”;上古本譯為“因為當上了鄉長而受貧”。王樹功先生《“蠹貧”別解》(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我認為‘蠹貧應解釋為因讀書謀取功名未遂而貧窮。蠹。這里是蠹蟲,書魚之意。”漓江本之譯文或許參考了王先生的“別解”,上古本的譯文則又別出心裁,可不論。其他注本或譯本皆以“蠹”為“胥吏”或“蠹吏”之謂,占大多數,與“讀書受窮”說堪稱處于“二元對立”的地位。現在在互聯網上所見高中語文教學有關課件,仍有并列兩說者。有關《促織》中之“蠹”何指,竟然聚訟至今,不得要領,的確令人費解。其實只要細心檢索有關工具書,這個問題并不難解決。
蒲松齡《聊齋志異》喜用典籍文獻之詞語,“蠹”即用《左傳》中語,比喻禍國殃民的人或事,這里即指皇宮“歲征”蟋蟀的弊政。語本《左傳·襄公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圣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圣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大意是:魯襄公二十二年的春天,魯國大夫臧武仲去晉國,天下雨,就去探望魯國御邑大夫御叔。御叔在他的封邑里,打算飲酒,就說:“哪里用得著圣人(指臧武仲)!我要喝酒了,而他卻冒雨出行,還要那些聰明做什么?”魯國大夫穆叔聽到這一番話后,就說:“御叔他不配出使,反而對使者臧武仲傲慢,是國家的蛀蟲。”于是下令將御叔封邑的賦稅增加一倍。蒲松齡故意將“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三句話郢書燕說,用其字面義“飛白”一筆,令“使”從“使者”轉換為“驅使”之義,從而語帶譏諷地批評了明廷禍國殃民的歲征蟋蟀之弊政。如果將“以蠹貧”理解為“因蠹吏敲詐而貧窮”或“因為讀書受窮”,不正確外,也消弱了小說固有的尖銳批判鋒芒。
(責任編輯:李漢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