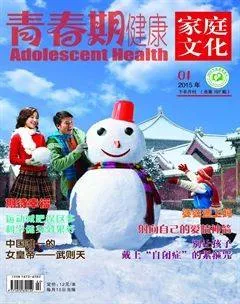青藤書屋
施立松
紹興城人文薈萃,古跡勝景比比皆是,可訪可游的太多,去青藤書屋是我提議的。
當地的同行說,沒什么好看的,很小的地方。
就徐渭那窮困潦倒悲摧不堪的一生,他的故居哪能不小。
這個明朝詩文書畫都有極高造詣的才子,留在我年少的記憶中,竟是他機智風趣懲惡揚善風流瀟灑的形象。記憶,來自于民間故事和連環畫。他人生的前二十年,雖然百日喪父,十歲生母被遣散出門(母親為父親的侍妾),母子分離。14歲,嫡母苗氏去世,他寄居同父異母的長兄家,飽受歧視,但他生性聰慧,六歲能讀,九歲能文,十歲仿揚雄的《解嘲》作《釋毀》,轟動全城,二十歲時被列為“越中十子”之一。年少才高,難免疏狂,或許,他真如民間故事里所說的那樣,有過恣意放蕩,快意恩仇,充滿青春活力和希望的錦繡歲月。
真希望他就那么衣袂飄飄地行走在那風煙四起的塵世里,讓后世仰望,欽佩,甚至解恨般的展顏一笑,讓我穿過時光的紛紛亂雨,遁著他的身影,聽一支短笛,在歲月的荒郊清脆響起。
可是,老天對他,實在太不厚道。他的后半生,簡直可用悲慘來形容。
從魯迅故居出來,陰了半天的天,終于下起了細雨。秋風細雨,寒意侵體,讓人心生惻惻。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路過人滿為患的咸享酒店,再往前走,右拐,就是青藤書屋所在的大乘弄。兩面高高的黑瓦白墻夾成的巷道,偶有幾扇門戶,卻都緊閉著,巷道窄小,彎曲,足音便得得地回響起來,恍若走在長長的隧道里。喧鬧的車聲人聲都已消失,仿佛剛才熙來攘往的人潮,都是幻覺。巷道左側,一陣枝葉簌簌聲,自洞開的木門后傳來,一簾翠竹,兩棵高大的芭蕉,映入眼簾,遁聲而望,簌簌的聲音,來自墻角一樹高大的枝繁葉茂的女貞。雨點打在葉上,葉隨風而落,腳踩在落葉上,腳底聲音熱鬧著。這就是青藤書屋了。
沒有游人,除了我們。
在城市一隅偏安,在小巷深處靜默,這青藤書屋像曾經的主人徐渭一樣,必受冷落。人跡罕至,這倒成就了它的清雅之氣。墻角四缸青翠的浮萍,堪比春天的顏色,映得斑駁老墻,像一張被墨汁浸透的宣紙,筆意縱橫的,是歲月的狂草。三棵石榴虬枝交錯,葉還綠著,卻失了血似的憔悴,當年“榴花書屋”之名,由此而來否?芭蕉結了一串青色的果子,藏在闊大的葉后,半隱半現。一塊鐫了“自在巖”的小石刻,就在芭蕉旁的墻上,據說,這三個字是徐渭親筆手書,卻被蒼綠的芭蕉映得沒了顏色。
這一切,都符合我對青藤書屋的想象。每個故居里,都居住著一個歲月無言的傳奇。
穿過月洞門,是一方小池,池水清淺,池壁蒼苔密布,幾只紅魚游弋,小小的身影,嬌怯可憐。池中立有一柱,柱上 “砥柱中流”四字,為徐渭親手所刻。“此池通泉,深不可測,水旱不涸,若有神異”,是徐渭所愛,他在此梳洗濯發,舀水磨墨,并稱此為“天池”,意即天賜之池。
想來,那時,他雖命運多舛,考中秀才后,三年一次的鄉試,連考八次,次次落榜,“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人且爭笑之”,卻還不至窮困潦倒。真正凄慘的命運,自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開始。因被胡宗憲(抗倭名將,徐渭當過他的幕僚)案件牽涉,時年45歲的徐渭貧病交加,焦慮恐懼導致精神錯亂,他寫好墓志銘,毅然決然地要告別這個荒涼而丑陋的人世。如果這個時候,自殺成功,也算是命運對他的眷顧,可是上蒼顯然不想輕易放過他。在他用利斧敲擊頭蓋骨,“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在他將一寸多長的鐵釘戳進兩耳,七竅流血;在他用鐵器擊碎睪丸,痛得滿地打滾,上蒼仍殘忍地讓他繼續茍延殘喘。后來,因幻覺懷疑繼室張氏不貞,他失手將她殺死,而入獄七年,肉體飽受摧殘,良心備受折磨。出獄后,貧困潦倒、惡疾纏身的徐渭以賣畫賣書為生,可惜“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忍饑挨餓是常事,但凡權貴上門求書畫,他卻手推柴門大呼:“徐渭不在!”堅決不給權貴作畫。1593年,也是這樣寒風瑟瑟的深秋,徐渭凄涼地走了,73年的人生,布滿辛酸和磨難。什么叫貧病交加,什么叫家徒四壁,看看那時的徐渭吧,他的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三十多年后,堪稱他的知已的袁宏道如此深嘆。
“天池”的另一側,是一木格花窗平房,門口掛著“青藤書屋”的木牌,小小的,僅尺余。房內陳列著徐渭的詩、書、畫、文。那力透紙背的筆墨間,獨特而清冷的線條里,淺淡或絢麗的色彩中,分明是他對抗那個丑陋的世界,對抗那坎坷悲慘命運的孤獨又不屈的身影。他的詩得“李賀之奇,蘇軾之辯”;他的文潑辣機智,幽默多趣,文風遠啟金圣嘆一流;他的字“誠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俠客”;他是中國大寫意畫派的宗師,擅寫意花鳥,用筆放縱,水墨淋漓,不拘形似,氣格剛健而風韻嫵媚,具有詩一般的抒情性和韻律感,自成 “青藤畫派”,一代大師鄭板橋曾自命為“青藤門下走狗”;他還是戲曲家,對佛經、道術、醫學、兵法都有研究。在胡宗憲門下時,為抗擊倭寇,他常常深入前線,觀形勢,度地形,施奇計,作方略,屢立奇功。
天妒英才啊。還是世道不公?
格花窗外,三條青藤貼墻而上,扭曲,冷硬,糾葛,堅忍地向墻外攀爬而去,仿佛一個寂寞的靈魂,在蕭瑟的浸滿血淚的歲月里煢煢孑立。這棵青藤,是明末清初畫家陳洪綬在此處居住時所植吧,“青藤書屋”便更名正言順了。而今,“青藤書屋”被刻在一片漆了桐油的木片上,綠色的字影,仿佛是青藤的新芽,油亮青翠地從歲月深處探出頭來說:貧病又怎么樣,誰能如先生這般,精神的端莊心靈的潔凈?
也再沒有誰更合適如先生般,風流倜儻地行走在樸素而親切的民間故事里,行走在生命最初最純凈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