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中國史
他者的中國史
Point
歷史研究的使命在于揭露真實,但多數情況下,真實其實是達不到的,甚至只有關于歷史的敘述,沒有真實的歷史,因此對歷史的闡釋顯得尤為重要。
海外中國研究素為國內學界和讀者重視,漸成顯學之勢,原因除了材料的豐贍以及寫法上往往別開生面之外,首要在于他者的言說更宜作觀照自我的鏡鑒。身處中國的我們卻往往忽視了所謂“中國”,其實于自己也是他者。當我們談到“中國”時,其實是在談論某一時空的文化共同體,它是流動不居的,而絕非固定的。不是“天不變道亦不變”,而是疆域屢屢變遷,文化也處于不斷變遷之中。所謂的中國傳統,本質上其實是一種變遷的傳統,正如湯之《盤銘》所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國一方面極其保守,另一方面又極善于變通,不斷吐故納新,把異質整合進自身傳統中,也把自己變得面目全非。我們面對蕪雜的中國歷史時的無從把握,很多時候是出于對這種既穩定又多變的文化性格的無所適從。
作為被譽為美國頭號“中國通”的費正清,自是深諳中國傳統與變遷之道。誠如百度百科的介紹,他關于中國問題的許多觀點在西方外交界和史學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而他主編的煌煌十五卷本的《劍橋中國史》對中國學界的影響,亦無須贅言。《費正清中國史》(即《中國:傳統與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劍橋中國史》的一個縮寫本,一次壓縮掃描。
作為一部通史,時間上的縱深是必不可少的,與許多通史相比,《費正清中國史》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橫向的寬度。此書是在世界視域內觀照中國,從而有著國內通史中很少出現的諸多比較。如它提及西亞出現古代文明基本要素的時間遠遠早于東亞,泰國北部的青銅器文化早于西亞,黑陶文化則顯示來自西亞的影響已經進入華北地區。這些看似無足輕重的細節,都帶給人跳出中國中心論觀看中國歷史的異樣觸動。旁觀者清,費正清幾乎是輕而易舉地看到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政府或教會,看到中國產生惰性的原因在于統治階級的世界觀或自我心像,而這些都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政治文化形態與面貌的生成。
《費正清中國史》行文雖簡,但不放過歷史的任何關鍵節點。如公元747年,高仙芝在怛羅斯之戰中被大食人擊敗,標志著中國對中亞控制的結束。這同時宣告漢族政權最后一次擴張的結束,從此轉向收縮。如此重要的事件,其意義在坊間眾多中國歷史讀物中卻很少提及。再如,他大膽地將唐攔腰斬為兩段,將盛唐和晚唐分別歸入古代和近代,原因是晚唐與此后一千年中國文化的一體性。費正清寫到:“隨著摒棄外來宗教和面對異族入侵時的節節敗退,中國逐漸失去了六朝和盛唐時的世界主義思想和文化寬容態度,代之而起的則是狹隘的民族中心主義思想。”這體現了研究者頗具大歷史觀的卓越洞識。
歷史研究的使命在于揭露真實,但多數情況下,真實其實是達不到的,甚至只有關于歷史的敘述,沒有真實的歷史,因此對歷史的闡釋顯得尤為重要。歷史的詭黠在于其所因循的規律并非自然法則,歷史的走向也不是簡單的因果律所能決定的。在費正清看來,中國缺乏進取,每一次變化都是外力的結果,即著名的沖擊—回應模式,這大致可以對應哈貝馬斯的“實然”與“應然”。中國長達八百年的超穩定結構,是因為“中國政治社會思想在十三世紀形成了一種平衡,且在當時思想技術條件下達到完美的程度,這種完美的平衡到了19、20世紀在經受了外界的劇烈破壞和撞擊后仍未完全打破。”而中國的落后也正是因為這種穩定,“當外界壓力增強時,中國便暫時做出應對,危險過后依然故我。”與日本相比,同樣經歷堅船利炮,中國沒有類似明治維新的改革,沒有迅速地現代化,“是因為中國社會十分龐大,組織亦極其穩固,因而無法迅速轉化為西方的組織模式。”“若不徹底摧毀舊的社會結構,就無法建立起現代化的中國。”正是基于這種普遍認識,才有了視傳統為洪水猛獸,有了打倒孔家店。但狂飆突進的結果簡直令人瞠目結舌,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與中國古代大同社會理想庶幾合一。甚至今天社會主義三步走的宏偉規劃,與康有為提出的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演進秩序也幾乎完全相同。從這一點上,我非常認同譯者張沛在此書譯后記里的概括:“變遷是傳統的前景,前景是變遷的歸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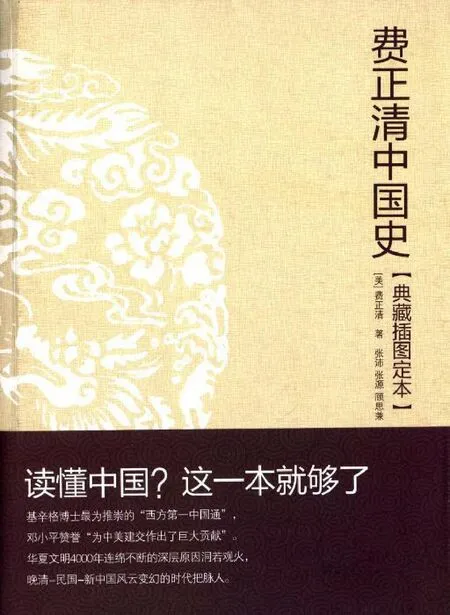
費正清深知“中國歷史并非發生在中國所有人的思想觀念中,而是發生在中國人中的思想觀念”,因此格外關注大歷史背后的思想資源與動機。中國歷史上曾有兩次大規模的外來文化進入,一是東漢至隋唐佛教的傳入,另一次是晚清以基督教文化為先導的西學東漸。佛教文化成功地實現了中國本土化,而基督教文化卻沒能如愿,倒是民主和科學這兩個相比之下更工具性的“陪嫁丫鬟”被奉上神壇,擁有了意識形態的功能。特別是科學的意識形態化,是一個大可商榷的問題。不但傳統文化的很多內容因不夠科學而遭“揚棄”,馬克思主義最初在林林總總的外來學說中贏得國人青眼,也是因其以科學自居,正好滿足了時人對科學的迷信。它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生物進化論的社會科學化,“解釋演化的真義,闡明紛繁復雜的歷史事件”。馬克思主義似乎為迷路中的中國提供了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一套完整理論,而蘇俄的成功,又為中國革命道路提供了方法,二者結合的誘惑力可謂巨大。
從天下正中到萬國一員,從民族國家到社會主義新邦,中國歷史事實的變遷對應的是一系列國家觀念的變遷。在歷史最近的一次大的選擇契機中,中國選擇了蘇俄道路,而不是英美模式。“革命以烏托邦社會為目的,烏托邦以革命為表達方式。(金觀濤)”嗣后發生的種種,幾可證出以俄為師無異于以病為藥。中國主流話語習慣于將革命的勝利敘述為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結果,反倒應和了古代的天命配德之說。除非將今人正在經歷的歷史視為一個尚未完結的大歷史循環中的一部分,否則很難釋懷這樁迷思。
像湯因比《歷史研究》中所寫:“追求歷史的好奇,不僅是一種知識的活動,而且是一種感情的體驗。”即使通過費正清冷靜的他者的目光,讀者仍然可以撫摸到中國歷史的體溫和脈息。通過閱讀的傳遞,那曾經灼熱的心靈也灼傷著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