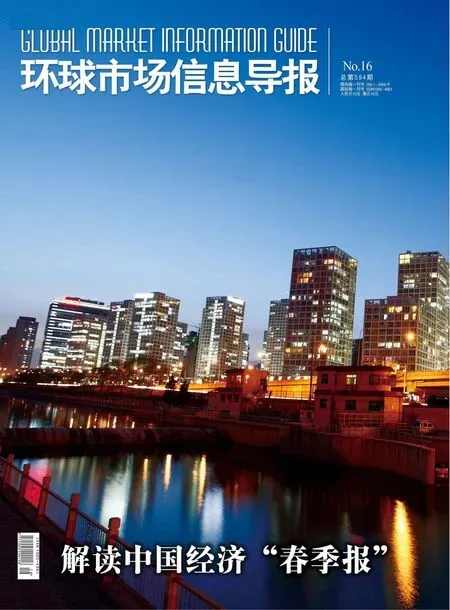李健:帶著萊昂納德·科恩的詩集去唱歌
李健:帶著萊昂納德·科恩的詩集去唱歌
李健一直認為自己的歌具有“反思性”,當初離開水木年華,有一部分原因也在于不想再寫愛情歌曲,他把目光投向現實生活中,甚至公共事件也成了創作的來源。
“他是那種喜歡獨處、靦腆羞澀的男人。不過如果你刨根問底,他也不會失風度地幽默應對。他的回答措辭謹慎,像是一位詩人,或是一個政客,精確、隱晦、富有韻律、避重就輕;他愛放煙霧彈,說話時顯得詭秘,一如他唱歌,仿佛是在吐露隱秘。”
英國作家西爾維·西蒙斯在游吟詩人萊昂納德·科恩的傳記開頭如此描述他。把這些形容放在歌手李健身上時,似乎并不違和。事實上,科恩恰恰是李健最推崇的一位音樂創作人,他長久地從科恩的音樂中汲取養分,一遍遍地讀科恩的傳記。最終他把這種熱愛帶上了舞臺——在《我是歌手》最后一場淘汰賽中,他穿著筆挺的西裝,拿著一本科恩的詩集上了舞臺,他并沒有朗誦其中的詩歌,而是把它放在了凳子上。“我想要萊昂納德·科恩賜予我更多的低音”,他事后解釋道。李健身上的文青氣質大受歌迷的歡迎。
從2001年水木清華組合發行的第一張專輯《一生有你》到現在,已經過去了15年,但從2015年1月參加《我是歌手》后的兩三個月里,李健接受采訪和登上雜志的次數比之前加起來還要多——他上一次受到大批媒體關注還是2010年,那年的春晚上,王菲演唱了他的《傳奇》。2015年3月18日,離《我是歌手》突圍賽只剩兩天時間。李健出現在《ELLEMEN》的攝影棚時穿著一件白色的連帽衫,看上去很像一名剛出校園的大學生。
除了幾乎在《我是歌手》的每場比賽中穿著西裝出場,出道十五年來,李健的形象并沒有太大變化。在“水木年華”出的第一張專輯封面上,他穿著短袖T恤和盧庚戌站在一起,各自望向遠方。離開“水木年華”后,他發行了六張專輯,沒有任何緋聞和炒作。那時,他的形象干凈、清澈,歌曲的題材大多跟青春和故鄉有關。

李健出生在哈爾濱的一個文藝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京劇演員,他從小在京劇團的院子里長大,在一篇回憶文章里寫道,“哈爾濱的人們喜歡談論生活,尤其喜歡談論自己遙不可及的事情,甚至是高于生活的形而上的問題。”在一個談話節目中,一位舊時好友回憶,李健在小時候就很喜歡唱歌,去朋友家串門,可以唱一宿的歌。這位兒時的伙伴仍然記得去李健家時,看到他用一小塊窗簾給自己圍出一個狹小的空間,一個人在里面彈琴唱歌。
樂評人李皖第一次聽到李健的歌時,認為他像極了齊秦,“從他的第一張個人專輯開始,李健自己的音色,逐漸從齊秦的聲音中脫胎而出,這音色有更多的輕盈,更少的人間煙火,像一只光滑發亮的瓷器。”
也有人質疑他的風格沒有變化,但李健認為自己很早就走上了個人創作的節奏,這意味著他創作的目的是只為了自己。“就像所有的真正寫作都是個人化寫作,并不是你換了風格就失去了聽眾,與其擔心,這應該不是問題,首先你不會換風格,因為一個人的寫作風格是非常有限的,你的語言就屬于你,別人之所以這樣才喜歡你,如果你改成別人那樣,別人也沒有聽你的必要了。”
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李健發現很多考試對自己來說很難,但其他同學能輕松拿到滿分。但在各類音樂比賽中,自己總能拿到第一。在清華大學他看到了在各個方面有過人之處的人,早早地明白了一個道理:各行各業都需要天賦,人必須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這讓他開始專注在音樂上。
李健的音樂天賦逐漸顯露,他曾在清華給九支樂隊伴奏并獲得全國大學生歌曲比賽金獎。他的母親試圖勸說他不要從事演藝事業,他并沒有聽從母親的勸告,從清華畢業后,他進入了國營單位,兩年后辭去工作,開始音樂創作。早在“水木年華”時期,李健就獲得了業界專業音樂人的肯定,這讓他對自己的音樂有了自信和篤定。“我一直都很自信,因為最早的一批聽眾就是業內人士,他們告訴我你的音樂品質是沒有問題的。《傳奇》也好,《麥浪》也好,無非是更加驗證了這樣一個事實。”
這十年中,因為對聲音的要求很高,歌詞文雅古典,表達上習慣使用隱喻,李健的歌并未被廣泛傳唱。但他并不認為那是他的艱難時光。他有著非常健康的作息和創作習慣,對物質的要求并不高,人們總是想象一個人在成名之前過得潦倒,李健對這種想象非常警惕,他反復提到生活的重要性,“生活并不是為了這一件事情。音樂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說音樂不是你唯一的命題,更不是你唯一的煩惱。”李健坐在沙發上,他剛剛結束半天的拍攝,“生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你依然需要每天一日三餐,你不能說那八年或那七年我天天只做一件事情,就磕這一件事情,生活上也有很多比音樂更有趣的事情。”

李健認為自己在生活里是個極其“正常”的人,“不是那種神經質的,也不是自毀的藝術家,把自己折騰得天翻地覆,傷痕累累的,我可能更愿意區分什么是生活本身,什么是物態,什么是藝術作品,什么是生活的實質。”他的歌大多取材于自己的生活,他熱愛閱讀和旅游,在《我是歌手》其中一期采訪中,鏡頭對準了他的書房,書架上有《哈扎爾辭典》《文學回憶錄》《茨維塔耶娃文集》《博爾赫斯全集》,《傳奇》的靈感就來自于茨威格的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民謠歌手在這幾年里集中爆發,鐘立風、小河、萬曉利等都逐漸被更多人認識和喜愛。李健在“我是歌手”的淘汰賽上選擇了萬曉利的《陀螺》,因為審查的關系,有兩句歌詞在演唱時被修改了:“在不可告人的陰謀里轉”成了“在深不見底的黑暗里轉”,“在東窗事發的麻木里轉”改成了“在任由天命的麻木里轉”。樂評人耳帝認為,這首歌讓李健的人文形象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傾向才算真正鮮明了起來,比此前文青層面的選歌上了一個臺階。陀螺有一種眾生宿命的象征,或者是世俗苦業的象征,在不斷抽打中維持運轉,所以他結尾也第一次表現出了力量,似乎在表達對抗意識。他的變化不在樂性上,而在寓意上。
李健一直認為自己的歌具有“反思性”,當初離開水木年華,有一部分原因也在于不想再寫愛情歌曲,他把目光投向現實生活中,甚至公共事件也成了創作的來源。他的專輯里有一首名為《松花江》的歌,它隱喻了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歌詞中這樣寫道:“松花江水/我童年的海洋/哺育我們成長/替我們受傷”。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對現實的反思,認為自己是個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歌手,“我的歌一直都有反思的色彩,只不過是隱藏著的,包括歌詞的意欲和表達方式,是內斂的,也是節制的。這種社會責任感并不是通過標榜個性來呈現的,是對自己不自覺的一個意識的闡釋。”在談話的尾聲,話題轉向了“困惑”。他引用“你不關心政治,但政治關心你;你不關心天氣,但天氣關心你”來說明當下的處境,“隨著年齡的增長,你的困惑是否會減少?”我問,他想了一會兒,“恰相反,困惑會越來越多。你無暇應對,或者說你惑不惑,困不困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你可能已經懶得去解決它,人并不是說沒有困惑才能生活得更好,有困惑一樣能生活得更好,一樣能活,是否能解決你的疑惑,已經不是你生活的一個主要目的,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