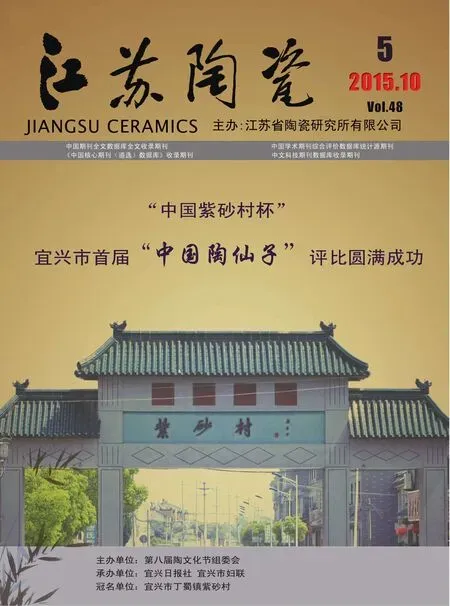謙謙君子之紫砂“六方竹壺”的風韻
吳君蘭
(宜興 214221)
制陶技藝是中國的傳統技藝之一,一直傳承至今,中國極具特色的紫砂藝術備受世人推崇,紫砂壺的發展是一個推陳出新的過程,以傳統作為根脈,以創新為基調,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紫砂藝術蓬勃發展,使其成為我國制陶藝術發展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紫砂藝術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發展體系,其造型款式呈多樣化發展,且與茶文化、雕塑、書畫、陶刻等相互融合,博眾家之長,得其精髓,拓展其發展空間,促使紫砂壺從日常生活器具向兼具實用性和藝術性的方向轉變,極具文化內涵,為人們的生活增姿添彩。
1 紫砂壺造型特點
紫砂壺具有幾百年的發展歷史,因文人雅士的參與,富有文人氣質,敦厚樸實、氣質獨特。總體上講,可將紫砂壺分為四個類型,即:圓器、方器、花器、筋紋器。圓器珠圓玉潤、儀態豐滿,方器線條簡明、輪廓周正,花器古樸自然、惟妙惟肖,筋紋器結構嚴謹、巧奪天工。任何一種都蘊含著紫砂藝人對紫砂文化獨特的見解,創作中反復推敲,將其與自然萬物巧妙結合,以增風韻。紫砂“六方竹壺”(見圖1)為典型的方器,延續了傳統六方壺造型特點,但有所變化,壺身線條簡潔、輪廓分明,與壺肩平滑連接,兼具陽剛與柔性美,構造新穎,讓人油然升起一種喜愛之情。

圖1 六方竹壺
2 紫砂“六方竹壺”的造型藝術
方有正直、穩重、端莊之意,圓給人以靈活、變化、圓通的感覺。這款紫砂壺方中寓圓,穩中求變,端莊中又不失幾分活潑,陽剛中又帶有些許柔情,極具表現力。“六方竹壺”采用立體結構進行作品創作,由六個光滑平面組成,對稱性強。壺身上腹略向外凸出,壺腰內收,整體呈上寬下窄狀,簡單明快,無一絲贅余;壺蓋為圓形,與壺身筋理紋形成鮮明對比,可謂剛柔并濟;壺蓋之圓,壺身及其他結構的方形,共存于該壺,體現中國文化中融合的精神;壺鈕呈拱橋狀,坐落于一彎清水之上,形成一幅小橋彎彎、流水潺潺的江南水墨圖,風光無限好,增加了視覺上的美感,使整把壺更具藝術性;壺鈕竹結節有竹枝長出,輕輕落于壺蓋上,有錦上添花的作用,展現出文人的高風亮節;三彎壺嘴,與壺蓋齊平,每處彎曲部位都有竹節自然承接,自近壺身竹節處有竹枝長出,竹枝蜿蜒向下,映于壺身,俊雅秀麗,一陣微風襲來,竹葉輕輕搖曳,隨風翩翩起舞,風雅生趣;耳型壺把,起至壺肩落于壺底,由粗到細,正是依竹尖而制,生動形象,與壺的整體形象相符;壺鈕、壺嘴、壺把均取形竹子,剛勁有力,生機盎然,三者遙相呼應,配合得當,線條明確、挺闊端正、力度十足,極具陽剛之氣,正如君子正直品性,浩然之氣蕩然而出,體現出文人的錚錚傲骨;壺底有矮足,支撐起整個壺身,顯得壺身婀娜多姿、豐滿姿態。線條是紫砂方器重要的藝術表現形式,紫砂“六方竹壺”以直線為主,均勻分布,富于變化,增加視野上的開闊感;曲線為輔,弧度圓潤,柔化了壺身棱角之剛硬,更增婉約大方之意,意境深遠。
3 紫砂“六方竹壺”的文化內涵
竹修長挺拔,四季常青,與松、梅并稱為“歲寒三友”,與梅、蘭、菊并稱為“四君子”。自古至今,詠竹者眾多,在中國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鄭燮《竹石》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展現出竹子的錚錚傲骨;劉禹錫《令狐相公見示贈竹二十韻·仍命繼和》曰:“峻節可臨戎,虛心宜待士”,體現出文人的堅貞不屈的品格;袁牧《芟竹》云:“竹性不耐雜,志在干青云”,體現出竹不與世俗同流、志向高潔的品質。竹在中國古代是美好品質的載體,自古便被視為君子的象征,挺立于風雪之中,不輕易壓折,體現其正直的氣節;竹內中空,虛懷若谷,具有謙遜的品質;群而居之,疏密適宜,有神仙卓然超群之姿。此外,竹與“祝”諧音,寓意結節高升、祝福平安。宜興為典型的江南水鄉,竹林成片,紫砂“六方竹壺”以壺為創作原型,細細把玩之,猶如置身于竹林中,舒適愜意,悠然漫步獨行,感其姿態清雅,嘆其高尚氣節,可深化人的情操,告誡人們正視人生中的困難,迎難而上。
4 結語
紫砂“六方竹壺”創意新穎、構造合理,取型竹子進行作品創作,賦予壺以靈魂,增加其生命力;該壺以方為主,筋紋分明、穩重大方、富有氣節,方中寓圓,使得整只壺的線條富有變化性,承接自然,剛直而不失優雅,豐滿中帶有幾分靈氣,展現出“不務妍媚而樸雅堅粟”的氣質,符合世人的審美情趣,不僅展現了世人對超然淡泊生活的向往,也表達了紫砂藝人對竹子堅韌不屈、高風亮節等氣質的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