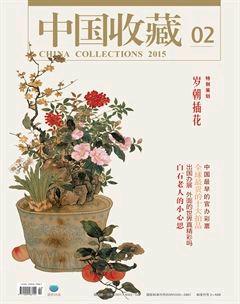沒有想像中“美好”?
王菁菁
如同出國深造一般,無論是“殿堂級”的威尼斯、圣保羅雙年展,卡塞爾文獻展,還是其他類型級別不一的展覽,中國藝術家們“走出去”不再是件高不可及的事,而人們從一些到國外辦展的藝術家名單中也不難發現,除了“標桿式”的藝術家外,越來越多的、占據相當分量的則是那些“新面孔”們。
有正規的
作為全世界最重要的三大雙年展之一,能夠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一直以來被眾多藝術家視為生命中的驕傲與榮耀。當然,中國的藝術家們也不例外。
1980年,“民間剪紙”參展威尼斯,掀開了中國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序幕;1993年,14位中國藝術家接受了第45屆威尼斯雙年展的邀請,參加雙年展的主題展,促進了其他頂級展事對中國當代藝術的關心,這被不少人看成中國當代藝術圈文化輸出的一個“里程碑”式范例。
一晃20余年過去,對比當年連想看個好展覽都得坐很長時間火車趕到北京的“艱辛”,現在社會的發展、信息的多元化早就不能同日而語。
柳淳風是中國美術館研究與策劃部策展人。就在兩個多月前,她剛結束帶領藝術家赴韓國釜山雙年展辦展的工作,這是亞洲地區非常重要的雙年展。談到中國藝術海外輸出的話題,這位爽朗的湘妹子深有體會。
“像出國辦展這樣的文化輸出,顯然屬于國家文化戰略的部署推廣之一。通過官方途徑走出去是最為正式的一種表現。不過,由于真正的文化是自然生長的,因此現在我們能看到一些民間力量也會投身其中。”
以體制內的操作模式為例,她告訴《中國收藏》記者,比如中國美術館,每一年或者每三五年都會有一個整體規劃來對接具體的文化項目安排。通常情況下,類似公立美術館這樣有官方背景的文化輸出項目,大致分為幾個類型。
一種類型是參加藝術節,主要是由文化主管部門牽頭。“例如在歐美、澳大利亞等國定期會有藝術節,以參展的國家形象作為主題。比較近的例子有2010年在比利時舉辦的‘歐羅巴利亞 中國藝術節’,以‘中國’為元素。當年中國美術館在布魯塞爾的圣地安廣場圍繞主題做了40多個展覽,我個人承擔策展了三五個,至今都印象深刻。像這樣的藝術節是文化輸出一個很重要的形式。”柳淳風介紹道。
另一種常見的形式則是館際之間的交流,例如中國美術館與美國MoMa這樣海外著名的藝術館、博物館合作,雙方展覽“一進一出”,也屬于一項重要的國家間文化交流。
至于第三種形式則是公立美術館獨立輸送展覽至海外展出,“中國美術館在海外做過很多不錯的展覽。比如去年,中國美術館就輸送了一批展覽分別到諸如韓國國立美術館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館際交流的模式中,我們往往會選擇用當代藝術的形式、模式將展覽送出去。這是出于老外對中國傳統藝術或者民間藝術,隔閡仍然比較深的考慮。而當代藝術屬于一種國際通用的語言,其交流障礙小。”
隨著近年來全球各類雙年展的陸續涌現,柳淳風發現,比之十年前,這些展覽對于中國藝術生態的影響正在減弱,她認為這與時間、資本對于藝術的影響都有很大的關系。
有“水深”的
據悉,十年前,民間要依靠自我與資本的力量將展覽推向國際舞臺,比如不依靠官方背景,而是通過畫廊的運作來帶領藝術家走進類似威尼斯雙年展這樣的“殿堂”,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這樣的體制在當時看上去就像是“神話”,權利牢牢掌握在相關策展人的手中。
然而近幾年來,社會的多元化讓藝術圈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尤其是2005年左右,當代藝術全面崛起后,各種資本力量對于學術的削弱比較明顯,致使策展人的權利逐漸減少。現在,不用依附體制,一些機構、民間力量也完全有“能力”來操作如此,比如藝術家通過出資的方式,在機構或有話語權的策展人帶領下參加雙年展的平行展、外圍展等。最近一屆的威尼斯雙年展期間,大量的中國藝術家參與的平行展的出現,就被輿論稱之為“把資本運作下的中國式平行展模式演繹到了極致”。名氣響亮的展覽尚且如此,那些偏小眾的藝術節或展覽就更不在話下了。
與此同時,帶著藝術家作品走進國外各大博物館、美術館以及研究機構的宣傳,本身就是十足的誘惑,名頭越響誘惑越大,藝術家愿意“掏腰包”不難理解,甚至有業內人士以“自費旅游”來戲稱之。
趙榮水是中國藝術文化普及促進會的秘書長。據悉,這是文聯下屬的一個國家一級協會組織。在接受《中國收藏》記者采訪時他表示,帶領中國書畫家赴海外辦展,這是近十余年來他們一直在做的事。“遠的地方有歐美、中東,近的有港臺地區。辦展地點有的在大學,有的是在藝術中心。”他說,“我們有一個考評專家委員會,人員組成各個層面上的都有,根據每一次出國辦展的主題,我們選擇藝術家進行通知。”
這當中有個小“插曲”,據相關媒體于去年11月的報道,由于未按規定接受相關年檢,該協會以及其他兩家協會接受了民政部關于暫停活動半年的處罰。而采訪中趙榮水也提到,自去年起他們停止了書畫出國辦展這個項目,不過至于原因,“是因為效果一直不大好。在我們的操作模式中,如果有贊助,藝術家出國辦展可以免費。但如果缺少贊助,或者他們要帶親友同行,是需要承擔一定費用的。這就牽涉到一個經濟效益的問題,否則很容易讓他們感覺沒有后勁。”他解釋道,并透露現在協會已經把精力更多轉向到寶石的收藏推廣上。
有知情人士認為,其實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在中國當前的體制下,做展覽輸出按理應該經過一定的申報程序,只是其中有“嚴與松”之分。據悉,比起來,國家背景、官方機構的送展至少在層面上肯定要把關得很嚴格,文化部門對此有一定的控制。但身處開放的社會中,民間的操作難免存在“用不同的方法辦事”,所以,很多不同渠道送出去的展覽,國人既看不見,也不清楚產生了什么效應。分析人士指出,這跟對展覽的宣傳、本身的學術性和目的都有關系。
如果說官方機構操作于此是一種“名正言順”;畫廊等民間力量的涉及是一種“能力”體現,那么,當前越來越多類似中介、“掮客”等形式的出現,就不得不令人備感“水很深”了。
“據我所知,像個人或者中介機構做這些事也分情況。稍微正式一點兒的,比如機構有這樣的海外資源對接,或者是個人長期生活在國外有一些‘門道’,介紹藝術家出國辦展在他們看來‘幾方共贏’。而不正規的,會向知名藝術家要作品,向一般或者不出名的藝術家要費用,至于能不能辦成展,辦什么樣的展,那就是未知數了。當然,無論是哪種情況,辦展地點的名頭無疑是對藝術家而言最好的‘回報’。”北京一位長期混跡于藝術圈的經紀人向《中國收藏》記者透露道。
別成自娛自樂
事實上,除了書畫這種最為常見的“走出去”領域之外,現在,現當代陶瓷、紫砂等中國傳統藝術的“語言”代表也已開始邁出了走向國際的腳步。看慣了各種各樣類似的消息,關注藝術圈的人們自然會心生疑問,老外對于這種“造訪”買賬嗎?而中國的藝術家們又能在這種方式中收獲多少?
采訪中,一位與中國現當代藝術陶瓷圈有過長年交情的人士向記者舉了個例子,頗耐人尋味。據其介紹,前段時間,曾有一批中國現當代陶瓷藝術家經介紹到大英博物館辦展覽。但這一讓外人艷羨的榮耀在他們眼中卻并非美事。“說是大英博物館,其實就是在他們類似地下室的場所舉行。”


據業內人士透露,其實像上述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當前,歐美的經濟環境不景氣。可以說,經歷過經濟的高峰和低谷,歐美人比亞洲人更懂得經濟的波動,他們對于資本的理解也跟國人不一樣;但在另一方面,自歐美現代主義興起以來,他們的社會整體而言是非常尊重藝術、尊重專業的,對于藝術有著自己的把握。“所以在歐美知名的藝術機構中,容易發生這樣的情況:一邊是他們不會太拒絕國人出資去做展覽;但另一邊,也不會發生‘你掏錢,我就幫你展,由你說了算’的情況。因此,類似這種在大英博物館地下室辦展的情況是信息不對稱和文化缺失的表現,值得引起業界重視。”柳淳風認為。
至于老外們買不買賬,最有發言權的恐怕還要回歸到作品質量上。福建籍畫家呂德安曾在美國生活過多年,“兩頭跑”的經歷讓他對這種現象感觸良多。“坦白說,國外的普通百姓對于東方文化仍然是比較陌生的,像中國山水畫這種直指國人心靈的東西,他們卻不一定能看懂。倒是當代繪畫,確實有著跨越藝術平臺的潛力。好的藝術是跨越民族的,國外的人認不認,除了認識的差異以外,最主要的制約因素肯定還是內容。我們的藝術家具備什么樣的水平,自身是否仍需要提高,都是問題。同時,也可能與相關機構的推廣力度有關。”
天津泰達當代藝術博物館館長馬惠東的觀點則更是直率,“不管你以什么樣的表現形式走出去,內容是最本質的。最近我和幾個圈內朋友聊天時,還談到在國外連出租車司機都知道艾未未的話題,為什么?這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
不過,盡管“熱情”不一定有理想的回報,盡管“海外鍍金”的市場復雜,盡管伴隨著國內藝術品市場的理性回調,抱著理智心態的人陸續增多,但“崇洋”依然是東方文化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通病。相當一部分來自圈內的聲音紛紛指出,自現代主義以后,整個亞洲對西洋文化的吸收快,尤其中國與日韓對“鍍金”的理念非常感冒。當然,人都有虛榮心,想提升名氣無可厚非。但在文化圈,往往很多人認為一旦走出去,履歷上就多了一筆,借此能拿到文化不對稱、信息不對稱的地方去“忽悠”,這種失衡的心態未免令人感覺“陰暗”。
更何況,藝術家、經營機構,都是市場鏈條運轉上不可或缺的環節。文化輸出本是好事,一旦浮躁、逐利的心態形成惡性循環,自娛自樂究竟是進步還是倒退,需要好好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