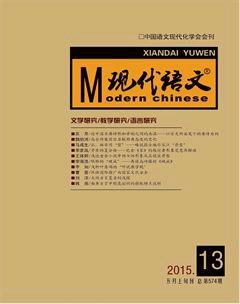《文心雕龍》中王粲論的不足
姚喜慧
摘 要: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王粲的作品、風格與品德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分析與評述,這是文學史上最早的關于王粲全面的評述,其中有褒有貶,且褒多于貶,可知劉勰對王粲總體藝術成就的認同及肯定。但劉勰很多的評述或止步于前人或脫離文本,趨于片面、主觀。
關鍵詞:劉勰 《文心雕龍》 王粲
王粲是漢魏之際重要的文學家,為建安七子之首,是建安風骨的開拓者之一。王粲的詩、賦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受到了眾多文學批評家的關注,他們對其詩賦作品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評論。然而,對王粲及其文學作品進行較為全面系統的評論,最早還是出現在《文心雕龍》中。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論及王粲的地方共計11處,其中有贊揚,有批評,這些贊揚與批評一方面全面地涵攝了王粲在文學創作中的各方面特點,具有建樹性。但另一方面劉勰很多的評述或割裂聯系或脫離文本,趨于片面、主觀。
一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干。”[1]這兩處分別在建安時期五言詩的內容和對四言詩及五言詩的總評中提及了王粲詩歌藝術成就。從現存王粲的詩歌作品上看,其詩歌題材完備,贈答、詠史、宴飲、戰爭等內容豐富,有《贈蔡子篤一首》《詠史詩》《公?詩》《七哀詩》《從軍詩五首》等。劉勰所提到的“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內容在王粲的詩歌中一應俱全。謝靈運在《擬魏太子鄴中集·王粲詩序》中說他:“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2]正是這種慷慨悲傷的感情積郁在內心,表而出之,因而其詩便呈現出“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藝術形態。《七哀詩》便是這其中膾炙人口的一首,“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3]感情樸質真誠,將內心對民生民瘼的關懷以及對前途的憂慮,簡單又真摯地躍然于紙上。這是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很好地踐行。寫景則不尚雕飾,一片自然,《雜詩一首》中“日暮游西園,異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王粲將西園之景以“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之態,用寥寥數筆平鋪于眼前。
雖說劉勰對王粲詩歌“兼善”地位認識不失偏頗,可卻忽視了王粲詩歌對李陵詩歌的學習與繼承,但其他的評論家們,如鐘嶸就發現了這個問題。鐘嶸在《詩品》中將王粲列為上品:“其源出于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余。”[4]可見鐘嶸對王粲詩歌成就及地位的肯定,并穿過表象認識到了王粲詩歌與李陵詩歌之間的共通性。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論述其五言詩“若其述歡宴,愍亂離,敦友朋,篤匹偶。雖篇題雜沓而同以蘇李古詩為原,文彩繽紛,而不能離閭里歌謠之質,故其稱景物則不尚雕鏤,敘胸情則唯求誠懇。而又緣以雅詞,振其響音,斯所以兼籠前美,做范后來者也。”[5]黃侃推本溯源,也同樣找到了王粲詩歌和李陵詩歌的互文性。可見,王粲的詩歌既是在“源出于李陵”基礎上不加雕飾地寫景與誠懇真實地抒情,故而才能在古詩中達到“兼善”的藝術境界。
劉勰在《明詩》中以縱向這一單方向軸線對詩歌的發展脈絡進行了梳理,從堯舜至齊梁,每個時代都具有獨特的色彩,可劉勰卻將每個時代看作斷層,割裂了它與其前、其后時代的聯系。如建安慷慨多氣的藝術特性,是離不開對漢代詩歌直而不野的繼承。同樣,王粲也是離不開對前代詩歌優良傳統的繼承與學習。
二
《詮賦》篇中在列舉出“辭賦之英杰”的漢賦十大家之后,也同樣舉出了魏晉時期的八位賦作名家,王粲就是這其中的第一人“及仲宣靡密,發篇必遒……亦魏晉之賦首也。”劉勰以“魏晉之賦首”冠于王粲,可見其對王粲賦作的肯定與贊揚。
王粲的《登樓賦》是最為人所熟知的,其中“遭紛濁而遷逝兮,漫逾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遭紛亂的時間之久讓作者想到歸去,故而登高憑欄,可坎坷路途與逶迤長河的眼前之景,讓作者禁不住感慨涕流。此段文辭縝密,以“聊暇日以銷憂”為主題,將心中所思與眼中之景細致無漏地聯系起來并展露于文本之上。“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嘆音。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于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此段用到孔子、鐘儀、莊舄、匏瓜徒懸、井渫莫食等典故,增加了語言的意蘊,顯示出作者筆力的遒勁。《思友賦》中“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游目于林中,睹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跡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漭,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逶迤,時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登城高觀,游目林中,見故地卻未見故人,鳥獸愁鳴,野草羅生,此景此情在心中跌宕起伏,“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這也正是《體性》篇中最為推崇的“雅麗黼黻”。可見縝密的情思與遒勁的筆力是王粲賦作的特色,而此種特色正是劉勰最為肯認的。故而,劉勰贊嘆王粲等人為魏晉時期的一流辭賦家。
但是王粲有很多賦卻是沿著濃麗繁蕪的套路走的,如《神女賦》中描寫神女的美貌“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發似玄鑒,鬢類削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朱顏熙曜,曄若春華。口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輔奇葩。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曄。襲羅綺之黼衣,曳縟繡之華裳”,這些外貌和衣飾的描寫占據了全文大半的篇幅,卻只是些淺陋的美詞堆砌,并沒有深層次的內涵,而且這其中還含有大量模仿的痕跡,最后點出主題“彼佳人之難遇,真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意而自絕”,可這個主題幾乎是與前文脫節的。無獨有偶,宋·王楙《野客叢書》卷十六“相如大人賦”中說“自宋玉《好色賦》,相如擬之為《美人賦》,蔡邕又儗之為《協和賦》,曹植為《靜思賦》,陳琳為《止欲賦》,王粲為《閑邪賦》,應瑒為《正情賦》,張華為《永華賦》,江淹為《麗色賦》,沈約為《麗人賦》,轉轉規仿,以至于今。”[6]清晰地指出了王粲的《閑邪賦》對宋玉等人賦作的模仿。再像《槐賦》:“豐茂葉之幽藹,履中夏而敷榮。即立本與殿省,植根抵其弘深。鳥明棲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襟。”這篇《槐賦》,不過贊美宮中的一棵槐樹,枝榮葉茂,植根深固,也不能和《登樓賦》相比。[7]這也是《文選》只選了王粲《登樓賦》的原因。可見王粲的部分賦作是劉勰所批判的“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類的典型,而劉勰并沒有全面地審視王粲的賦作,只是從他的主要風格和主要作品著手,所作的評論難免陷入片面。
三
《雜文》中評價王粲“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仲宣《七釋》,致辨于事理……”劉勰將王粲的《七釋》放在較高的地位上。《七釋》抓住了“仕與隱”這一主題,并反復以潛虛丈人與文藉大夫的議論來表現抱志之士的價值與生存意義。“于是四海之內,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聲暨海外,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逸跡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賤是恥。”正如《小雅·白駒》云:“慎爾優游,勉爾遁思。”[8]思考“道”和游四方是儒家士大夫們一直以來勤政愛民的表現。王粲利用儒家的倫理道德批判了道家的隱逸超脫,并宣揚天下大道的無上崇高。這種精密的邏輯與說理正印證了劉勰的“致辨于事理”。
但是《七釋》也同大多數的“七體”一樣,雖然義理精辟,可文辭駁雜。在勸一諷百的模式下,大肆地談論田獵、美食、音樂、奇服等文中所批判對象的美好,這種迷惑人心的聲色描寫,是一種泛濫的表現,可最后作者往往都能走上正路。然而,這種諷諫卻也失去了本初的意義,還是不能使讀者扭轉對那些事物的喜愛。尤其是文中對田獵盛況的描寫:“乃致眾庶,大獵中原。植旌拊表,班授行曲。組網連置,彌山跨谷。弦不虛控,矢不徒注。僵禽連積,隕鳥若雨。”這種激蕩人心的文字描寫,在炫耀作者文筆的努力之下,并沒有與主題相關的太多深意。可劉勰卻并未將王粲列入“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余家。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皙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髓,艷詞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云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之類。劉勰以時間為系統的編排方式,抹殺了一些好的作品或者混淆了一些層次不同的作品,可見,這種以時間來分割作品藝術成果的方法并不科學。
綜合看來,劉勰是對王粲全面評述的第一人。他對于王粲的評論及觀點,幾乎涵蓋了王粲文學創作的方方面面,雖然是零星分散在各篇之中,可歸結起來仍是比較系統全面的作家評論。尤其是贊揚肯定的部分,這對王粲文學史地位的建構意義深遠。不過劉勰關注的多是王粲前期的創作,并且也未對王粲作品的藝術淵源進行探討,雖然大部分準確全面,但也有一部分閾限于淺顯的表面,而有偏頗之意與浮泛之失。
注釋:
[1]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以下《文心雕龍》原文皆據此。
[2][唐]李善注,[梁]蕭統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0卷。
[3]俞紹初點校,王粲著:《王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以下王粲作品原文皆據此。
[4]呂德申:《鐘嶸<詩品>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頁。
[5]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36頁。
[6]王文錦點校,[宋]王楙:《野客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卷十六。
[7]周振甫:《論王粲詩賦為建安七子之首》,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4期。
[8]梁錫鋒注:《詩經》,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