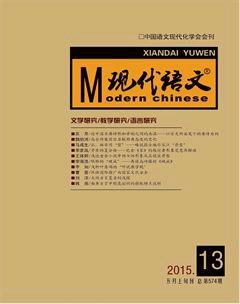艾麗絲·門羅小說集《逃離》中女性形象分析
董星
摘 要:加拿大女作家艾麗絲·門羅于20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代表作小說集《逃離》引起讀者的廣泛關注。逃離,或許是舊的結束,或許是新的開始。小說集以女性視角講述了多個主人公企圖逃離生活、逃離現實的故事。探析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為何逃離,又為何歸來,以此解讀門羅筆下女性的特有魅力,并在她們身上尋找門羅的影子。
關鍵詞:艾麗絲·門羅 逃離 女性
艾麗絲·門羅1931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溫格姆鎮,少女時代即開始寫小說,上大學時,課余做女招待、煙葉采摘工和圖書館員。長期居住于荒僻寧靜之地,使門羅逐漸形成以城郊小鎮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為主題的寫作風格,筆觸細膩深刻。故事人物和現實人物并無二致,他們或多或少也帶著門羅自身的影子。1986年門羅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并獲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后來共創作了14部作品并多次獲獎,作品同時被翻譯成13種文字傳遍全球,受到讀者與媒體的高度評價。2013年10月10日,艾麗絲·門羅獲得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給出的頒獎詞是“當代短篇文學小說大師”。
短篇小說集《逃離》是門羅的代表作,由八個短篇小說組成,以逃離為主線講述了不同年齡階段、不同生活背景的女性內心的迷惘、惆悵,并紛紛想要逃離現有生活的故事。門羅的小說世界是非常純粹的女性世界,她通過非常純粹的女性視角來觀察世界,描述世界[1]。她們看似生活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里,卻在精神世界中有著某種程度的契合,具體分析如下。
一、門羅筆下女性形象的特征
(一)獨立勇敢
門羅并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作家,在1987年的一次采訪中,門羅說到:“當我寫《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的時候,我并不認為自己正在寫一本女性主義的書,我當時僅僅想到的是我要寫一些關于年輕少女的性別經驗的東西,而這些通常會表現在年輕男孩的身上,此后,我只是在書寫女性以及她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掙扎,直到現在,我也只是有意識地對女性的生活方式感興趣,類似于男人和女人在中年的生活狀態等等。”[2]雖說她自己并不想被貼上女性主義的標簽,但是從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故事中的女性追求獨立、渴望自我價值實現的愿望。她們大多有自己的工作和學業,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人生。在《機緣》中,朱麗葉才二十一歲,卻已經獲得古典文學的學士與碩士學位,并一直想要改變別人眼中她只會讀書的形象;在《逃離》中,卡拉為了追求自己的愛情,十八歲便離家出走,逃脫父母;在《激情》中,格雷斯在旅館里當女招待,自己賺錢養活自己,并想把義務教育免費提供的東西全都學到手,她討厭被寵壞的富家小姐,她們什么負擔都沒有,只會撒嬌發嗲、索錢要物。
總之,她們的生活不依附于任何人,包括父母和丈夫,她們向往的是獨立、自由,是實現心中所想的不懈追求,也因為如此,才引發了一次次的逃離,一次次沖破現實牢籠的沖動。
(二)平凡與特別
門羅筆下的女性多為生活在普通小鎮的少女或是婦女,她們經歷著陰晴圓缺的人生,但平凡并不是她們唯一的主旋律,在她們的身上,亦散發著與眾不同的獨特氣質。在《逃離》中,西爾維婭眼里的卡拉與她所教的學生毫無共同之處,她認為卡拉聰明可又不是聰明過了頭,她是天生的運動員卻不計較名次,樂樂呵呵卻不喧鬧煩人,連快活都是快活得自自然然的。可是當卡拉在西爾維婭家里放聲大哭訴苦時,她無法不感覺卡拉很普通。在《機緣》中,朱麗葉是別人眼中聰明的孩子,也是個只會讀書、古怪和孤獨的孩子,可是在她的內心也有想與人交往的渴望,有過“搭伙兒聊聊”這樣的念頭。正如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也沒有任何兩個人是一模一樣的,我們都在共性與特性的交織中塑造著自己的形象。看似平凡的女性,她們各有自己的魅力和性格,而我們正在羨慕和向往著的某些人,也有自己不堪和落魄的一面。門羅的故事中的女性正是在這種平凡與特別的交織中更顯迷人。
(三)逃不出家庭生活的困擾
盡管門羅筆下的女性有個性有追求,但仿佛是女人的天性使然,她們的生活終究逃不過丈夫、孩子和家庭。《逃離》中的卡拉在逃走的時候還在惦記家里的生意;《沉寂》中的佩內洛普,長大成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逃離相依為命的母親,可是多年過后她依然是過著和母親類似的普通生活。這似乎也與門羅自身的經歷有關,1951年,年僅二十歲的她離開大學與詹姆斯·門羅結婚,移居到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溫哥華。她的女兒 Sheila,Catherine和Jenny相繼出生于1953年、1955年和1957年,Catherine出生后15個小時便不幸夭折。1966年,他們的女兒Andrea出生。1972年,艾麗斯·門羅與詹姆斯·門羅離婚。艾麗斯回到安大略,成為西安大略大學的住校作家。1976年,艾麗斯與地理學者Gerald Fremlin結婚,夫婦二人搬到安大略省克林頓鎮外的一個農場,后來又從農場搬到克林頓鎮,從那以后一直住在那里。門羅后期的創作大多是在爐邊和女兒的啼哭聲中完成的。也許是家庭生活在門羅心中占據著不可撼動的地位,這其中的幸福、痛苦、煩惱都是她創作永不枯竭的源泉。
二、逃離的意義
(一)逃不出時間的流逝
門羅像契訶夫一樣,對時間這個主題十分著迷。時間的強大在于永不停止,永不回頭。它留下的痕跡是任何人都無法抹去的。“可是今天,這個姑娘卻與西爾維婭記憶中的卡拉完全不一樣了,根本不是在她游歷希臘時一直伴隨著她的那個安詳、聰慧的精靈,那個無憂無慮、慷慨大度的年輕人了。”[3]這是《逃離》中,從西爾維婭眼中透視到的卡拉的變化。生活的瑣碎已經將那個純凈美好、勇于追求愛情的年輕姑娘變成了另一般模樣,她不再深愛那個她為之逃離父母的男人,而是用“太可怕了”“我再也受不了了”這樣的詞語來形容他。這也是無數平凡夫妻所面臨的問題。愛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終成眷屬的厭倦,要么苦于未能終成眷屬的悲哀[4]。門羅筆下的女性正經歷著這樣的困惑,家庭生活從幸福走向不幸,丈夫的冷暴力與斤斤計較讓她難以承受。她們在無奈的掙扎、無望的逃離中,消磨時間和生活。
(二)逃不出自己內心的牢籠
在這些故事中,女性們逃離家庭,逃離兩性,逃離自我。如《沉寂》中的佩內洛普逃離母親,《激情》中的格雷斯逃離未婚夫與其哥哥獨處一個下午,《機緣》中的朱麗葉,雖然她也喜歡那個熱愛知識和文化的自己,但內心深處卻更想要逃離,甚至不惜與僅一面之緣的導師外甥在草地上草草結束自己的童貞。小說里有不少精神恍惚的女人,在某種程度上,她們逃離了自己不再留戀的那個“清醒正常”的自我[5]。盡管如此,她們依然逃不出生活這個巨大的網,心是困倦的,逃到哪里都是徒勞。在卡拉失敗的逃離中我們看到,她最終還是離不開那個家,離不開自己的丈夫,終究還是不能舍棄早已習慣的這一切。
“昨天晚上還有前天晚上她都夢見弗洛拉了。在第一個夢里,弗洛拉徑直走到床前,嘴里叼著一只紅蘋果,而在第二個夢里——也就是昨天晚上,它看到卡拉過來,就跑了開去。它一條腿似乎受了傷,但它還是跑開去了。它引導卡拉來到一道鐵絲網柵欄的跟前,也就是某些戰場上用的那一種,接下去它——也就是弗洛拉從那底下鉆過去了,受傷的腳以及整個身子,就像一條白鰻魚似的扭動著身子鉆了過去,然后就不見了。”[3]弗洛拉是卡拉的小山羊,它似乎是卡拉的某種寫照,從一開始的“情竇初開的天真女孩”到后來的“有了能看透一切的智慧”,再到它的走失和卡拉的這個夢,它逃開了卡拉,一條腿卻受了傷。這些預示著無論逃離與否,都會是一種悲劇,都會承受痛苦。
結語
門羅用她深刻犀利的眼光、樸素細膩的文字將女性形象的平凡與偉大展示給讀者,我們體會到的不僅僅是故事,更是人生。沒有起伏的情節,也沒有曲折的經歷,那些最稀松平常的生活場景帶來的是更大的震動。真實是文學最本質的力量。從她的筆下我們看到,逃離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情緒,一成不變的瑣碎使人們的心承受著重復的壓力和困惑,忘了最初的追求與喜悅,于是想要逃離,可是逃離后才發現那只是另一種重復的開始。女性對家庭生活的向往有時候也成為困住自己的牢籠。“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進去了一根致命的針,淺一些呼吸時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當她需要深深吸進去一口氣時,她便能感覺出那根針依然存在。”[3]這根針或許是未能逃脫的遺憾,或許是對另一種生活殘存的希望,它像是潛伏的敵人,時而敲打著人類脆弱的心靈。
注釋:
[1]林玉珍:《艾麗絲·門羅短篇小說的多重主題》,世界文學評論,2006年,第2期。
[2]陶鐵柱譯,[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
[3]艾麗絲·門羅:《逃離》,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4]錢鐘書:《圍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
[5]梁艷:《逃往何處——艾麗絲·門羅的<逃離>中的“逃離”主題探析》,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上旬),2012年,第4期,第1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