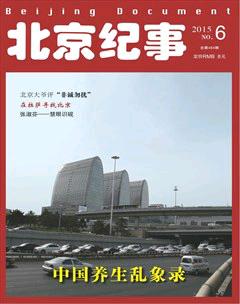看今天兒童,憶我等童年
孟慶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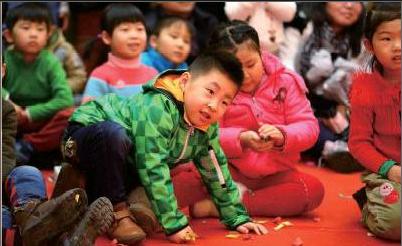

兒童節快到了,看到今天小孩的生活,真是讓人羨慕,孩子們簡直是生活在蜜罐里。許多30后的人在一起說起自己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當時整個國家就窮,又趕上了抗戰時期,在那民不聊生的年代,孩童的生活能好得了嗎?
那時,到了上學年齡,家長們都千方百計地讓孩子穿得好一點。但是饑寒交迫的家長真是力不從心,那個年代沒有獨生子女一說,各家的老二、老三只能撿“剩裝”穿。小孩也能把社會流行語帶到學校,紛紛把自己的衣著說成:“破鞋、破襪子、破軍裝!”孩子們夏天還好湊合,嚴冬實在難熬,真是應了那句話:“十冬臘月的孩子——凍手凍腳的。”多數孩子沒大衣、沒帽子、沒手套、沒圍脖兒,如此著裝怎能不得凍瘡。小學男生流行一種“航空帽”,航空帽雖是皮革制品,但是沒有皮毛和棉絮,只有一層褡褳絨的里兒,嚴寒的季節耳朵照樣長凍瘡。冬天小孩把手揣在袖口里,是普遍的習慣動作。
那個年代的小孩上學、放學基本無人接送,寒假前夕天最短也最冷,一年級小學生也是黑咕隆咚自己走著上學。現在接送孩子上下學現象很普遍,每當小學生上學時那場面太壯觀了,出于安全考慮本無可厚非。現在的普遍現象是小學生都赤手空拳上學,書包、用具一律由“老書童”背著,只有到了校門口,學生才背著書包進課堂。放學時校門口的場面更是壯觀,眾多的“老書童”堵著校門,恭候學生。學生到達校門口,雙方沒有交流,沒有稱呼,學生習慣性地拿下書包,遞給“老書童”,“老書童”心甘情愿地接過來,挎在自己肩上。這些“老書童”還經常深入教室,自覺自愿地替學生做值日。
早先一年級小學生,從開學第一天起就開始輪流做值日(即打掃教室衛生),那個年代從來沒有家長代勞的。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興起一種連體課桌椅,沉極了,不管多沉都是小學生自己克服。當年一年級都有唱游課,班里幾個稍大一點的男生,要從教員休息室把風琴抬進教室,現代小學生沒有這項勞動。上珠算課要有一個學生替老師拿大毛算,體育課如果學墊上運動,學生還得去搬墊子。對于此情此景老師感覺很自然,參與搬東西的同學感覺很自豪。早年的一年級小學生會抬風琴,今天的小學生卻不管背自己的書包。
當年的小學從二年級就開始描紅模字,并且有正式寫字課,不同的寫字課使用不同的文具:大楷筆、小楷筆和墨盒、硯臺,幾種文具輪番配套使用。比如大字課帶墨盒是不行的,必須帶硯臺,寫字課時現研墨。珠算課必須自帶珠算,好在當年對于珠算的規格沒有統一要求。勞作課學生必須自帶刀剪和糨子,全班四五十個學生,幾乎全都是自己打糨子,裝在火柴盒里帶到學校,雖然那年頭文具店也有賣香糊的,但是一般學生是不會花這冤錢的。
玩是小孩的天性,什么年代的孩子也得玩,六十幾年前的小孩玩得很單調,主要受錢的制約。那個年代沒有電子玩具,即便電動玩具也極少。就拿冬天的踢毽來說吧,雖然市場上有賣毽子的,但是小學生基本都是自己炮制毽子。那個年代家家幾乎都有制錢,有雞毛的用雞毛做毽子,毽子踢壞了再重做,只剩一兩根雞毛時也能當玩意兒,玩“雞毛雞毛你看家!”(實際上是使雞毛摩擦生電的反映)。即便手頭沒雞毛,也可以用作廢的大仿紙做毽子。當年毽子的最廣泛的玩法是三六九功。
男孩子在夏天都愛玩蛐蛐,多數小孩玩蛐蛐也是一分錢不花,假期幾個小孩結伴到南下洼子或城根兒逮蛐蛐。幾個小孩中必然要邀請一位有蛐蛐罩子的小朋友參加,兜里裝著幾張32開的廢作業紙,一旦逮著蛐蛐,將作業紙卷成小圓筒,窩死一端,將蛐蛐置入筒內,再窩好另一端。回家后,再將其放入蛐蛐罐中,整個過程分文不花。為了斗蛐蛐,鄰居的小貓可倒霉了,孩子們逮著貓就揪貓胡子,用幾根貓胡子做蛐蛐探子。
彈球兒也是男孩子的玩意兒,當年所有小學均不允許學生在校內玩彈球兒,可能是因為彈球兒有一點賭博的性質。每個小孩都有幾個球中精品——老子兒。彈球一般都在冬天玩,患凍瘡的手根本無力彈球,只能張著大嘴把小手哈熱。
空竹和風箏也是男孩的長項目,新年買個雙輪空竹,玩著玩著摔壞一個輪,就拿這個空竹當單輪的抖,實在不行茶壺蓋兒也能當無聲的空竹抖。買不起風箏的小朋友,都可以自己糊屁簾兒,歷來市場上沒有賣屁簾的,自制的好屁簾可以跟正經八百的風箏一比高低。
那個年代的小孩都會自己琢磨玩意兒,一瓶沃古林眼藥水的橡膠瓶蓋兒也能當玩意兒,男孩們將其摁到腦門上還很得意。街頭撿到一根竹管,用鐵棍兒在其頂端燙一個孔,拿一根筷子纏上布條兒這就是一把水槍。小蔥兒剛剛上市,剪下一寸長的蔥葉兒就能做一個鼻兒。當年玩意兒少,口頭上也虧嘴,拿一根干粉絲在煤爐上一燎,立即成為一根膨化食品。雖說花生是食品,也是小孩的玩意兒,吃花生的過程中許多小孩都把花生當“耳墜”。走街串巷賣吹糖人的,其代表作是“猴兒拉稀”,賣猴拉稀還同時配備一個小勺,這個小勺僅僅比耳挖勺大一些,小孩就用這個小勺款待他的小朋友——每人一勺黑色糖稀,偶爾還會遇到一兩粒芝麻。現在的小孩幾乎個個都有一輛與自己身高相匹配的自行車,六七十年前的小孩都是利用大二八車,掏大梁偷學騎車技藝,如果把車弄壞了定遭體罰。
過去小孩春節或多或少能得點壓歲錢,多數家庭壓歲錢也不讓亂花,甚至于花炮都不許買大的,只許買小鞭兒和耗子屎。“耗子屎”這個詞聽著就不雅,耗子屎屬呲花類,一分錢給好幾個,用香頭兒一焌,在地上冒著火星刺刺亂轉。
女孩子愛玩子兒和跳房子,這兩樣玩意兒都屬于無花銷的玩意兒。子兒的“子兒”分兩種:一種是羊拐,羊拐就是羊的骨關節,比栗子稍大一些,女孩們找到羊拐后,將其刮洗干凈,并分別涂上紅藍墨水。另一種“子兒”是自制的布包,一般女孩會縫制3×3厘米的小布袋,其中裝進米和豆再縫口,當年三年級以上的小女孩都會自己做這些玩意兒。那時男孩、女孩都玩跳房子,跳房子又叫踢排(pǎi),但是男女生風格不同,男生找塊磚頭瓦片就當排踢著玩,女生則會用制錢和算盤珠子,或者用玻璃珠子串成小圓環當排踢。冬季的課間10分鐘許多孩子也都感覺百無聊賴,紛紛在向陽的墻根瞎擠著玩——這項活動定名為“擠狗屎”。
現在的小孩很早就涉獵電子玩具,但是實際動手能力較差。家長對孩子的照顧無微不至,而且各項照顧無限期延長,孩子考高中家長作陪,考大學家長還作陪;孩子報考藝術院校更是雙雙陪同,坐火車、坐飛機、住旅店都得家長陪著,孩子考試時,家長坐在馬路牙子陪著。某人今年32歲,電腦玩得熟練極了,該人最愛吃炸醬面,但不會做炸醬面,這不新鮮。然而,那么大個子居然不會拌面,32歲的人了,每次吃炸醬面都得媽媽給他把面拌好。該大兒童從不在飯館吃炸醬面,因為飯館的服務員不管拌面。這雖然是個別現象,但是聽著新鮮。
鼻兒:北京土語,指豎著可以吹響的管子。
(編輯·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