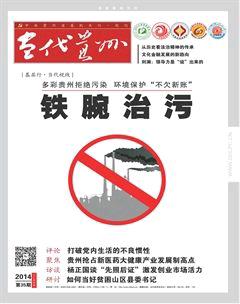周恩來式的愛 (二)
梁衡,本刊顧問,當代作家,著名的新聞理論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論家,人教版中小學教材總顧問,歷任《內蒙古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周恩來人格精神有多方面,其基本點有三:仁愛、犧牲和寬容。
犧牲是一種自愿的付出,有愛才有犧牲。大公無私,為別人犧牲自己,這是周恩來的本性,一種生來具有的基因。陸定一在回憶錄中講了一件令他一生難忘的事。當年陸定一隨周恩來在重慶工作,常乘飛機往返于重慶和延安。一次遇壞天氣,飛機表面結冰下沉。飛行員著急,讓大家把行李全部拋出艙外,并準備跳傘。這時葉挺11歲的小女兒因座位上無傘急得大哭。周恩來就將自己的傘讓給她。他并沒有覺得自己的命比一個孩子還重要。
周恩來規定凡有重要事情,無論他是在盥洗室、辦公室、會議上,還是在睡眠,都要隨時報告。他經常坐在馬桶上批閱要件,因為無時間吃飯,服務員只好把面糊沖在茶杯里送進會議室。已重病在身還要接見外賓、談判、到外地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他不只是為中國人服務,許多外國人也來吃他的唐僧肉。1975年,越南總理到中國來要援助,不給不走,談判從夜里兩點談到天亮。周恩來渾身虛汗,每十分鐘要一次熱毛巾。他絞盡腦汁地工作,砍光青山燒盡材,一生都在毫無保留地消耗自己。人們都記得他晚年坐在沙發上的那張著名的照片,枯瘦、憔悴,手上、臉上滿是老年斑,唯留一縷安祥的目光,真正已油燈耗盡,春蠶到死,蠟炬成灰,鞠躬盡瘁。
除了身累之外還有心累,即精神上的犧牲。中國政治長期形成了一個格局,毛澤東是決策者周恩來是執行者。周恩來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一方面要考慮億萬人的生計問題,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一方面又要顧及毛澤東一人的態度與情緒。民以食為天,老百姓的事辦不好,國家要翻船;決策者翻了臉,國家也要翻船。我們知道周恩來是很喜愛戲劇的,有一次工作人員發現他在紙上無奈地抄錄下兩句戲文:“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暖和參要寒。種田哥哥要落雨,養蠶娘子要晴干。”其實歷代,做官最難是宰相,君要折騰民要安。屈居一人屋檐下,卻憂萬民吃與穿。建國后周恩來就一直處在“相”位,常處于二難境地。要么犧牲大局,要么犧牲毛澤東的權威,這兩樣黨和國家都承受不了。那么,就只有他自己一次次地作出犧牲。“文革”中有一次服務員送水進會議室,竟發現周恩來低頭不語,江青等正輪流發言,開他的批判會。但是,走出會議室后周恩來又照樣連軸轉地工作,盡力解放干部,恢復秩序。 “文革”中周恩來說過一句讓人揪心的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這是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的犧牲。
周恩來的犧牲精神還有一個更嚴酷之處,我把它稱之為“超犧牲”。他有“十條家規”,除了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樣要求家屬、部下和身邊的人。這和現在的官場上為家屬謀利、提拔重用親信,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中國古代最忌諱但又最難根治的就是外戚政治與朋黨政治。周恩來深知這一點,他矯枉過正,勿使有一點灰塵,不留下一點把柄。這樣,親屬部下也要跟著做出了犧牲,超常規的犧牲。夫榮妻貴是千百年來官場的鐵定律。但是在周恩來這里有另一條定律:只要他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進國務院。周恩來住的西花廳年久失修,特別是地板潮濕,對他的身體很不利。一次乘他外出,建國初老秘書何謙主持將房間簡單裝修了一下。他回來后大怒,這個可憐的秘書被調出西花廳,到最后也沒有提撥。如果是現在,正好相反。現在官場腐敗,有一個詞叫“利益集團”,而周恩來的身邊卻有一個甘為國事犧牲的“犧牲集團”。當然,當年這樣嚴格的不只是周恩來一人,這在中共第一代領袖中很普遍,毛澤東就主動不拿最高的一級工資,否則共產黨也不可能得天下。不過周恩來做得更徹底一些。
對比現在存在的官風不正、公權私用,不貪不官的現象,周這種殘酷的犧牲精神叫后人一想起就心中隱隱作痛。人心是肉長的,誰無感恩之心?當年總理去世時我正在外地一城市,從郊外入城忽見廣場懸空垂下一黑色條幅上書“悼念人民的好總理”,滿城黑紗,萬人慟哭。而在北京,淚水洗面萬巷空,十里長街送總理成了共和國史上最悲壯的一頁。人們恨不能寧以我身換總理,80高齡的胡厥文老人寫詩道:“庸才我不死,俊杰爾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為國傷。”火化之日,火化工為使總理能平靜入爐,竟以身試尸,躺在尸床上幾次進出焚化爐,仔細體會進爐的感覺,調試尸床的速度和節奏。 “總理愛人民,人民愛總理”,這絕不是簡單的領袖與公民的關系,而是人心與人性的共鳴。(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