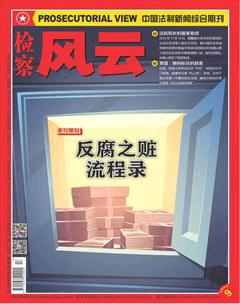司法改革雖難卻可期
周建軍
所謂“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不過是按圖索駿,知易行難。相形之下,中國的司法改革知難,行亦難,地地道道的“硬骨頭”。如今,改革已向法治國家、權力制衡等縱深方向發展,僅有如臨深淵的態度還不夠,最難啃的骨頭甚至需要主政者具有思接千載的心智、壯士斷腕的勇氣。
巡回法庭:毫末用功成一水
巡回法庭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司法依法獨立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幾年之前,憲法適用、司法獨立還是學術表達的禁區。有一個著名的憲法案例——齊玉苓受教育權被侵犯的案件:1999年1月,山東鄒城的齊玉苓以侵害姓名權和受教育權為由,將陳曉琪等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并賠償經濟損失。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此作出《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認定“陳曉琪等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規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并造成了具體的損害后果,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同年8月24日,山東高院根據《批復》作出二審判決:陳曉琪停止對齊玉苓姓名權的侵害;齊玉苓因受教育權被侵犯而獲得經濟損失賠償48045元及精神損害賠償5萬元。由于《批復》破天荒地在相關侵權依據中直接引用了《憲法》的規定,時任最高院副院長的黃松有在《人民法院報》撰文指出:此案“開創了法院保護公民依照憲法規定享有的基本權利之先河”,“創造了憲法司法化的先例”。不久,黃松有“出事”,《批復》也被廢除了。據說,《批復》被廢除與黃松有“出事”之間并沒有太多的聯系。前者之所以被廢除,主要在于憲法適用抑或司法獨立將會影響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
2012年以后,忽如一夜春風來,不僅關于憲法適用、司法獨立的研究、表述紛紛解禁,飽受詬病的勞教制度被廢止,針對被指具有侵犯人權嫌疑的計劃生育政策、戶籍制度的改革也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眾所周知,勞教制度、計劃生育政策長期具有某種“神圣”性質。在過去,誰要是批評得太狠,便會因此遭受不利。因此,勞教制度廢除、計劃生育制度的放松抑或改革表明執政黨推行法治國家建設和相關改革工作的決心相當之大。
當然,所有這些也為以“審判獨立”為宗旨的改革工作做出了背書。在司法改革各類措施中,巡回法庭制度的推進具有標志性的地位。根據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最高院設立巡回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法院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說到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是要根據黨中央的統一部署,加強法院的獨立地位,從根本上改變司法權力嚴重依附于地方黨委和行政的問題,部分實現審判獨立抑或司法依法獨立的要求,逐步改善司法嚴重不公的局面。
執政黨推進司法改革的魄力甚至超過了多數學者的期望。從旁觀者的角度來講,難免喜出望外。
在司法改革中,尤其巡回法庭的建立,執政黨將改革的矛頭指向了自己,率先觸及地方權力,頗有些鳳凰經火的意氣。從本質上說,司法以公正為根,獨立以制度為本,司法依法獨立的根本在于公正的判決和制衡其他國家權力的司法制度。由此觀之,巡回法庭的建立雖則毫末用功,卻也成了一水。
審判獨立制度:水源山脈固難尋
栽樹判決算得上司法改革的陳年往事。2006年7月,時年58歲的溫州老太季某上墳失火,由于沒有經濟賠償能力,溫州鹿城區人民法院一審判處季某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同時在兩年內植樹13620株。在司法不過是階級統治工具的年代,此等判決無異于石破天驚,因此被冠以“栽樹判決”的美名。眾所周知,2006年前后,時任最高人民法院肖揚院長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為主旨推行以刑事和解、程序簡易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等司法試驗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運動。除栽樹判決外,其他試驗事項多在2012年的《刑事訴訟法》中修成正果。現在看起來,即便號稱司法改革“硬骨頭”的審判獨立制度(包括相關的財政、人事保障制度),在當時也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方案。此情此景,正好回應了方干“水源山脈固難尋”的詩詞老話。
究其本質,栽樹判決屬于從寬政策下的“非刑罰處罰措施”的制度創新。雖是創新,但栽樹判決屬于《刑法》第36、37條規定的賠償經濟損失抑或賠償損失的范疇,符合罪刑法定的規定。與之相反,在2012年修訂《刑事訴訟法》之前,全國法院系統推行的很多改革措施,如刑事和解、程序簡易化的改革試驗,并沒有法律依據。說白了,就是改革抑或政策沖破法制底線的問題。問題是,改革究竟能不能沖破法制底線?通常情況下,基于法的安定性和權威性,改革應在法治的軌道內進行。這也是法治精神的應有之義。然而,2006年前后的中國,基于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的脫節,出現了旺盛的制度需求與立法極度保守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妨稱之為變革社會情形下的制度短缺問題。從制度經濟的角度來講,制度短缺的問題愈發嚴重,增加制度供給的必要性隨之增加。因此,在立法嚴重受阻的情況下,基于司法(正義)的本義,司法機關應該承擔起將制度需求(實質理性)與判決合法(形式理性)結合起來,增加有效法律制度供給的責任。當然,這是要求極高的司法藝術。為此,德國法哲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專門提出了著名的“拉德布魯赫公式”——凡是正義根本不被承認的地方,法律不僅僅是不正確的法,甚至根本就缺乏法的性質。根據這個公式,不僅“法律的不法”是客觀存在的,有時還會非常嚴重;此時,通過“非法律的法”(拉氏稱之為“超法律的法”)增加法律供給的合理性也才凸顯出來。
有人說,這里判決栽樹,那里判決種草……更重要的是,司法權力的地位因此可能獲得難以料及的提升。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判決栽樹、種草,甚至看門、做保潔,為有效恢復被害法益而要求犯罪人承擔的這些非刑罰處罰措施,不僅于法有據,而且改善了我國向來重刑有余、輕刑不足(非刑罰處罰措施尤其不足)的刑罰結構。于公于私,何樂而不為?至于司法權力的提升,在積貧積弱的司法背景下,何必杞人憂天。然而,栽樹判決還是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滿,被按了暫停。隨之被暫停的,還有前文提到的憲法適用問題。
司法權力:有無明月在潭心
司法改革有難度。依現在的情形,不過爬山爬到半山腰的樣子。古人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可是,中國的司法改革,知難、行亦難。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更習慣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式。好比孩提時代,鄉下的孩子光著屁股學游泳,不得已抱著石頭慢慢熟悉水性。但如今的中國社會,早就不屬于光著腳走路抑或光著腚游泳的孩提時代,再堅持摸著石頭過河就有點貽笑大方了。
從頂層設計的層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等文件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現代國家的治理體系中,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根據法理學的研究,這句話至少包含以下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法律是國王,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第二,沒有任何其他一種治理方式可以與法治相提并論。在法治的框架下,道德、紀律、習慣、鄉規民約等治理方式都居于重要但不是最高的地位,與法律一起共同組成社會治理的堤壩體系。因此,從頂層設計的層面來講,司法改革的確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因噎廢食、半途而廢,也不能囫圇吞棗、不講原則。前者不必多言,不能囫圇吞棗、不講原則主要是指司法改革務必要遵循法治國家的基本原理,決不能違背司法務必依法獨立的理性和規律來開展司法改革。
以“就地審判,不拘形式,深入調查研究,聯系群眾,解決問題”為核心內容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只是革命戰爭時期邊區政權的臨時措施。在缺乏基本司法條件的年代,馬錫五審判方式不失為踐行群眾路線,滿足民眾的公平正義需求的好方法。但是,作為邊區政府任命的隴東專署專員(行政負責人)兼任邊區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有違司法職業的專業化。“就地審批、不拘形式”的審判方式,明顯不符合司法程序、儀式的基本要求。深入調查研究,甚至達到不計成本的地步,也只有行政一把手兼任法官的時候才有可能做到。更有意思的是:馬錫五的時代,制定法極少,無法可依,大量采用調解的方式結案也就罷了。現在呢,立法汗牛充棟,還提倡調解結案,豈非南轅北轍?經驗表明,在事實清楚、法律明確的情況下,當判則判,否則還會影響到司法的權威和形象。對我們的司法改革來說,馬錫五審判方式并非毫無意義——司法不依法獨立,馬錫五都要去田間地頭,法官、法袍、法槌也不必再要了。
編輯: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