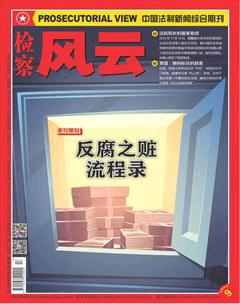瑤族的“度戒”鼓樂
申波
作為瑤族重要的民俗活動之一,“度戒”儀式是瑤族全體成年男性標志性的“集體記憶”
瑤族是一個歷史悠久、支系眾多、人口分布較廣的民族,他們主要分布在中國廣大的南方地區和泰國、緬甸、老撾和越南等國家。云南各地的瑤族大約在200多年前由兩廣境內遷徙而來。
作為瑤族重要的民俗活動之一,“度戒”儀式是瑤族全體成年男性標志性的“集體記憶”過程疊加了諸多文化意義,是瑤族的宗教意識、社會倫理、生活習俗相互層疊和交織的濃縮。瑤語稱“度戒”為“在”,它是所有瑤族男子人生經歷中最為隆重的一刻,是他們在鼓樂的陪伴下從少年走向成人重要節點上必須完成的“成人禮”……
“群體性”儀式的首要特征。作為人生成長歷程的重要環節,度戒儀式通常要邀請全寨的老少共同見證。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一種類型化與程式化的設計,戒師的各式宣諭,就通過度戒鼓的聲音傳遞到人們的心靈深處并通過儀式予以鞏固。
為集中描述“度戒鼓舞”的特征,僅以居住在云南河口一帶瑤族藍靛支系中流傳的“度戒鼓舞”進行描述。
“度戒鼓舞”是瑤族“度戒”式中系列舞蹈套路的總稱。從民族信仰的整體立場來考察,藍靛瑤族雖然以信仰盤匏文化為主體,始終把“盤王節”視為族群重要的儀式記憶。鼓在瑤族民眾的心目中就是盤匏的化身,敲鼓即意味著驚動諸神。鼓聲對“局內人”而言具有強烈的威儀感,在這一時空坐標里,儀式中的鼓樂對所有的參與者具有“浸入心靈” 的力量,音樂現象依托信仰儀式運作生成。在度戒儀式上, 戒師的法器就是法鼓(俗稱“契子鼓”)以及鑼、鈸三大必備“神器”。它們發出的聲音主要是用于為戒師吟誦的經腔“伴奏”、為戒師肢體的動態提供情緒的渲染和為儀式場景營造氛圍的烘托,以此強化儀式對人們心靈產生的震撼和威懾力。
契子鼓又名盤鼓,直徑50 厘米、厚30 厘米。人們將一段圓木鑿空,兩面蒙以黃牛皮,再用牛皮繩將雙鼓面連綴并用木契子從鼓的邊緣切入,由此將鼓面卡緊,一般以單鼓槌擊之。需要說明的是,云南的瑤族沒有長鼓。據老人們說,來到云南的瑤族由于常年的遷徙生活,長鼓不便攜帶,因此長鼓就淡出了人們的生活。
在度戒儀式上,第一個環節是燒香,然后由戒師進行公戒,這時所有參與儀式的村民會情不自禁地唱著《吟誦調》, 其唱詞主要根據受戒者的背景條件即興展開。隨后,若是戒師吟唱經文,他會用左手扶住法鼓,右手握槌邊敲邊唱,其助手在一旁敲小馬鑼,他們敲擊的手法都非常簡單。在這里,藝術形式雖然有著追求藝術美的韻味, 但這并不是他們舉行儀式的目的, 其核心重在表達經文的宗教內涵,以實現以度戒儀式“勵其心志”而育人的目的。這時,敲擊的節奏較快采用均分鼓點,通過鼓聲產生一種象征意義以鞏固儀式的內涵。待經文吟唱完畢,其儀式套路會轉向鼓舞的環節,這構成藍靛瑤族度戒儀式中帶有“表演”性質的重要組成部分。
屆時,儀式將由一位主事的戒師領著受戒的少年共同跳起《戒師動鼓雙人舞》,這時戒師懷抱法鼓,邊跳邊敲,另有兩位場外戒師隨著場內戒師肢體的變化分別擊鈸、敲鑼為之伴奏。在場上戒師的引導下,整個度戒鼓舞由“起師入宅”開始,經“動鼓開經”“招龍運水”“請圣迎神”“川光”“度師樂兒”“度道樂花”“安龍接祖”“燒香拜師”“壇堂受戒”等基本套路構成儀式的全過程,而這一過程都在鼓點營造的聲音環境中進行。
作為一種出于生存需要的行為方式,“文化傳遞”是整個“成年禮”的主線與核心,表達這一核心內容的途徑就是在儀式中所做的種種“執事”,體現出“隱層”意識向“顯層”意識的轉化。因此,在這種“傳幫帶”機制的模塑下,鄉村固有的文化傳統就在少年鼓之舞之的習得中獲得了強化。鼓語通過固定的節奏成為在儀式中溝通人際、人神的媒介,即在世俗生活中實現溝通人際,在精神信仰中實現溝通人神,最終達到沿襲傳統規范以完成族群成員心理和生理教化的目的。
在鼓語的陪伴下,少年由此完成了社會角色的轉換,意味著由此成為了一個必須承擔社會責任、有社會地位的人。作為瑤族藍靛支系人生禮儀的重要一環,“度戒鼓樂”的存在,使其促成了儀式的意義轉換,實現了族群現實價值與理想價值的相互滲透,其春雨潤無聲的“寓教于樂”作用,是我們對度戒儀式最貼切的識讀。度戒鼓樂指導和規范瑤族生存、生活的世俗功利目的是在其審美愉悅價值之上的。可以說,鼓樂在這里已經超越了“音樂”固有的內涵和外延,而是為文化持有者搭建了一個完成文化行為、體驗人生感悟的場域。
(本文摘自《鼓語通神——云南少數民族鼓樂文化研究》,人民音樂出版社,2015年1月。該書在京東“人民音樂出版社(上海)有限公司旗艦店”有售。)
編輯: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