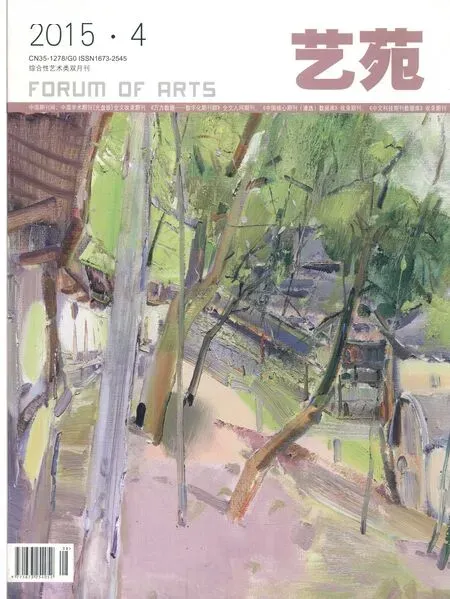鏡像時代的生命沉思——再論《一一》的主題與電影語言風(fēng)格
文‖劉金平
鏡像時代的生命沉思
——再論《一一》的主題與電影語言風(fēng)格
文‖劉金平
“ 昏迷/死亡”事件刺穿了世紀末華麗的富足神話,使《一一》反轉(zhuǎn)進入一個“由死及生”、追問生命意義的敘事進程。而在鏡頭語言上,楊德昌一方面運用豐富的都會建筑元素展開對人性異化境況的暴露;更重要的是其創(chuàng)造性地對鏡像時代的高度自覺與批判性思考,正是借由對鏡像的反身指涉,他不僅實現(xiàn)了對電影本身的解碼,同時完成了對新千年虛實邊界模糊的科技時代的重新編碼。
《 一一》;由死及生;鏡像時代
在一次采訪中,吳念真曾用“看山依然是山”來形容《一一》(2000)時期的楊德昌,在經(jīng)歷了《恐怖分子》(1986)、《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的悲觀和《獨立時代》(1994)、《麻將》(1996)的憤怒之后,楊德昌在自己知天命的年紀迎來了對生命的寬柔理解,時隔四年再次出手給世界留下了一份“平淡而山高水深”的感動。
一、由死及生
大概是要表達的東西實在太過豐富,從《恐怖分子》開始,楊德昌便醉心于人物群像的錯落式敘事。《一一》也是如此,不過不同于之前影片中都市各階層人物因種種偶然性的交遇而旋生悲喜歌哭,這一次楊德昌將視點落在了“家庭”,他要拍的是生命的各個階段,是生老病死,而家庭中“所有的年齡都有一個代表,所有的人又都是密切相關(guān)的,他們的經(jīng)驗可以投射都彼此身上”[1]。
影片描寫的是一個典型的臺北中產(chǎn)階級家庭,父親NJ(簡南俊)是一家電腦公司的合伙人,母親敏敏是職場女強人,他們跟8歲的兒子洋洋、念高中的女兒婷婷以及孩子們的外婆住在一起。故事開始于小舅子阿弟的婚禮,陽光明媚、草木葳蕤,高調(diào)光、優(yōu)美舒緩的背景音樂以及全家福的全景鏡頭都展現(xiàn)著家庭生活的和諧和意趣盎然。然而,經(jīng)典敘事的原則是問題的產(chǎn)生與解決,唯此情節(jié)才能得以不斷推進。風(fēng)波似乎首先來自于阿弟的情人云云突然出現(xiàn)在婚禮上的攪場,不過影片在此著墨并不太多,因此真正的沖突來自于攪場后心緒難平的婆婆提前回到家中,而后卻因替婷婷倒垃圾而暈倒在路旁,此后她始終昏迷不醒——于此,“昏迷∕死亡”成為一個象征性因素貫穿、籠罩著影片始終(最終以婆婆的葬禮結(jié)束),它的驟然登臨,讓所有人的困境都朝向鏡頭敞開,也讓影片的敘事成為一個由死及生的過程。一貫雷厲風(fēng)行的敏敏沖著NJ的哭訴可謂是這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鏡頭段落。家里人輪流向昏迷的婆婆說話,但敏敏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每天跟母親講的東西都是一樣的,生活的貧瘠和僵硬令其震驚,她說:“我怎么只有這么少……我覺得我好像白活了,我每天像個傻子一樣……我每天在干什么?”在這里,“昏迷∕死亡”完成了一個反轉(zhuǎn)動作,刀鋒般刺穿了世紀末華麗的富足神話——淚流滿面之后,現(xiàn)身的是對“意義”的追問。
然而NJ也無法給出答案,事實上影片中每個人仿佛都有著一種宿命般的失敗經(jīng)驗:重視友情、深具遠見的NJ在金元原則至上的淺薄商業(yè)環(huán)境中屢屢受到朋友們擺布,卻只能獨自憤懣;婷婷因?qū)ζ牌诺睦⒕味找故撸谟亚槭軅那闆r下以為遇見愛情卻最終遭到胖子的背叛;瘦小卻敏感而早熟的洋洋則在對世界和性的朦朧初覺時便飽受挫折……甚至從這個家庭延伸出去的種種社會關(guān)系中的諸多人物,如阿弟、小燕、莉莉、胖子、阿瑞、大大等無一不處于生命的焦灼、沮喪狀態(tài)。影片中多次出現(xiàn)婷婷手中的那盆綠色植物,無法不讓人覺得這是導(dǎo)演有意設(shè)下的象征——它總也長不開,一如這個布滿挫折的世界中人們無法綻放的生命。

圖1 電影《一一》劇照
如前所述楊德昌試圖講述的是生老病死的生命各階段,家庭成員的經(jīng)驗彼此投射。為了實現(xiàn)這一意圖,他充分運用了電影的魅力,以一段精彩紛呈的交叉剪輯將時間性引入共時的空間之中。這個段落將NJ與初戀情人阿瑞的東京之旅、婷婷的初戀以及洋洋對一個女生的暗戀共置在一起;導(dǎo)演選擇了相同的時間(連時差都被考慮)、相似的環(huán)境,而NJ對初戀的描述(小學(xué)時的暗生情愫和中學(xué)的第一次約會)也完美無間地完成了對婷婷、洋洋彼時狀態(tài)的描述……以上種種,構(gòu)成一個精致的關(guān)于“生命∕愛”的循環(huán)敘事!然而,故事依然還是不可逆轉(zhuǎn)地走向了悲觀——阿瑞不辭而別、胖子落跑、洋洋一生濕淋淋地回來。后來,NJ抽著煙對敏敏嘆氣說:“本來以為再活一次可能會有什么不一樣,結(jié)果,還是差不多,沒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覺得,再活一次的話,好像真的沒有那個必要,真的沒有那個必要。”而剛從山上靈修回來的敏敏也說,“其實真的好像沒有什么不一樣,只是那個位子好像換了一下……”——諷刺的是,這是整部影片中這對夫妻最彼此同情的一次交談,風(fēng)沙滿袖、悲不可遏。一個經(jīng)典的楊氏前文本幽然現(xiàn)身:“變化是輪回的循環(huán)”——《恐怖分子》中的女作家如是說。
但或許是彼時的楊德昌漸漸告別了激憤與悲觀,影片給出的結(jié)尾卻格外溫暖。這個逆轉(zhuǎn)由洋洋完成。陽光明媚、草木葳蕤、高調(diào)光都一一呼應(yīng)開頭;穿著西裝的洋洋以童稚而嚴肅、一字一頓的聲音向去世的婆婆念著告別辭:
“婆婆,對不起,不是我不喜歡跟你講話,只是我覺得我能跟你講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不然你就不會每次都叫我‘聽話’。就像他們都說你走了,你也沒有告訴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覺得那一定是我們都知道的地方。
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嗎?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情,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我想這樣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說不定有一天我會發(fā)現(xiàn)你去了哪里,那時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講,叫大家一起過來看你呢?”
在這個過程中,鏡頭分別拍攝分坐靈堂兩側(cè)的敏敏與NJ、婷婷,他們的目光集中于洋洋,若有所思……鏡頭的緩緩搖動足以在觀眾頭腦中構(gòu)成又一副家庭全景(度過劫波之后生命重歸平靜)。這樣一個溫暖而百感交集的段落無疑是另一個楊氏經(jīng)典,這個喜歡拿著相機拍攝別人后腦勺、告訴他們自己看不見的東西的小男孩平衡了整部影片的悲觀色彩,向所有人揭示了生命的意義。無怪乎吳念真后來回憶這部電影時感慨著說“何其溫暖”。然而,從整部影片的情節(jié)來看,這種溫暖卻似乎來之太易、顯得勉強——更大的可能或許是洋洋長大后依然會循著NJ的前輒,某一天也感嘆“結(jié)果,還是差不多,沒什么不同”,畢竟影片中NJ曾對昏迷中的婆婆說洋洋“跟自己很像,真的很像”。不過,也可能這個溫暖的結(jié)尾是楊德昌要給我們的一千根琴弦,史鐵生意義上的一千根琴弦?
二、電影語言的現(xiàn)代性更新
與“素人藝術(shù)家”般的侯孝賢不同,始終堅持以電影探討臺北都市現(xiàn)代性主題的楊德昌發(fā)展出了一套精巧、繁復(fù)的現(xiàn)代主義電影語言。這套語言在《一一》時已臻純熟,工巧精微而渾然天成,頗有“老去詩篇渾漫與”的味道。或許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彼時的楊德昌還生發(fā)出了對“鏡像”本身的高度自覺。
(一)都會建筑元素與人性的互動
除去錯落的群像敘事,《一一》電影語言的現(xiàn)代主義風(fēng)格最主要的表現(xiàn)在于對現(xiàn)代都市建筑元素(不管是整體的建筑物,還是其燈光和內(nèi)部的線條、景框、物品等等)的驚人運用。楊德昌曾說“建筑是人性與科技平衡的最佳體現(xiàn)”[1],而工科出身的他也確實在影像中廣泛涉及建筑與人性的互動——說到底,這根源于建筑森林本就是都市人最顯著的生存景觀,而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人性異化境況也最外觀地暴露于建筑對人性的壓迫與宰制中。婆婆昏迷送進醫(yī)院后,NJ在醫(yī)院走廊遇見匆匆趕來的小舅子阿弟和美國等人的一個全景鏡頭(圖1),且不說攝影機僅僅拍攝人物在玻璃窗上的影像從而形成雙重鏡像的大膽構(gòu)思不說,其構(gòu)圖也極具匠心。畫面前景被三縱一橫的窗框分割,中景是NJ和阿弟,遠景則是美國等三人;NJ雖然位于畫面的中軸,但其相對瘦小的身軀卻被兩條縱向的窗框分別與阿弟、美國等人隔開,而且其空間逼仄、促狹,僅占整體空間的五分之一不到。畫面的情境則是婆婆昏迷,趕來的阿弟卻吵嚷著“運氣”、“還錢”,遠景中的美國則正在撒酒瘋,如此我們便可理解其構(gòu)圖的意義所在——窗框的分隔表明了NJ的不被理解,以及堅守;而空間的逼仄則明白無誤地傳達出其無奈。此外,深夜里醫(yī)院走廊的低調(diào)光用來形容NJ的黯淡心情也恰到好處。
不過,影片中對建筑物燈光最令人驚嘆的一次運用出現(xiàn)在敏敏哭訴第二天后在其辦公室里的一個長鏡頭(圖2):燈光全熄,辦公室里一片黑暗;然而臺北夜景里遠近建筑和道路上往來奔馳的汽車的燈光全部通過玻璃窗的反光而被窗外的攝影機拍下;最詭異的是,不遠處一棟高層建筑的最頂端的紅色閃爍燈化為一個紅點竟停留在敏敏的心臟不遠處跳動;大約三十秒之后,沉思良久的敏敏轉(zhuǎn)身走向南茜,南茜迎上來,依然形成一個人物占據(jù)中景的全景鏡頭,而透過玻璃攝下的畫面竟像是兩人臨空于臺北夜景之上。“我沒有地方去。”敏敏說——“這城市的所有人都無處可去”,楊德昌的意圖昭然若揭。有論者甚至認為“這是楊德昌電影中對于城市地志及都會意象最具有象征力量的鏡頭”[2]196。類似的鏡頭在《一一》中出現(xiàn)多次,可以說楊德昌對此是自覺且視為得意之筆的。
(二)科技時代的“鏡像”自覺
《一一》中精細而渾融的現(xiàn)代主義語言特色固然令人驚喜,但筆者以為,整部影片最讓人感受到楊德昌巨大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的語言藝術(shù)在于其對鏡像時代的高度自覺和批判性思考。玻璃、鏡子、照相機、監(jiān)控攝像頭、電玩游戲乃至電影本身,楊德昌將這些現(xiàn)代都市中常見的紛繁的鏡像制造者有條不紊地納入影片,與影片形成一個個雙重鏡像的“鏡中鏡”結(jié)構(gòu)。借由這種反身指涉,他不僅實現(xiàn)了對電影本身的解碼,同時完成了對新千年虛實邊界模糊的科技時代的重新編碼。
正是于此,胖子和洋洋的意義得到了全新的詮釋。
影片中胖子(及其未現(xiàn)身的舅舅)是個地道的影迷,他認為“電影使人類的生命經(jīng)驗延長了至少三倍”——這或許是我們聽過的對電影最美麗的一次告白;然而,急轉(zhuǎn)直下的是他最終殘忍地殺害了那個英語老師;更關(guān)鍵的是,血腥的砍殺場面被一段拳打腳踢的電玩游戲替代。在這里,真實與虛幻急遽地彼此互相指稱:虛擬的電影經(jīng)驗被指認為真實,而真實的殺人經(jīng)驗又被替代為虛擬。不幸的是,電影中體驗而來的殺人經(jīng)驗無法為其消除仇恨,而其殺人也絕非一場電腦游戲。于是悲劇終至于誕生。

圖2 電影《一一》劇照
如果說胖子的悲劇構(gòu)成了對虛實之間邊際混淆的鏡像時代的諷刺與批判,那洋洋則無疑處于價值鏈的另外一端。事實上他是影片中唯一的天使般的角色。這個8歲但身體發(fā)育遠遠落后于同齡人的小男孩卻對世界懷著純真或許略顯執(zhí)拗的熱情與視野。這種熱情和視野來自于一個令其百般困惑的問題:“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這樣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么?”因此他拿著照相機拍攝了大量人物的后腦勺,只是想要讓別人看到自己看不到的東西。某種程度上說,他同樣受到鏡像時代的戕害,比如被學(xué)校里無處不在的攝像頭的監(jiān)控。這當(dāng)然涂抹出“以外在的或直接的力量使個體屈服于社會操縱”[3]xxiii的當(dāng)代景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的某一面相。然而,不同于福柯筆下“全景敞式監(jiān)獄”式的當(dāng)代社會悲觀隱喻,楊德昌并沒有徹底將抵抗驅(qū)逐出場:洋洋初心不改,依然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情,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整部影片最具力量的時刻即來自于此。
筆者認為無論是對電影有著動人告白的胖子還是舉著照相機尋找更廣闊的真實并視之為生命意義的洋洋,無疑都是楊德昌的夫子自道。本片拍攝于20世紀的最后幾年,正在到來的鏡像時代成為楊德昌新生的問題域;而作為當(dāng)代華語影壇兼具理性思維和人文關(guān)懷的導(dǎo)演,他對鏡像時代的批判性思考也達成了迄今仍罕有其匹的高度與深度。通過胖子的生命悲劇和都市中無處不在(公寓樓、學(xué)校等)的監(jiān)控攝像頭以及電腦游戲,他對鏡像時代的虛實不清深懷憂慮;而通過那個感動過無數(shù)人的小男孩洋洋,他又傳達了鏡像的積極力量,或許也可以視為他對自己電影生命給予的一個溫柔的總結(jié)。
無論如何,十三年后我們回頭再看,不得不驚嘆于楊德昌的深刻預(yù)見:在那個臺灣還流行著小田抄大田的年代,他便以鏡像本身的方式完成了對鏡像時代的解構(gòu)與重構(gòu)。而如今這個越來越數(shù)字化的時代正越來越將所有人放置于一座鏡城之中,無人可以逃脫。
然而是陷落還是重生?結(jié)局是開放的,而《一一》本身就構(gòu)成一個召喚,正像它的英文名字——“a one and a two”——唯一“鏡像”,兩般命運。
[1]木衛(wèi)二,利小刀,左敦.空前絕后,獨一無二:楊德昌的價值與遺產(chǎn)·楊德昌說楊德昌[EB/OL].http://news.mtime.com/2011/10/28/1473958-9.html.
[2]黃建業(yè),等.楊德昌:臺灣對世界影史的貢獻[M].臺北:躍升文化,2007.
[3]Meenakshi Durham,Douglas Kellner.Media and Culture Studies:Keywords[M].Oxford: Blackwell,2006.
J90
A
劉金平,廈門大學(xué)中文系2013級文藝學(xué)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