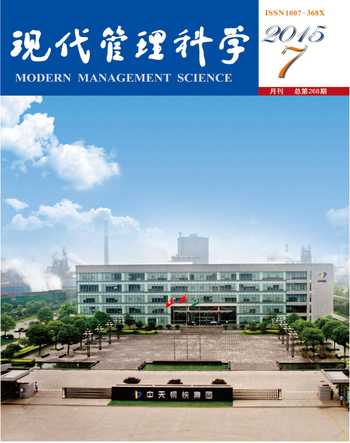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低端鎖定困局與突圍
李智永 景維民
摘要: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模式與傳統的制造業依賴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類似,都得益于產品內國際分工的深入展開。同樣,這種發展模式也造就出了眾多的“文化富士康”們。因而,它們在試圖沿著全球價值鏈升級的過程中也必將面臨著相似的低端鎖定困局。然而,文章發現文化創意產業中強大的本土市場效應的存在將為該產業鋪就一條內生的突破低端鎖定的升級道路。
關鍵詞:文化創意產業,產品內國際分工,低端鎖定,本土市場效應
一、 問題提出
創意與創新、創造等的含義都不相同,與后兩者相比,創意更多的是指思想、觀點、設計等人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創新活動。體現在經濟生產領域,創意需要借助于某種物質載體或具體形式表達出來,例如新穎的產品造型,獨特的文化內涵、特有的產品表現形式等。其滿足的是人類的精神、文化和娛樂需求,提供的乃是一種文化體驗。所以,創意經常和文化相聯系。當從事文化創意工作的企業、人員、機構等達到一定規模,采用工業化大企業的組織和生產模式時,就形成文化創意產業。該產業因其無污染、附加值高、難以被模仿、運用廣泛等特有屬性可以成為推動產業升級的動力。然而,正如一些學者觀察到的,在文化創意產業國際分工體系下,作為后發國家的文化創意產業本身可能也需要升級。當然,文化創意產業本身也可能因為其特有屬性而具有獨特的升級道路。例如王緝慈等(2008)、通過對我國動漫產業興起和發展的案例研究發現缺乏互補資產是我國文化創意產業國際競爭力不強的關鍵原因之一,因而,升級道路就是大力完善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互補資產。然而,完善互補資產僅是構建完整產業生態系統的必然要求,并不能保證該產業生態系統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從一些案例來看,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有進一步提高產業地位的趨勢,例如電影業的2D轉3D產業,一些企業正在從從低層次接包方向總接包方的轉變。這種地位的提高是以本土電影制片企業發包為前提的,一些核心的技術仍未能有效掌控。但無論如何,正是由于中國電影轉制企業很早就參與到了國際分工體系中,對這一體系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成功地擔任總接包方的角色。從這一點看,只有先加入到國級分工的產業鏈中,才有可能進一步向上游發展的機會。此外,依賴本土市場效應是一個有效的提高企業在產業鏈中的位置的戰略,這一戰略雖然不是以掌握核心技術和提高創新能力為前提,但確實有效地提高了企業的利潤、品牌價值和擴張能力,不失為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突破低端鎖定困局的一條可參考的路徑。
二、 產品內國際分工與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低端鎖定困局
1. 產品內國際分工與價值鏈低端鎖定。產品內分工是國際分工演進過程中出現的新形態。按照蒲華林、張捷(2006)的觀點,產品內分工是比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更高級的一種國際分工模式。相比于后兩種國際分工生產模式,產品內分工主要是指針對某一具體產品生產的國際分工,例如,Tempest(1996)詳細描述了“芭比娃娃”的產品內國際分工和價值鏈分布情況:在“芭比娃娃”的生產流程中,美國公司提供產品模板,并承擔最終的彩繪和市場銷售業務。印尼、馬來西亞、中國等地區的企業承擔原材料采購和零部件的生產和組裝。“芭比娃娃”在美國的零售價約為10美元,其中美國公司獲得了8美元的價值,而由中國勞動力所產生的增加值僅有0.35美元。中國等地的企業盡管所獲得利潤十分有限,但也有機會借助參與國際分工合作所帶來的知識溢出效應來提高技術水平和改善分工地位。中國的汽車、計算機、機電產品、設備制造、甚至是服裝等產業,都曾走過由零部件加工、組裝到原始設備制造,再到自主品牌制造的路徑。當然,這一變化過程不可能是自然而然、一帆風順的,處于產業鏈上端的國際壟斷企業不可能將賴以獲得高額利潤的產業地位拱手相讓,如果國家產業政策和企業發展戰略失誤,則很可能導致產業長期陷入低端價值鏈環節。Lall等(2005)的研究結果顯示,南亞地區的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等國由于過度依賴紡織品出口,在全球價值鏈中停留在低端環節,相比東亞、拉丁美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其國際分工地位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發包企業的角度來看,產品內國際分工問題的本質是一個關于產品生產環節在全球范圍內的最優地理布局的決策問題。該決策過程中遵循的核心原則是工序的要素密集度與區域的要素稟賦結構匹配。張紀(2013)在制造業中觀察到的球價值鏈地理布局規律體現了這一原則:發達國家憑借強大的技術能力和鄰近主流市場的優勢,占據最終產品和核心零部件的研發和銷售等關鍵環節,而發展中國家則憑借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資源,承擔非核心零部件的生產和產品的組裝等低端環節。一些文化創意產業也具有明顯的產品內國際分工的特點,例如動漫、電影等產業,也可能陷入價值鏈低端鎖定的困局。
2. 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中國創意文化產業的興起與文化產業的國際分工密切相關。首先,創意文化產業是從發達國家引入的一個新興產業。日本早在1995年就確立了21世紀的文化立國方略;1997年,英國將創意產業列為國家重點扶植產業。時至今日,在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中,文化創意產業在其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甚至至關重要。美國的好萊塢大片、NBA職業籃球賽;日本的動漫;韓國的韓劇等等不僅已經成為這些國家的文化名片,而且也是其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據報道,美國和日本的文化創意產業的規模已經超過了傳統的農業、工業、交通和建筑等行業。相比較來說,盡管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迅速,當仍處于起步階段,無論是產業規模、技術水平、市場環境和組織結構等都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其次,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大規模地參與了國際文化產業分工。近年來,我國創意服務貿易發展十分迅速。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我國創意服務進出口額分別從2001年的3.1億美元、3.0億美元,擴大到2011年的31.7億美元、41.4億美元,年均增速分別為28.2%、31.3%,不僅遠高于同期世界創意服務進出口年均增速,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年均增速,創意服務進出口占全部服務進出口的比重,分別由2001年的0.8%和0.9%提高到2011年的1.4%和2.3%,對我國服務貿易增長的貢獻度明顯提高。(周升起、張鵬2014)與此同時,也涌現出了一批承接服務外包的文化創意公司,如靈動力量科技、幸星動畫、瑪雅影視、尚陽數字科技等等。
中國文化創意產業參與國際文化產業分工,不僅能夠激發一個新的產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也有利于技術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夠學習到先進的市場運作模式和經驗,從而有利于提升產業地位。江小娟(2008)曾明確指出國際服務外包對于承接國來說能夠產生巨大的技術外溢效應,包括人力資本流動效應、示范和學習效應、競爭效應、規模經濟效應以及關聯產業帶動效應。文化創意產業概莫能外,例如中國的一些電影和動漫制作企業,通過參與國際分工積累了大量的制作經驗和儲備了一批技術人才,在代工了一段時間后,開始通過自主培養立體分析師、合成師以及和院校合作等多種方式積極謀求技術能力升級,以期提升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當中的位置。
3. 中國文化創意產業面臨的低端鎖定困局。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歷程表明,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制造企業可能被發包企業俘獲,陷入全球價值鏈的低附加值環節和全球技術體系的非核心領域的雙重鎖定局面。(康志勇,2009;時磊、田艷芳,2011)這一發展現實否定了早年Gereffi(1999)等人所斷言的嵌入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沿著價值鏈實現“從工藝升級到產品升級到功能升級再到鏈的升級”的升級模式。這是因為在Gereffi等人的抽象世界中,他們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企業之間關系的處理過于簡單,沒有考慮到二類企業在產業轉移與產業承接過程中的利益博弈。早在1991年,在產業內分工體系下,Grossman和Helpman基于南方和北方動態利益博弈的“質量階梯”理論就揭示了南方和北方之間的技術差距會持續存在,最后得出后發國家將永遠專業化于生產技術含量低的產品的結論。這一結論在將分工對象從產品推進到工序后更具魯棒性,原因是在產品內分工體系中,發達國家可以進一步將完整的生產技術片段化、黑箱化,從而導致后發國家企業的學習更加困難。
不僅制造業面臨低端鎖定困局,中國的軟件業以及動漫、油畫等文化創意產業中的許多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也都長期處于低端環節,陷入了產品內分工陷阱。盧峰(2007)發現,中國所承擔的軟件外包業務很大一部分也屬于編碼和測試工序流程等對員工技能要求比較簡單,附加值比較低的環節。王緝慈等(2008)在動漫、油畫等文化創意產業中也觀察到了類似的價值鏈結構。該文認為,中國大量動漫企業還處于加工制作的低端環節,缺乏原創動漫產品和動漫互補性資產,這些動漫產業與其說是創意產業不如說是代加工工廠。尚濤,陶蘊芳(2011)的研究顯示,我國文化創意產業雖然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但總體上的創意服務競爭力不高,表現出量大而結構低下的特征。這一方面是由我國的總體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根據邁克爾·波特的經濟發展四階段論,文化創意產業的大發展應該和創新驅動階段和財富驅動階段相匹配,而我國目前總體上還停留在投資驅動階段。在群眾消費結構較低、科技文化儲備不足的情況下,要求文化創意產業跨越式發展顯然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也和發達國家的市場壟斷行為密切相關。以美國為首的一些發達國家利用TRIPS協議,在國際文化貿易中設置知識產權壁壘,不僅在進口國形成市場優勢,也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以此來維護其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
三、 本土市場效應與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突圍之路
在關于發展中國家企業如何突破低端鎖定的研究中,劉志彪和張杰(2007)等學者從全球價值鏈理論視角給出的突破路徑是:實現從嵌入全球價值鏈到構建國內價值鏈的轉變。路風和慕玲(2003)等學者通過對激光視頻播放機等產業和企業的案例研究也給出了類似的突破路徑:實現從代工向發掘和滿足本土市場需求的轉變。然而,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該結論成立的前提是在滿足本地市場需求的競爭中,本地企業比跨國公司等非本地企業具有更強的競爭優勢,也即存在所謂的本土市場效應:貼近本土市場能帶來競爭優勢。從現實情況看,中國文化創意產業完全可以通過這一路徑實現提升產業水平的目的。
首先,中國有著規模巨大的潛在文化消費市場。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發布的“2013中國文化消費指數”的測算,中國內地文化消費潛在規模為47 026.1億元人民幣,而當前實際文化消費規模為10 338億元,存在超過3.6萬億元的文化消費缺口。而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數據,2012年中國文化產業的市場規模為16 000億元。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增長,影視、歌劇、體育賽事、游戲等文化娛樂消費走入千家萬戶。2013年,中國城鎮家庭人均文教娛樂消費支出2 294元,比2012年增長12.8%。農村家庭人均文教娛樂消費支出也保持了9%的增長速度。國際文化產業巨頭也越來越重視中國市場,植入中國元素成為好萊塢電影的一種流行趨勢。迪斯尼、夢工廠等世界知名主題公園紛紛登陸中國市場。總之,我國巨大的經濟體量和居民消費轉型為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所有未有的發展機遇。
其次,中國政府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2009年,我國出臺了第一部文化產業專項規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標志著文化產業上升為國家的戰略性產業;“十二五”規劃提出,要將文化產業發展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隨后,一系列關于支持文化產業的財政、稅收、金融、用地等方面的政策出臺落實;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又下發了《關于印發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和進一步支持文化企業發展兩個規定的通知》,修訂完善一系列推動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出臺,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很好的外部環境。
最后,當地市場知識的粘性是發揮本土市場效應的一個重要的機制。當地市場知識是指企業在某地經營時,處理與當地政府、供應商等價值網絡參與者之間關系以及對產品進行適應性創新滿足當地消費者需求等過程中需要了解和掌握的知識。這是一種具有情境性的分散知識,其發送、傳遞、接收、理解與運用需要成本,因而具有粘滯性。由此造成理解、獲取和利用該類知識需要在當地進行多次面對面的交流互動,有時甚至還需了解當地語言、消費習慣、風俗等情境性因素。因而,在滿足本土需求的競爭中,貼近市場和具備相應情境知識的當地企業可能獲取比非當地企業更多的當地市場知識。利用當地市場知識非均勻分布的特性,通過本土適應性創新,當地企業就能得到由其帶來的超額準租,從而獲取相對于非當地企業的競爭優勢。
四、 結論
從以上分析中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兩個結論:
第一,后發國家的某些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模式與制造業的依賴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類似。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產品內國際分工體系的深入展開,作為后發國家的中國企業由于缺乏足夠的技術創新能力以及遠離主流市場,只得依賴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等要素或資源嵌入全球價值鏈,承擔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環節。在這種外向型的文化發展模式下,企業在其成長過程中只能積累代工服務能力,缺乏利用創意以及技術創新滿足市場需求的能力的積累。因而,從本質上來看,具有這些能力特征的企業就是一個個“文化富士康”們。同樣,與制造業中企業的命運類似,這些處在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的“文化富士康”們在升級的過程中將面臨著低端鎖定的困局。
第二,文化創意產業中強大的本土市場效應的存在將為該產業鋪就一條內生的突破低端鎖定的升級道路。如今的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是一個技術知識和創意知識相互交融的產業。然而,由于創意知識的粘性更強,現實的知識流動規律必定是技術知識遷移到創意知識處,再加上創意知識的本土特性,由此導致文化創意產業中存在著強大的本土市場效應。即在通過創意滿足本土市場需求的過程中,更貼近本土市場需求的當地企業相比于非當地企業更具有競爭優勢。同時,在滿足本土市場需求的過程中,企業的技術創新與創意能力必將獲得更快的成長。也就是說,依托基于本土市場效應的升級路徑是內生的。
參考文獻:
[1] 郭新茹,劉冀,唐月民.價值鏈視角下我國文化產業參與國際分工現狀的實證研究——基于技術含量的測度[J].經濟經緯,2014,(5).
[2] 江小娟.服務全球化與服務外包:現狀、趨勢及理論分析[M].人民出版社,2008.
[3] 康志勇.稟賦結構、適宜技術與中國制造業技術的“低端鎖定”.世界經濟研究,2009(1)
[4] 盧峰.當代服務外包的經濟學觀察:產品內分工的分析視角.世界經濟,2007,(8).
[5] 路風,慕玲.本土創新、能力發展和競爭優勢——中國激光視盤播放機工業的發展及其對政府作用的政策含義.管理世界,2003,(12).
[6] 蒲華林,張捷.產品內國際分工與中國零部件貿易——理論、現狀和問題[J].世界經濟研究,2010,(4).
[7] 尚濤,陶蘊芳.我國創意產業中的國際分工研究,——基于典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分析.世界經濟研究,2011,(2).
[8] 時磊,田艷芳.FDI與企業技術“低端鎖定”.世界經濟研究,2011,(4).
[9] 王緝慈,梅麗霞,謝坤澤.企業互補性資產與深圳動漫產業集群的形成——基于深圳的經驗和教訓.經濟地理,2008,(1).
[10] 張紀.基于要素稟賦理論的產品內分工動因研究.世界經濟研究,2013,(5).
[11] 周升起,張鵬.中國創意服務國際分工地位及其演進——基于“相對復雜度”指數的考察[J].國際經貿探索,2014,(10).
[12] 郭新茹,韓順法.文化民生:率先實現現代化的新探索[J].現代經濟探討,2014,(6).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項目號:14JJD790035)。
作者簡介:景維民(1966-),男,漢族,河北省大名縣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轉型經濟學、國家治理;李智永(1980-),男,漢族,河南省輝縣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博士生,研究方向為轉型經濟、產業經濟。
收稿日期:2015-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