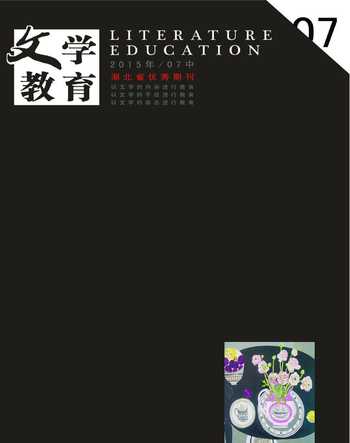淺析葉芝的審美現代性
劉娟
內容摘要:葉芝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英語詩人”之一,其現代性問題近來成為評論界爭議的焦點。本文試以卡林內斯庫提出的兩種現代性為切入點,著重考察葉芝主要詩歌作品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批判以及拯救現代人兩個層面,分析并揭示葉芝特殊的審美現代性。
關鍵詞:葉芝 現代性 審美現代性 批判 拯救
愛爾蘭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Yeats1865-1939)在世界文壇上無疑是位舉足輕重、頗具影響的人物。他在長達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里,為世人留下大量優秀經典的詩歌作品。學術界對葉芝的研究與關注從未間斷。葉芝的現代性問題,評論界普遍存在兩種觀點:反對方指出葉芝對歐洲宗教和藝術傳統的質疑并沒有龐德那樣深刻,且藝術創新上也沒有龐德和艾略特那樣徹底。支持方卻堅持認為葉芝在19世紀詩歌語言上的創新為龐德的“直接對待事物”詩歌理論做出了貢獻。有誰在讀到“基督重臨”(The Second Coming,1919)不被作者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現時的一種深深的焦慮所震撼[1]?在安妮·福格蒂(Anne Fogarty)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找到最新關于葉芝現代性的論述。安妮以葉芝廣泛投入到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被視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運動一部分),和其作品呈現出的自省性來重新探討葉芝特殊的現代性[2]。
相比之下,國內對葉芝現代性的研究似乎顯得較為貧乏。何寧曾在2000年的一篇題為《葉芝現代性》文章中突破簡單地以艾略特創作為標準的瓶頸,代之從葉芝作品所反映現代人的精神狀況等方面來探討葉芝現代性問題。
一.理論基礎
在討論葉芝現代性這一問題之前,首先梳理下其中幾個關鍵概念:現代性,現代主義與現代化。它們看似相似,卻有著不同的內涵。“現代化主要是從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中總結出來的一個概念,指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不斷發展的一個轉化過程。現代化可視為一個如鮑曼所言的‘未完成且無法完成的一個過程,我們及世界文化正處在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中,而這個發展過程是指向未來的[3]。”可見,現代化是一個表示過程的動詞,是動態的。關于現代性,卡林內斯庫認為它是一個時間∕歷史概念,我們用它來指在獨一無二的歷史現時性中對于現時的理解,也就是說,在把現時同過去及其各種殘余或幸存物區別開來的那些特性中去理解它,在現時對未來的種種允諾中去理解它——在現時允許我們或對或錯地去猜測未來及其趨勢﹑求索與發現的可能性中去理解它[4]。卡氏還進一步提出存在“兩種現代性”的觀點。“無法確言從什么時候開始人們可以說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卻又劇烈沖突的現代性。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某個時刻,在作為西方文明史的現代性同作為美學概念的現代性之間發生了無法彌合的分裂。(作為文明史階段的現代性是科學進步﹑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帶來的全面經濟社會變化的產物)……相反,另一種現代性,將導致先鋒派產生的現代性,自其浪漫派的開端即傾向于激進的反資產階級態度。它厭惡中產階級的價值標準,并通過極其多樣的手段來表達這種厭惡,從反叛﹑無政府﹑天啟主義直到自我流放[5]。”這兩種現代性一直處于一種對抗的態勢,形成一種張力,而也正是現代性自身的矛盾性與對抗性推動社會的進步。
現代主義則是一場運動,一種文學思潮,是現代性的一種載體。現代化,現代性和現代主義是分別表過程,本質和理念的詞。梳理完三個核心概念,再來審視葉芝的現代性,我們不難發現其特殊性。作為風格多變,創作年限長,自詡為“最后的一位浪漫主義者”的過渡性詩人,葉芝同時又被稱作愛爾蘭的“第一位現代主義者”。本文試以兩種現代性為切入點,從審美現代性的兩個層面分析詩人特殊的現代性。
二.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批判
卡林內斯庫認為,在西方現代化歷程中,不知從何時起,逐漸產生了兩種現代性:一種是以進步、理性、個人主義為核心價值并滲透到社會各領域的資產階級現代性∕啟蒙現代性;一種是對此予以否定、批判、反思與超越的審美現代性∕美學現代性。所謂審美現代性,是對前者所代表的資產階級重商主義、功利主義與市儈主義,對資產階級和世俗階層的現代價值觀的否定與批判,是一種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現代性”[6]。
以藝術和文學為代表的審美現代性同資產階級現代性之間一直處于緊張的對抗中。作為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審美現代性以審美的方式站在資產階級的對立面。正是現代性這種內在的矛盾與沖突才使得現代性達到一種平衡、和諧的狀態。那么葉芝的詩歌又是如何體現詩人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批判的呢?
首先,葉芝對資產階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是嗤之以鼻的。詩人早年在母親的家鄉斯萊戈(Sligo)小鎮渡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斯萊戈美麗迷人的自然風光同倫敦工業化城市中雜亂不堪的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葉芝來說斯萊戈代表的是工業革命前的愛爾蘭,一個寧靜、和諧的世外桃源,而倫敦和英格蘭則是資產階級工業化革命和資本主義的搖籃,充斥著臟亂、嘈雜的工廠與貧民窟。葉芝將英格蘭與其厭惡的現代物質世界的一切——帝國主義、貪婪的物質主義、城市的丑陋、骯臟與陰暗面聯系起來,將愛爾蘭視為資產階級所謂文明中的一方凈土。在《1913年9月》(September 1913,1913)中,葉芝運用犀利的反諷,尖銳地抨擊了愛爾蘭新興的天主教徒中產階級庸俗的市儈氣及其自私吝嗇的拜金主義:“清醒過來之后,你們需要什么,∕除了在油膩的錢柜里摸索,∕給一個便士再加上半個便士,”∕給顫聲的禱告再加上禱告,直到∕你們把骨頭里的精髓榨干;∕因為人們生來就是為祈禱和攢錢:∕浪漫的愛爾蘭已死亡消逝,∕隨歐李爾瑞一起在墳墓中。”當時戴著偽善面具的資產階級們,面對愛爾蘭的民族事業,他們是麻木、妥協的,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個獨立的愛爾蘭,而是金錢、地位,是唯利是圖。
《基督重臨》(The Second Coming,1919)中葉芝又為讀者描繪了一幅現代西方文明已成荒原的全景圖:“盤旋,盤旋在漸漸開闊的螺旋中,∕獵鷹再聽不見馴鷹人的呼聲;∕萬物崩散;中心難再維系;∕世界上散布著一派狼藉,∕血污的潮水到處泛濫,∕把純真的禮俗吞噬;∕優秀的人們缺乏信念,∕卑劣之徒卻狂囂一時。……[7]”詩人用兩個交相滲透的旋轉的錐體圖形來說明造成人類歷史循環的主客觀因素的相互作用。一個文明從其中一個錐體的尖端開始,呈螺旋形旋轉到底部而“崩散”結束,然后又從另一錐體的尖端開始反向旋轉,開始另一個文明的循環。葉芝認為從一個文明結束到另一個文明開始要經歷兩千年的時間并預言舊的文明(意指二十世紀前的西方文明)已走到盡頭。詩的開頭三行是螺旋錐體象征的形象變體。文明的發展從錐體的尖端開始,呈螺旋形旋轉,“漸漸開闊”,到底部而“崩散”結束;然后從對立錐體的尖端開始反向旋轉,開始另一個文明的循環。詩人采用了一系列具有特定含義的意象“旋錐”、“獵鷹”、“大漠”、“世界靈魂(大記憶)”等,構成一幕幕充滿混亂、瘋狂的景象。“世界上散布著一派狼籍”,“卑劣之徒卻狂囂一時”,荒漠中的“獅身人面的形體”(兩千年歷史文明的象征) 在動搖……急迫的節奏、夸張的語調、奇詭的形象,渲染出一派陰暗、恐怖的氣氛,顯示出詩人崇尚的貴族文明——“純真的禮俗”,已淹沒在這片恐怖之中。就詩而論,我們只看到歷史的“旋體”轉向了黑暗的反面,能否再轉回到詩人理想的正面,真正實現“基督重臨”,不能不讓人產生質疑。
總之,葉芝一開始就拒絕了資本主義迅猛發展帶來的進步,他認為資產階級發展與進步并不能將人類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相反,它造成世界一片混亂,給人類還帶來更多的危機,使現代人深陷泥潭不能自拔。那么現代人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三.拯救之路
隨著十九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興起,西方工業的高速發展與進步,日益膨脹的商品經濟與突飛猛進的科學技術給世紀之交的西方物質世界帶來巨大的財富。然而,物質世界財富的積累似乎并未給現代人帶來快樂。相反對物質財富過分的追求給人的思想戴上工具理性的枷鎖,造成信仰的缺失,精神世界變成一片荒原。文化產業過分追求世俗的結果使人在大量低俗文化產品面前,顯得更加茫然失措,無所適從。怎樣才能將人從危機中拯救出來?審美現代性給出了答案。
拯救世俗是審美現代性內含的一個層面。現代社會之前,宗教始終扮演著救世主的角色。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發展,人們對上帝能否拯救人類產生了質疑,宗教開始衰落。社會學家韋伯曾提醒我們:“生活的理智化和理性化發展改變了這一情境。因為在這種狀況下,藝術變成了一個越來越自覺把握到得有獨立價值的世界,……藝術都承擔了一種世俗救贖功能。它提供了一種從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脫出來的救贖,尤其是從理論的和實踐的理性主義那不斷增長的壓力中解脫出來的救贖[8]。”在人們已喪失宗教信仰的年代,審美取代宗教而承擔起救贖世俗的責任。審美將主體從現代社會工具理性的桎梏中解救出來的同時,還實現對現代文化的提升。這種提升表現在通過審美,人感覺的靈性得到恢復,人在審美過程中得到美的享受,陶冶情感,獲得情感上的財富。藝術作為主要的審美形態,成為審美現代性發揮救贖功能最重要的載體與方式。藝術在宗教衰落的現代社會中成為生存意義的提供者,一方面向人們敞開了一個科學技術無法提供的關于生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把人們帶回到“本真”的領域,遭遇到自己的感性身體、欲望和情緒,這正是“救贖”的深意所在[9]。
1928年,葉芝出版了代表其最高藝術成就的詩集《塔》(The Tower,1928),這部詩人在晚年完成的現代派詩歌的經典之作匯集不少杰作,包括《駛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1927)、《塔》(Tower,1926)、《一九一九》(Nineteen Hundred and Nineteen,1919)、《麗達與天鵝》(Leda and the Swan,1923)及《在學童中間》(Among School Children,1926)。該詩集問世之前,面對現代世界的精神荒原,詩人并沒有告訴我們人類的出路到底在何方。在《塔》中,我們似乎找到了答案,詩人呼喚現代人通過藝術實現自我救贖,在藝術為人類建造的“烏托邦”中得到永生。
詩人想通過藝術拯救現代人的思想突出表現在《駛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1927)這首詩中。“拜占庭”包含了兩種對立的概念。一是愛爾蘭,另一個則是拜占庭。拜占庭是小亞細亞古城,后由羅馬皇帝康斯坦丁一世(287?-337)重建,在330年改名為康斯坦丁堡;公元六世紀時為東羅馬帝國首都,東西方文化在此交匯,繁榮一時,葉芝視之為理想的文化圣地,藝術永恒之象征[10]。詩中的愛爾蘭不僅僅是指葉芝生活的地方,它同時象征葉芝所處的當下現實世界。在葉芝心中自然物質世界“絕非老年人適宜之鄉”。而拜占庭完全是神圣的理想國度,寧靜祥和,保持著古時繁盛的風貌,它是藝術的世界,永恒的國度,神圣的殿堂。葉芝寫這首詩的時候已經是六十歲的老人,肌體已衰老,他將老年人比作無用之物猶如一根竿子撐著的破衣裳。但詩人卻保持著年輕詩人豐富的想象力,他要離開愛爾蘭,猶如渡過生命之海,去到拜占庭,求得永恒的藝術,在藝術中永生。詩人曾寫道:“我覺得我應該花一個月的時間到我選擇的拜占庭去過一段時間[11]”,可見拜占庭是詩人向往的理想之地。詩人描繪出現實物質世界的一派景象:年輕人沉湎于感官的刺激中,沉浸在青春、情欲和自我放縱的可愛盛夏季節里。但他們卻忽視了對精神、智慧的追求。在他們身上“我”看不到希望,所以“我”要拒絕這種年輕人的感官享樂世界,擺脫肉體束縛,在永恒的藝術世界里求得永生,得到救贖。詩人來到向往已久的圣地拜占庭后,請圣人們從火中走出來,成為“我”靈魂的導師,火要將“我”所帶有的塵世欲望之心燒盡。圣人們從火中走出來拯救“我”的靈魂。“我”來到這“神圣的城堡”,“神圣的城堡”在這里已經沒有宗教意味,它是神圣崇高的,遠離土、氣、水等俗物,卓立于燦爛的凈火之中。敘述者“我”強烈希望自己變成古希臘金匠制成的金鳥,棲立在金制的枝條上唱歌,將皇帝喚醒,向貴族歌唱歷史、現在和未來。這時詩人也“脫離自然界”,變成停在金枝上婉轉嘀啾的金鳥。可以說,這雖是一首關于“歌唱”的詩文,但是其象征意義遠遠超出故事的本身。葉芝在一本關于拜占庭藝術的書中讀到過這種描繪:鳥兒與它的歌聲不分彼此,它們即是在烈焰中鍛造成的靈魂和靈魂所創造的詩歌。雖然葉芝本人并沒有去過拜占庭,但拜占庭在他心中是藝術永恒的象征,詩人認為塵世中的一切終歸會消失,只有藝術才能永恒,藝術正是葉芝為現代人探尋的拯救之路。
作為不斷追求詩藝創新——從后期浪漫派﹑唯美派﹑象征主義到現代派的過渡性詩人,葉芝在長達四十幾年的創作過程中,不斷進行自我批評和內省,使其整個創作體現出無所不在的變化感。其作品反映出詩人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批判,詩人進而又為現代人探索出一條拯救之路,并體現出他獨特的審美現代性。
參考文獻
[1]Holdeman David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B.Yeat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59,118.
[2]Fogarty, Anne. “Yeats, Ireland and moder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t Poetry. Davis Alex, Jenkins M. Lee.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胡鵬林.文學現代性[M].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 22.
[4][5][6]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M].顧愛彬,李瑞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6-337.
[7]葉芝.葉芝詩集(上中下)[M].傅浩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450.
[8]H.H.Gerth and C.W.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342.
[9]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趙一凡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89:187.
[10]Jeffares,A.Norman. Poems of W.B.Yeats A New Selection. London: Macmillan,1950.367.
[11]Yeats, W.B. A Vision.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5. 190.
本文為四川省教育廳2013年科研一般項目,項目編號13SB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