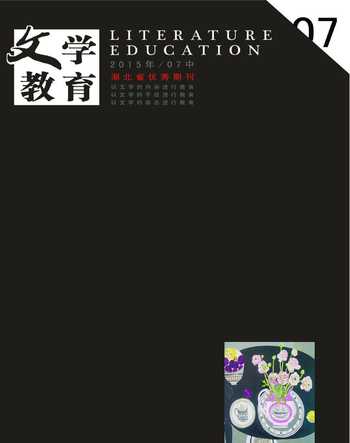例談男女作家關于“第三類女性”創作的差異
左惠連
內容摘要:伍爾芙與安德森作為二十世紀初英美兩國最具有代表性的意識流派作家,都表現出對于現代社會人類內心世界的極大興趣。在《到燈塔去》與《陷阱之門》中,伍爾芙與安德森分別成功塑造了兩位兼備傳統女性素養與現代女性思潮的第三類女性——拉姆齊夫人和沃克夫人。本文試圖通過里波韋茲基教授在《第三類女性》中所提出的第三類女性的概念,深入對比剖析兩部著作中的女性形象,為讀者展示現代社會女性的生存狀態,解決女性如何實現自我身份探索的問題,并且試圖分析男女作家對于同一類女性角色塑造的差異及其原因,借此鼓勵更多女性進行女性文學寫作。
關健詞:伍爾芙 安德森 到燈塔去 陷阱之門 第三類女性
作為英美文學領域同時期的兩位意識流派典型代表人物,伍爾芙與安德森在《到燈塔去》與《陷阱之門》中共同借用了意識流的手法,生動地刻畫了兩位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混亂而無序的生活中被困擾壓抑的兩位男性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暴怒無常,封閉內心,冷漠無情,拒絕與外界社會交流;他們企圖明白社會的秩序,但都是無終而疾。同時,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作家筆下所描繪的妻子,一方面,她們作為傳統的家庭婦女,肩負著妻子與母親的雙重角色,身上保有為男權社會所頌揚的所有優秀的女性品質,另一方面,兩個妻子較男主角來看更加從容:她們同樣意識到了世界的無可奈何,但卻最終選擇安然接受,并且安撫兩位作為知識分子的丈夫,同情憐憫著那些不得志的男性群體。她們勇敢獨立,具有領導力,能夠妥善安排家庭事務,在無序中尋求秩序,這些都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了第三類女性的特質。
一.第三類女性
縱觀二十世紀初,有關女性的探討不一而足。一方面,女性主義的先行者們紛紛走上了抗爭命運的道路。如,西蒙·波娃和貝蒂·弗里丹分別在《第二性》、《女性的奧秘》中指認女性從屬的、被愚弄的生命事實;凱特·米利特通過《性的政治》張揚性的平等;伍爾夫則用《一間自己的屋子》鼓勵女性自尊、自立、自信,改變“像蜘蛛網一樣附在人生上的生活”[1]。另一方面,二戰后陸續有不少男性學者對同時代女性的新型地位及兩性之間的關系也重新進行思考。法國社會研究院院士吉爾·里波韋茲基教授的《第三類女性》,便歸納出三類女性:第一類,受歧視的女性,任何稍有風采的事件中都找不到女人的影子,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初;第二類,受頌揚的女性。女性作為妻子,母親,老師的形象已被神化,她們特殊的能力得到空前贊美。然而,不管是飽受歧視污蔑抑或被過分吹捧,女性始終依附男性,在男性社會的目光與觀念中生活。直到二十世紀末,第三類女性,即不受限制的女性出現[2]44-50。有史以來,女性地位第一次徹底擺脫了社會秩序及自然秩序的束縛,開始了生存與發展的新階段。
二.解讀伍爾芙與安德森筆下的第三類女性
伍爾芙創作的《到燈塔去》在第一部分“窗”中集中刻畫了拉姆夫人的形象,主要以其思路想象和意識展開全文對于現代社會的不滿,而燈塔也象征著拉姆齊夫人內在的精神光芒。《到燈塔去》中的拉姆齊夫人,既保有女性傳統的特質,如:溫柔善良,順從得體;她堅持,“人必須要結婚,人們必須要生兒育女。”[3]73面對丈夫的暴躁脾氣,卻溫順地回答“他是她最尊敬的人,自己還不配給他系鞋帶。”[3]73甚至,為了迎合丈夫,妻子不斷壓抑自己的真實自我,“不喜歡自己感到自己比她的丈夫優越,即使在一剎那也不行。”[3]4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名傳統女性角色的拉姆齊夫人,面對殘酷的生活狀態,卻力圖從中辨析出一個清晰的圖案,探索出一些規律和秩序。對于丈夫,拉姆齊夫人同情他,安撫他,因為拉姆齊先生需要同情,需要得到保證,只有這樣,他才能“確信他處于生活的中心,確信他是人們所需要的人物。”[3]44至于男人,“拉姆齊夫人確實如此——她永遠同情男人,好像他們缺少了什么東西;對于女人,她從來不是如此,好像她們都能獨立”。[3]103至于周圍不得志的貧苦人,拉姆齊夫人憐憫他們,“好像她的疲勞有一部分就是憐憫別人的結果,而她體內的生命力,她生活的決心,也是被她的惻隱之心所喚起的。”[3]102至于生活,“她必須承認,生活是可怕的,充滿敵意的,它會迅速地向你撲來”,“但她被某種力量驅使著前進,向著生活揮舞著手中的利劍”。[3]73拉姆齊夫人既溫順傳統,又寬容大度,是一位典型的集傳統與現代于一身的第三類女性形象。
對比而言,《陷阱之門》作為一篇短篇故事,以沃克先生的心理視角抨擊了社會的無意義與支離破碎。文章中的妻子以配角的形式,不斷穿插在丈夫的思維里。沃克夫人,生育了三個孩子,體態走樣。每日照料家庭,時常閱讀來消遣時光。面對丈夫的沉默,沃克夫人選擇接受;面對一位突然出現的女學生瑪麗,夫人表示視而不見,認同接納;面對丈夫的火爆脾氣,沃克夫人沒有反抗。家庭的不美滿,生活的落寞,婚姻的束縛,丈夫的怪誕,在沃克夫人一個中年女性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但同焦躁不安,內心掙扎的丈夫不同,沃克夫人淡然,不回應,仿佛單純的不諳世事一般。這些證據似乎表明了沃克夫人的傳統身份。但,在文章開篇,安德森表示,“沃克夫人清楚地知道那些事。她懂得男人被囚禁在了鐵門之后,便是進了監獄。但婚姻對她來說,只是婚姻罷了”[4]1與之完全相反,沃克先生,“他仍舊不明白,但是他也許明白了會更好,至少那樣他可以找到一部分自我。婚后的五六年生活就像是風中浮動的投在墻上的樹影一樣”。[4]1面對婚姻,夫人與先生同時保持沉默。但是沃克先生的沉默緣于自己的無知,緣于自己的無解,而沃克夫人的沉默是一種淡然,因為她更加明白生活的意義,知道婚姻的內涵。
無論是拉姆齊夫人還是沃克夫人,家庭主婦的身份,好妻子,好母親的美好形象恰巧符合里波韋茲基教授所定義的傳統女性,但是兩位夫人的獨立,堅強,對于丈夫的扶持,自己面對殘酷世界的坦然,包括妻子獨攬狂瀾的個性又符合前衛女性的特點。因此,可見,拉姆齊夫人和沃克夫人是典型的第三女性。
三.男女作家筆下第三女性的創作差異
在伍爾芙筆下,拉姆齊夫人“灰白的頭發,憔悴的面容,才五十歲”,但穿著得體,善于社交,在周圍人里面,她是平聲見過最美的人物,“眼里星光閃爍,頭發籠著面紗,胸前捧著櫻草花和紫羅蘭,鬢發在風中漂浮。”[3]14拉姆齊夫人盡管年過半百,但風韻猶存,對男性的魅力不減當年。
《到燈塔去》中善用比喻等修辭手法,伍爾芙時而將夫人比作一棵“靜止的樹”,時而比喻為“殘敗的花兒”。細究其場景,凡是如此,都是當拉姆齊夫人與丈夫一起生活的時刻。文中描繪到,安撫完暴怒而失落的丈夫后,拉姆齊夫人“頃刻之間,像是一朵盛開后的殘花一般,一瓣緊貼著一瓣兒地皺縮了,整個軀體筋疲力盡的癱軟了。在極度疲憊的狀態下,她只剩一點兒力氣,還能動一動指頭來翻閱格林童話。”[3]45除了將本體與植物相對比,伍爾芙緊抓拉姆齊夫人的端正儀態,為了凸顯夫人在家庭與社交圈內的領導位置,中心作用,甚至把夫人比作“女王,居高臨下,傲然的觀望著她的臣民”[3]99。無論喻體是鮮花,樹,還是女王,伍爾芙都著力地突顯了拉姆齊夫人的特殊氣質--那種突破傳統的獨立現代女性的對于自我的渴望。她強大的內心精神光芒恰如燈塔,照亮每一個人。從中讀者不難看出,伍爾芙的女性主義信仰在拉姆齊夫人一人身上大放光彩。
在安德森筆下,同樣也多次描繪到了沃克夫人的身形。其中沃克夫人,生育后身體發福,整個身子在閱讀時常常臃腫地陷入沙發座里,像個“布袋子”一樣的中年女人[4]2。生了孩子后,“她的鼻子長得一般,眼睛也不出眾”,“頭發雜亂地堆著”,“自從婚姻,她就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了。”[4]2安德森的筆下,女人是愚昧的,麻木的,只靠外貌才能施展對于男人的魅力。這段婚姻開始是因為,當年沃克先生喜歡了年輕的夫人,親吻了她,和她結婚了,生了三個孩子;而婚后的沃克夫人,便令丈夫厭倦,疲憊,以致于他把精力投放在了一個不屬于自己的年輕學生瑪麗身上。安德森將瑪麗比喻為“年輕的未結果實的樹”[4]5同“靜止的”沃克夫人不同,她外貌齊整,品性自由,沒有受到婚姻的束縛,沒有叫現代虛無的社會所侵染,她年輕漂亮,不會撒謊,不會擔憂。小說中的兩位女性,不約而同地都被描繪成了一個沒有靈魂,沒有思想的生命,任由沃克先生擺布:如,年輕的沃克夫人,嫁給了他,品貌逐年消減;而自由的瑪麗被他親吻了,學會了撒謊,驚慌失措地離開了這個被詛咒的大房間。女人,在男性作者的描述中都成了犧牲品。
從《到燈塔去》與《陷阱之門》的對比研究中,讀者可以看出,盡管同時刻畫了一個第三女性的形象,伍爾芙的女性較安德森所刻畫的沃克夫人來看,更加獨立。拉姆齊夫人以一個獨立的個體的方式存在,并且不受男性角色的干擾,相反,還能反作用于男性角色的生活;而沃克夫人卻不同,除去身上新女性的淡然與堅強,她不是一個客觀的存在,而是男性世界的一個補充。男女作家對于第三女性的刻畫,從語言上,手法上,主題上都大相徑庭。因此,女性作家的女性寫作應該得到鼓勵和弘揚。
參考文獻
[1]郭乙瑤.《性別差異的詩意書寫--埃萊娜·西蘇理論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里波韋茲基,吉爾.《第三類女性:女性地位的不變性與可變性》[M].許華,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2009:44-90.
[3]Woolf,Virginia.To theLighthouse.NewYork:WordsworthClassicsPress,1994.
[4]Anderson,Sherwood.The Door of the Trap in Collected Stories. 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