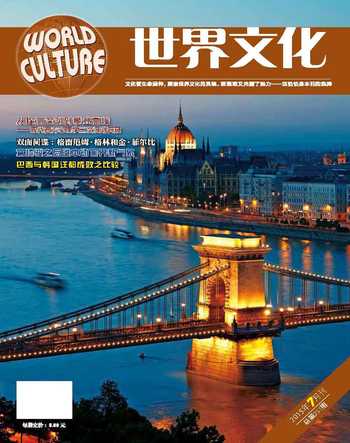美國猩猩都聊哲學了
有這么個小說,故事里的男主角愛上一個未成年的小姑娘。說到這里,有個名字恐怕已經呼之欲出——洛麗塔。沒錯,這正是小說的題目。
可這里說的,不是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那部名作,而是一個短篇小說,作者德國人,筆名海因茨·封·里希貝爾格。此人曾作為騎兵軍官參加過“一戰”,退役后進入報 界。1929年,他成為“齊柏林號”飛艇環游世界的隨行記者,全程報道此次創紀錄的空中航行,因此薄有文名。希特勒上臺后,他像很多人一樣,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納粹)。《洛麗塔》是他早年行伍時期的作品,收錄在一本名為《被詛咒的喬貢達》的小說集里。2004年,德國學者馬爾先后在《法蘭克福匯報》《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撰文,稱納博科夫可能無意識地援用了里希貝爾格的故事原型,而且兩位作者都曾在同一時期住在柏林。
納博科夫本人對此卻另有說法。1956年,在《洛麗塔》的美國初版后記中,作者聲稱該書最初的靈感,來自報紙上的一篇消息。那篇報道講到巴黎植物園馴養的一頭黑猩猩,被動物學家忽悠著,畫出世界上第一幅出自動物之手的速寫——畫面上潦草地排列著分割它視野的鐵欄。然而不論作家提到的那篇報道,還是那頭猩猩畫出的速寫,始終沒有人找到其下落。由此也可看出人類記憶不靠譜的程度,即便博聞強識如納氏本人。
不久前,巴黎植物園還真辦過一個展覽,叫做《猩猩之路》。象征性的雨林環境中,觀眾可以了解猩猩的六個亞種,它們的進化過程和生存威脅。此外也有它們的社會交流方式。如您所知,所有這些方式當中,并不包括繪畫。現實中被剔除的細節,卻不妨在虛構文學中,覓得落子的眼位。美國年輕小說家本杰明·黑爾的《布魯諾·利托莫爾的進化》(有漢語版譯為《進化吧,布魯諾》)中,敘述者是一只黑猩猩;他在掌握人類語言之前,正是通過繪畫表達情緒和想法,后來還賣出高價。但使他脫穎而出的,卻是語言,無遠弗屆的人類語言。
小說中的男主角布魯諾,是歷史上第一只掌握人類語言的黑猩猩,也是整個故事的敘述者(確切說是倒序者)。他像《洛麗塔》中的失足大叔一樣,因為殺人,在囚室中回顧自己的生平。他出生在芝加哥林肯公園,母親是動物園的“家生子”,父親則是來自剛果雨林的非法獵獲物。野外成長而來的野蠻力量,使它成為動物園的猩猩王,但也染上人類的惡習,比如抽煙。游客們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在提供香煙時,表現十分慷慨。更多的好奇心來自研究人員。他們向接受智力測驗的猩猩,展示放在一個透明盒子的桃子。最后是布魯諾,找到開啟盒子的機關,拿到果實,并由“它”晉身“他”,這一新的格位。“我敢食用一只桃子嗎?”他借用艾略特詩中普魯弗洛克的口氣反躬自問。答案是“的確,我敢”。他吞下禁果,并將觸犯天條。
這本小說有些類似本雅明所謂的引文匯集,同時充滿狂歡式的反諷;賣弄到有些欠扁的老克勒文風,處處和當今流行的極簡原則對著干,用在人類角色身上,該書恐怕得自費出版。換作猩猩便大不相同。這個天才動物頓時成為奇異的語言標本。像世上所有天才一樣,他也需要有人慧眼識珠,而此人恰好是個美女。當年輕的靈長學家麗迪亞·利托莫爾出現在研究中心,布魯諾的生活就此改變,愛情也隨之發生。就像童話中的被咒王子,布魯諾以獸形現身,卻懷有人類渴望智性不朽的欲望。這個進化意義上的勢利眼,看不上自己本屬的物種,對于青梅竹馬的雌猩猩,基本無動于衷。
他愛上了人類女性。按照他的描述,這個女性如此完美,除了北歐諾迭克式的相貌,作為芝加哥大學博士,她還是良好教育的產物,談吐措辭典雅,句讀精準到每個分號清晰可辨,只有一絲外省口音隱隱出沒,來自她的阿拉巴馬偏遠故鄉,就像一只交響樂隊的弦樂組中,隱藏著一把伴奏鄉村音樂的班卓琴。
據說黑猩猩與人類的基因近似度,高達百分之九十五。點睛的一筆,或許就在語言。《動物解放》的作者彼得·辛格,也把猩猩說成人類失語的另一半。語言是布魯諾修成人身的最終障礙,也是唯一途徑。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就是那個著名公知)確信,語言能力為人類先天獨有。為驗證這一論斷,曾有心理學家做過一個實驗。他選中一只名叫尼姆的黑猩猩幼崽,從它母親懷抱中帶走,寄養在紐約一個富有家庭;稍微長大,又將其關進研究中心。專家們軟硬兼施,向它灌輸啞語,用手勢和人交 流。它曾學會表達一些簡單的意思,但始終不會按語法原則組織手勢。后來因經費短缺,項目半途而廢。猩猩又被送到一家藥物研究中心,成為血清研究的受試對象,直到動物保護人士把它買下,養在德州一座牧場,并于26歲去世。
在小說里,布魯諾掌握了語言,通過“他者”的視角,對世界重新編輯和估價。他把麗迪亞的姓氏利托莫爾,用到自己身上;自我命名的權利,至少被他實現了一半。“我用詞語塑造自己,我把自己寫入世界,”他說。顯然,這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小說人物。與之相比,來自16世紀的孫悟空,從獲得姓名的那一刻,就是一個被收編者。像真實存在過的尼姆一樣,布魯諾被美女研究者帶回家。在家庭生活中,他學會了布置餐桌,只是晚餐一旦有第三者參加,他會十分不爽。這是一只戀愛中的猩猩。
從樹上爬下,來到文明的地面,得救之際便已墮落。文明除了魅力,還有偏見和傲慢。“我自知不配廁身于人類社會,可是誰配?”這是王爾德,也是布魯諾的追問。 跨越物種的禁忌戀情,讓麗迪亞失去學術地位,同時結束了他的學徒時代。為他舉辦的畫展上,一番大鬧天宮式的發泄后,他和女主人逃離芝加哥,南下跑到科羅拉多一座牧場。他的成長故事,由此進入漫游階段。與他恰好相反,已經懷孕的麗迪亞因腦部腫瘤,逐漸喪失語言能力。后來在紐約,布魯諾遇到一家地下劇團,有機會在莎士比亞的《暴風雨》中,扮演人怪之間的卡列班。這個經典角色,就像是為他而設。
布魯諾的敘事口吻,本身帶有明顯的舞臺腔,夸張而賣弄。談到素面朝天的麗迪亞,布魯諾說張揚從來不是她的風格,隨即補充:“張揚是我的風格。”似乎文學中的動物視角敘事,都有巴洛克風格的浮夸矯飾。兩個世紀前的德國作家霍夫曼,在《公貓妙兒的生平和見解》(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格麗塔》、夏目漱石的《我是貓》,都是其影響的產物),也是通過一只貓的自傳寫作,把古往今來的經典惡搞一遍。貓能做到的事,靈長類更不在話下。
1909年, 法國數學家勃萊爾在《概率論原理》中,用“打字猴子”這個比喻,闡述字母的隨機性排列:一群猴子在打字機上亂敲,最終可能打出巴黎國立圖書館全部藏書的內容。這個想法流傳到英語國家,又被通俗化為“無限猴子定理”——無限多只猴子,或給一只猴子無限多時間,就會在鍵盤上打出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作為漢語使用者,我準備用《西游記》替換莎翁。假定一只猴子拼音輸入漢字(總不能先背五筆字型吧?),且電腦鍵盤共有60個鍵,那它一次性正確敲出“孫悟空”三個字的概率,考慮到輸入法的聯想功能,也低于六十分之一的三次方。那么這只猴子若想寫出整部《西游記》,恐怕壽命真要達到我們宇宙的年齡?
但布魯諾拒絕打字。鍵盤上“搜尋—捕捉”的過程,讓他意識到自己的原始動物性。他無法容忍這種痛苦。霍夫曼書中的貓,克服了解剖局限帶來的執筆困難,進行書面筆耕。而布魯諾更愛擺譜嘚瑟。他的自傳是通過口授完成的。他把負責筆錄的研究員,稱作他的amanuensis。筆者不敢確定這個矯揉造作的古老用語,是否可以粗譯為書童。這猢猻,怕是用力過猛了。
《布魯諾》應該屬于大詞匯量寫作。從翁貝托·艾柯到大衛·華萊士,都為這種寫作提供過范本。他們構成當代文學的一極: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人的物質、歷史背景和哲學前提,比人本身更重要。他們的知識興趣,以及對于本源命題的關心,似乎在中國當代文學當中相當罕見。后者更多強調現實中的人際智慧,關注對象限于五倫之內,而終極善惡也往往被簡化——有時也會復雜化——成為是非。好像世界無非一桌麻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