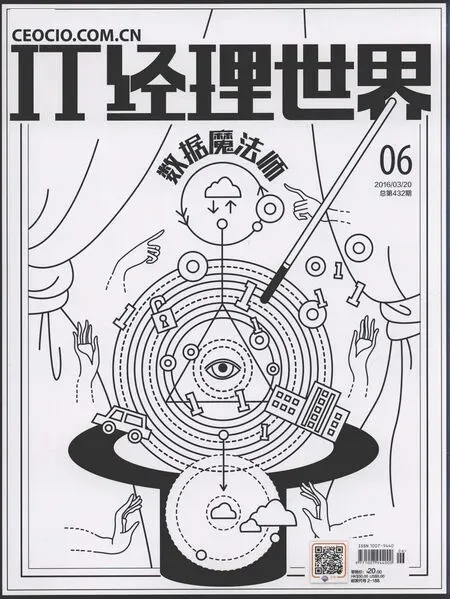搖滾鳥和它們的音樂
陳婧

鳥兒們演出了一場非同凡響的電子音樂會
你能想象一只只飛鳥變身搖滾吉他手,彈奏起動人的音樂嗎?這件由法國聲音藝術家塞萊斯特·布希耶-穆杰諾(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創作的《從這里入耳》(From Here to Ear)再一次讓我們思考音樂該如何產生,我們又該如何與音樂產生互動。
在這次別開生面的場景裝置個展中,穆杰諾將畫廊空間轉變成為一座可以供觀眾直接走入其中的大鳥籠,70只小鳥自由翱翔其間。“鳥籠”的地面被沙石覆蓋,陳列著電吉他、樂架和音箱,鳥兒們累了就停歇在上面。它們尖銳的爪子如同細細的牙簽,撩動著琴弦,發出別樣的聲音,隨后這些聲音被收集并通過揚聲器擴大到整個室內空間。由于每條琴弦的音高并不一致,在這飛來飛去和停停飛飛間,鳥兒們就演出了一場非同凡響的電子音樂會。
穆杰諾給這些鳥兒彈奏的樂器十分名貴,14把來自美國Gibson的“萊斯·保羅”電吉他。這把樂迷們心中崇拜的經典吉他,選用了上乘木材制成了桃花心的木琴身和光亮的楓木面板。“聘請”的鳥兒藝術家也經過細心挑選,學名叫“斑胸草雀”,通常被作為觀賞鳥類飼養,或是科學家用于脊椎動物行為和演化的研究。它們體型雖小,卻非常活躍,喜歡在寬敞的空間里飛行,但通常并不擅長鳴叫。斑胸草雀有高度的社會性,見到人群并不羞澀,它們成雙成對行動,雄鳥會通過“唱情歌”向雌鳥求偶。在表演時,它們的行動既受到同伴的影響,也會與觀眾互動,創造一個持續變化的聲學效果。

揚聲器不僅收錄了琴弦發出的聲音,穆杰諾還有意加入了電聲效果
展廳里不時有鳥兒從你頭上飛過,偶爾還會停在你的肩膀上。每把吉他都被橫向放置,因此當有斑胸草雀停落在吉他上或是起飛時,琴弦都會在無意中被輕輕撥動。它們在移動中,從一根弦跨到另一根弦上,就像是吉他手用撥片在擦弦。它們一會兒停在升E弦上,在聽到回聲后,又躍躍欲試地抓握另一根琴弦。由于琴身十分光亮,這些草雀在移動時顯得有些顫顫巍巍,讓摩擦聲更加劇烈。旁邊的揚聲器不僅收錄了琴弦發出的聲音,穆杰諾還有意加入了電聲效果,如混響、過載或是延遲,還有和弦,讓“吉他手們”的表演更加富有魅力。
由于展廳面積有限,每次只能容納25名觀眾。要想進入其中親身觀摩演出,至少得排上大約二個小時,但還是有很多家長帶著孩子們前來。斑胸草雀們創作的音樂不僅在現場表演,還通過YouTube電視向全球轉播,僅僅在一個月的時間里,這個裝置就成為了YouTube上當月收視率最高的視頻之一,超過60萬點擊率。錄制動物和樂器互動的藝術視頻,對YouTube來說還是史無前例的。
在聽到自己彈出的樂聲后,這些斑胸草雀會成群飛起,發出歡快的鳴叫聲。一名樂團的吉他手在觀看草雀們的現場表演后表示,這些草雀吉他手的臺風很像吉米·佩奇,在彈奏時會隨著音樂搖擺起來。更有意思的是,在英國倫敦展覽期間,除了收獲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演唱會,這些“吉他手”們還在一個月的表演期間產下了63枚卵,有一枚還誕生在復活節時前來參觀的游客的包袋里。
作為音樂家、作曲家、造型藝術家的穆杰諾,以其在國際藝術舞臺上成功占據獨特地位的視覺和聲音裝置作品而令人著迷。他的作品被重要的公共和私人機構收藏,例如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澳大利亞新老藝術博物館和以色列博物館等。他在2010年榮獲享有崇高聲望的法國藝術大獎——馬塞爾·杜尚獎。他還擊敗了同為提名者的奪冠熱門人物Tatiana Trouvé,將代表法國參加2015年夏季舉行的第65屆威尼斯雙年展。穆杰諾將音樂作為一種傾聽的形式,邀請觀眾遣興地傾聽我們環境中的聲音。在他的精心營造下,音樂展現了一種非完美的、意外的自然美。
生于1961年的穆杰諾早年曾在法國尼斯音樂學院接受正規音樂訓練,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時間里,他在一家先鋒藝術劇場擔任編曲家,并在偶然的一次機會中開始在博物館和畫廊展示聲音藝術。他的作品專門探究偶然的聲音,擅長使用可以操控的物體,去創作出一種“刻意安排的”隨機音樂,并同時包容了視覺藝術。例如,他在歐洲的第一場個展是在位于法國圖盧茲的Abattoirs當代藝術空間,使用探空氣球創作出了這樣一件裝置作品——用氣球進行射線叩擊,發出有規律的聲音,并形成怪異扭曲的圖像符號。
穆杰諾認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音樂”,他看到了所有物體都可以創造音樂的無窮潛力。例如,這位久居巴黎的藝術家,曾經讓13臺吸塵器奏響交響樂,并讓它們模仿此起彼伏的有趣的打鼾聲。街道上掠過樹的風在他那里,也是一種隨機產生的音樂,帶著自己的旋律。他還讓盤子、杯子在藍色的充氣泳池里自由漂浮、撞擊,并在麥克風和揚聲器的幫助下,成為美妙的音樂。在巴黎,我們在工作室里采訪到了這位“能讓一切成為音樂”的藝術家。
記者:什么原因激發您創作了《從這里入耳》?
穆杰諾:一天晚上一些畫家來我家聚餐,在用餐期間他們聽到了音樂聲,然后問我這些樂聲來自哪里。我打開了門,他們看到了一些雀鳥在敲擊一些金屬碟子。這讓我開始嘗試用另一種方式,讓這些鳥兒音樂家去進行表演。我從小的夢想就是做音樂,上了音樂學院之后讓我有機會嘗試不同的樂器。這個作品中在找到吉他之前,我也想過小提琴、鋼琴,最后選擇了吉他,作為我自己作品的呈現方式。這件作品的目的不是為了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去展示鳥類,而是人類被邀請進入鳥類們的生活空間和領地。這件作品希望啟發人類的想象力,而不是去探索技術的無限可能,我想提出的問題是,究竟什么才是音樂?
記者:您是從哪里邀請到這些斑胸草雀演奏家?
穆杰諾:這些斑胸草雀來自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島,它們并非珍惜物種,而是觀賞鳥類,平時由專業人員飼養,專門供影視劇組使用。在表演期間,我們請來有25年經驗的鳥類專家設計它們的籠舍和整個環境,給它們足夠的飛行空間。每天會有工作人員通過監視器察看它們的狀態,并有獸醫每周前來觀測它們的健康情況,如果有鳥兒生病就會被隔離。我們還設計了專門的機制,讓那些即便飛離鳥巢區域的斑胸草雀,也可以安全地回到家。它們得到了很好的照顧,生活在懸掛著的“草雀公寓”里,每天有自然燈光模擬日出日落,還有一些斑胸草雀在演出期間繁衍了后代。不幸的是,在展覽結束之后,吉他手們又將回歸籠舍的生活。

穆杰諾認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音樂”,他看到了所有物體都可以創造音樂的無窮潛力
記者:這些斑胸草雀接受過人工訓練嗎?
穆杰諾:在每個城市展出時,觀眾們問的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這些草雀真的會自己創造音樂嗎?事實上,我認為它們會創造音樂,它們根據自然的特性表現自己。比如雄性草雀為了求愛繁衍時,在潮濕的環境里或者看到綠色物體時,就會變得非常活躍。但是它們的表演也需要我們在藝術上的技術性配合,我花了大概10天時間在展廳里走來走去,研究不同的音符應該從哪個角度發出,它們的音樂應該具備哪些聲學效果。如果你想了解一種生物,你必須與它們進行互動。在作品里,我并不是使用這些鳥類,而是像與其他藝術家或是一個搖滾樂隊那樣,進行著友好的“合作”。

記者:你觀察到觀眾們在參觀時通常會有哪些反應?
穆杰諾:觀眾進入這個空間時第一反應是變得安靜,他們靜靜地站在這里,欣賞、聆聽那些在人工環境中的野生動物展示它們的天然習性,或者觀眾會留神腳下,怕一不小心踩到這些活潑的鳥兒。盡管畫廊里的環境是模擬自然條件的,但是因為有了適宜的溫度和模擬陽光,觀眾也仿佛進入了澳洲的叢林。觀眾們與鳥類的互動,也是展覽組成的一部分。創作的音樂來自14把電吉他,當電吉他被同時或先后奏響時,觀眾們可以最直觀地看到草雀們以哪種方式在對人類活動進行回應。例如,它們選擇待在房間的哪里,以及以什么動作去回應觀眾的闖入。尤其當我們經過電吉他旁邊,或者在鳥巢底下走過的時候,它們的舉動常常會讓觀眾大吃一驚;有一些觀眾甚至會以為,這是人類在彈奏著吉他。
記者:斑胸草雀在看到觀眾們移動時,會產生應激反應嗎?
穆杰諾:草雀會把房間看作它們自己的世界,把電吉他當作一棵音樂樹。草雀們并沒有回避這些參觀者,而是表現出強烈的好奇心和試圖探索發現那些外來者,這些行動都會創造更多的音樂。它們很快就能弄明白從一根琴弦跳到另一根時,產生什么樣的結果。你看,這只斑胸草雀看到人類走過它的巢穴時,就悄悄地停在他的鞋子上,它非常愛與人類社交,這是它第一次這么嘗試做,非常酷。不同的草雀還有自己的小脾氣和個性。觀眾們都對這種互動非常滿意,我也在思考未來的展覽里如何發生更多類似的“生命間的邂逅”。我喜歡把自己稱為“生物作曲家”,我的作品是奉獻給每個生命的。
記者:您在這次展覽中有什么意外的發現嗎?
穆杰諾:草雀創作的音樂和我們想象最不同的一點,是它們的音樂聽起來更像搖滾樂。我們在作品中發現,鳥類成長過程中一直伴隨它們的聲音,對它們的音樂創作影響很大。生活在城市中、受到噪音干擾的鳥類更喜歡輕柔、安靜的聲音,避免去制造太多的噪音,在學習使用電吉他的過程中,它們會嘗試創作清脆明亮的聲音。而在野外長大的鳥類,則喜歡發出比較聒噪、有沖擊力的聲音。幼鳥受到父母的影響比較大,它們創作的音樂不僅會模仿求偶時的叫聲,而且會去模仿自己父母的歌聲。還有雄性鳥類喜歡向下張望,它們是為了看護好自己的地盤,打敗競爭對手。比如在展廳中間的三把吉他,就最容易發出噪音,因為對這塊地盤的爭奪最為激烈。
記者:您以前是受過專業教育的音樂家和作曲家,為什么會從事聲音裝置和視覺藝術的創作呢?
穆杰諾:我的家族和藝術息息相關。我的曾祖父是攝影師,祖父是漫畫家,父親為教堂繪制彩繪玻璃和制作公共雕塑,母親是從事城市規劃的社會學家。我的父母認為藝術和文學的所有形式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們的藝術家和作家朋友經常來我們家聚會,并創造了非常藝術的氛圍,但他們從來不讓我看電視。我很小時就喜歡聽不同類型的音樂,不管是古典、民族、流行還是爵士等等,每個星期都去看音樂演出或是藝術展覽、電影。我20歲有了自己的公寓,也有了人生第一臺電視,我沒日沒夜地看電視,直到有一天我扔掉了這臺電視。我對自己說,總有一天我要做一個項目,改變這種被動式的觀看方式,讓觀看者學會去判斷自己在看、在聽的究竟是什么。以后,這些疑問和思考一直伴隨著我的作品。
記者:一些人會把您的作品歸入“自我發展的結構音樂”,只是交代了一個場景,然后由主人公自己去運作,他們還會把您的作品與斯蒂夫·萊奇這樣的結構先鋒作曲家進行比較。哪些人物對您的藝術創作有比較大的影響?
穆杰諾:我受過很多藝術家作品的影響,但他們對我的影響都是潛移默化的。對我來說,一個實實在在的故事或是記憶,比一些空泛的理論更有吸引力,所以有些藝術家的作品會讓我感到失望,因為他們的作品不能讓觀眾感到有意思,或是有生命力。我并不想給自己在藝術史中找出對應的位置,而是希望觀眾在進行美學鑒賞時,能夠發現我們之間的某些共通點。
記者:作為法國最知名的藝術家之一,《從這里入耳》這件聲音裝置作品給您的藝術道路帶來了哪些改變?


它們尖銳的爪子如同細細的牙簽,撩動著琴弦,發出別樣的聲音
穆杰諾:現在我被朋友們戲稱為“巴黎的鳥人”。我很高興,現在我的作品有了比較高的知名度。但是幾年之前,周圍的朋友們都認為我瘋了,因為我想到不是由人類去彈奏樂器,而是讓鳥類的爪子代替人類的手指。我經常會想這樣的問題,如何才能創造人類之外的音樂形式?這些音樂不是由電腦創造的機械的聲音,它必須是“有機的”。以前在我的藝術作品里出現過的動物有松鼠、魚類、貓,還有綿羊。但這次對我來說是最震撼、最感動的一次。我會和朋友說,我找到了夢寐以求的“飛行著的手指”,它如同上帝般的手指,在自由地彈奏著這些樂器,譜寫著音樂。我想,藝術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方法,去達成自己的目的。